0
留言稍后联系!

本文摘要:内容摘要: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墨学虽不如孔学、佛学和西学重要,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谭嗣同对墨学的接受实际上是他对历史处境和生命处境的感受与回应,青年谭嗣同只关注墨学中的任侠精神和自然科学部分,且对任侠精神的理解只限于游侠生活和游侠理想
内容摘要: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墨学虽不如孔学、佛学和西学重要,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谭嗣同对墨学的接受实际上是他对历史处境和生命处境的感受与回应,青年谭嗣同只关注墨学中的“任侠”精神和自然科学部分,且对“任侠”精神的理解只限于游侠生活和游侠理想,至其作《仁学》时才对墨学有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认识。
墨学内部本无派系之别,但在谭嗣同的视界中则被划分为“任侠”“格致”两派,谭对这两派的理念推崇备至并亲身践行。除无条件服膺于孔学外,谭嗣同对包括墨家在内的其他诸子学说均持批判继承态度,他基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考量,明确表示不赞同墨子“尚俭非乐”的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崇奢黜俭”的消费观,实可视为对墨家思想的超越。
关键词:谭嗣同,墨学复兴,任侠,崇奢黜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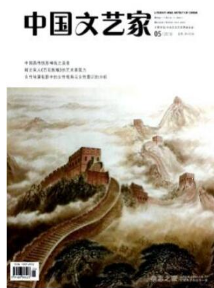
晚清时期墨学得以复兴,治墨者亦随之增多,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等,其中还存在一位虽谈不上“治墨”但又与墨学有着特殊渊源的士人———谭嗣同。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相比,谭嗣同既无《墨子》的校勘著作,也无长篇论述墨学思想的著述问世,其对墨学的叙述大多散见于《仁学》当中。
严格来说,谭嗣同对墨学更多地只是一种认知和推崇,而非研究。不过,谭嗣同虽较少从学理层面研读墨学,但其对墨家“任侠”精神的践行和对墨学的推崇则非梁启超、章太炎等所能及。学术界目前对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的墨学研究关注较多,而对谭嗣同与墨学的关系则甚少涉及①,这与墨学与谭嗣同之间的特殊关联不无关系。从谭嗣同甚少的叙述中探寻其与墨学的关系,似乎本身即存在着建构之嫌,但毕竟谭嗣同以身殉难之举和“崇墨贬儒”的倾向等都表露出了相当明显的墨学渊源,加之其在晚清思想史上的特殊地位,探寻谭氏烈士精神背后的墨学因素亦显得相当必要。在不同层次的概念框架中,概念具有不同性质,概念必须在特定的框架中获得意义[1]。
墨学对于晚清不同士人亦有着不同的意义,谭嗣同的言行思想并非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无不本之于墨学,宗之于墨学”[2]。譬如,其以身殉道的侠义精神就不唯受墨家思想的影响,还与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和佛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生死观有关。把谭嗣同所言所行皆归因于墨学的结论不仅过分拔高了墨学在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还掩盖了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基于谭嗣同思想体系及其对墨学认知的特殊性,在研究谭嗣同思想中的墨学渊源时,要着重注意发掘其思想萌生的原初环境,并与谭思想体系中的其他思想以及同时代治墨者的研究相比较,若不注意这点,就很容易出现过度解读的情况。有鉴于此,笔者拟立足西学东渐、“墨学复兴”的时代大背景,以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儒、释、耶等思想因素为参照,剖析谭对于墨学的认知和推崇,挖掘烈士精神背后蕴含的墨学渊源,这无论是对于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体系,还是把握当时“墨学复兴”的时代潮流,均具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一、谭嗣同早年对墨学的接受与认知转向
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墨学占据重要地位。墨学由隐到显,由微到著,直至清末形成复兴潮流,蔚为壮观。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或可视作霍布斯鲍姆笔下的“被发明的传统”②,是西学冲击与学术变革交相作用的结果。在晚清变局下,墨学这一传统资源被充分挖掘,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适应了社会需要,被时人用来振世救弊和回应外来文明的挑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墨学在近代的重现固然是时势使然,但也与晚清学人的推崇休戚相关。晚清士人对墨学的认知表现为两种,一是开展学理研究,二是对墨学精神的提倡和弘扬,当然,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为条件,相互包含。不过,即便是对墨学纯粹的学理性研究,晚清的知识分子们也会将墨学中的传统因素与时势相结合,且不能完全摆脱对墨学的认同与推崇。譬如,梁启超就曾论道:“今欲救中国,厥惟墨学。”[3]
章太炎亦认为:“墨子之学诚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则非孔老所敢窥视也。”[4]毫无疑问,救亡的时代旋律促使知识分子从传统资源中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改造萎缩的心灵,墨学正好契合了这种需要,从而推动了当时的墨学研究。对墨学的研究与推崇使得墨家的人格精神进一步为世人所认知和接受,并将其发扬光大。谭嗣同对于墨学的接受更多表现为后者,他在变法失败后的以身殉道之举即为例证。
在对谭嗣同思想体系的建构上,墨学虽不如孔学那般对其影响至深,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谭的书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对墨家思想有着独到见解,而且对弘扬墨学精神表现出极大兴趣。谭嗣同开始接触墨学是在1883年,其时谭只有19岁[5],但第一次读《墨子》时他就已“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谭氏初读《墨子》时正处于墨学复兴的早期阶段,他有条件系统地接触、研读、吸收墨学,无疑得益于墨学复兴这一历史潮流。谭嗣同身处墨学复兴的历史潮流之中,再加上早年“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6]的经历,使得他从小养成叛逆心理,对“纲常名教”深恶痛绝,故一接触墨学便沉醉其中。
“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足何惜。”[7]289-290不过,谭嗣同早年对墨学的认知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西学墨源”说的赞许以及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审视墨学。“西学墨源”说虽为回应西学入侵的被动之举,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该说并不具有合理性,而谭嗣同早年对这一学说极为推崇。他曾论道:“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以此知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中外所不能超越。”[7]
399在1886年所作的《治言》中他亦谈道:“世之言夷狄者,谓其教出于墨,故兼利而非斗,好学而博不异。其生也勤,其死也薄,节用故析秋毫之利,尚鬼故崇地狱之说……景教之十字架,矩也,墨道也,运之则规也。”[8]233可以看出,谭嗣同在谈及墨学时赞同“墨学西源”说并表现出“夷夏之防”观。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直接促成了谭嗣同对墨学认知的相关变化,这一变化从《治言》和《仁学》内容体系的对比之中可以看出:谭嗣同早年只关注墨学中的“任侠”精神以及自然科学部分,至其作《仁学》时,则对墨学有了更全面和系统的认识。不过,青年时代的谭嗣同对“任侠”精神的理解还只限于游侠生活和游侠理想,并未参透“任侠”精神的实质。他那时“好任侠,善剑术”,甚至还于1884年离家出走,“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6]。
游侠生活对他的性格养成和人生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后来他在维新失败后真正践行“任侠”精神奠定了基础。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谭嗣同对墨学的接受实际上是他对历史处境和生命处境的感受与回应。一方面,谭嗣同早期深受“墨学复兴”潮流的影响,至其思想成熟之时,又适逢传统义理的根基开始动摇,他急切地向传统资源寻求新的政治秩序,这其中就包括墨学,当然也有儒学、佛学以及道家的部分思想;另一方面,谭的一生为死亡阴影所萦绕,同时也深受家庭矛盾以及情感纠纷所带来的痛苦折磨,他对墨学的认知与推崇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他在这种处境中挣扎时心声的自然流露。
二、谭嗣同对墨学的派系划分及其理念的践行
侠义精神是墨家的重要表现。墨学内部本无“任侠”“格致”的派系之别,谭嗣同在《仁学》中从主观认知上将墨学分为两派。关于“任侠”一派,谭把墨侠精神与东汉党锢之士、宋代永嘉学派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略得其一体”[7]289,由此可见谭嗣同心中的“任侠”精神既是党锢之士痛陈时弊、兼利天下之志,亦是永嘉学派那种舍身为公、经世致用之志。
谭嗣同真正践行“任侠”精神是在戊戌变法时期,日益腐朽的封建王朝以及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谭嗣同产生了救世思想,再加上墨学“任侠”精神的引导,他在时代变局中心怀摩顶放踵之志,试图学习党锢和永嘉之士,以“任侠”精神力挽狂澜。谭嗣同把日本的“变法自强”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其俗好带剑行游,悲歌叱咤,挟其杀人报仇”[7]344的气概,他认为日本变法的成功实则是“任侠”精神促进改革的成功案例。
在此理念的指引下,身为改良派的谭嗣同竟萌生了暗杀思想,他曾论道:“若其机无可乘,则莫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7]344谭嗣同甚至还有过“杀固恶,而仅行于杀杀人者,杀亦善也”[7]301的言论。不过,即便如此,谭嗣同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向革命,这与他的阶级立场不无关系。谭氏的侠义精神中掺杂了许多封建纲常伦理,在整个维新变法过程中,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礼节尤其是“忠君”思想的约束。
谭嗣同虽没有将暗杀付诸实践,但其以身殉道、舍生取义之举显然是墨家“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9]理想的践行。谭作为“为变法流血”第一人,他的精神对后来许多革命党人侠义之性的养成影响至深。谭嗣同在狱中“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7]532的悲壮精神虽是其践行墨家“任侠”精神的结果,但亦掺杂有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因素。
谭嗣同坐求等死的心态显然是儒家“杀身成仁”的思想和佛教“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生死观以及墨家“任侠”精神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只受单一思想的影响。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墨学在对其侠义精神的养成和殉难之举的影响上并不占主要位置③,谭向来对孔学极为推崇,后期又沉醉于佛教唯识宗的义理当中,墨学更多地只是谭所认为的中介学说。
在“仁而学,学而仁”[7]289思想的指导下,谭嗣同践行“任侠”精神的同时,尤为重视他所说的“格致”学问。谭氏在《仁学·自叙》中将墨家分为两派,一派是“任侠”,另一派则被他称为“格致”。谭嗣同认为“格致”之学在秦有《吕氏春秋》,在汉有《淮南子》,他们各识“格致”之偏端,墨家的“任侠”“格致”两派实是“近各孔、耶,远探佛法”的中介。
《吕氏春秋》《淮南子》均是杂家的代表作,它们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谭嗣同把它们当作自己推崇的墨家之一端,足以见得谭嗣同的治学取向是广泛涉猎、博采众长。谭嗣同所指的“格致”学问即是“杂取百家,兼收并蓄”之学,且“百家”并非独指诸子百家,还应包括西学、耶教、佛教等。“格致”的信念促使谭在墨学复兴、西学东渐的大环境下广博而贪婪地读书,他广泛的兴趣可从其《学篇》中明显看出。
《学篇》共七十七则,系谭嗣同的读书札记,凡经、史、子、集、理、化、数、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这显然与其所倡导的墨家“格致”理念不无关系。先秦墨学只有前后之分,并无派系之别,所谓的“墨有两派”,一为“任侠”、一为“格致”实际上是谭嗣同的主观诠释,这与其对孔学和儒学的区分相差无几。“墨有两派”无疑奠定了谭嗣同对墨学的认知基础,不过,“格致”之学实际上还与谭嗣同对西学的兴趣有关,墨家当中真正使他心仪的还是“任侠”精神,这种“任侠”思想和他的游侠经历以及豪爽的性格极为相契,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相当影响。
三、谭嗣同对墨学的推崇与“崇奢黜俭”的提出
谭嗣同对墨家“任侠”与“格致”两派的划分更多的只是一种认知,其对墨学的推崇则集中表现为“崇墨贬儒”的取向。当然,基于谭嗣同对孔学和儒学的区分及其对孔学的服膺,此处的“儒”并不包括孔学。谭嗣同认为墨家思想除了“尚俭非乐,似未足见于大同”[7]289之外,其所蕴含的“兼爱”理念足以与孔子的“大同”理想相媲美。
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儒抑墨”不同,谭氏在关于“仁”的学说上把墨家提高到与儒家相同的高度,实则体现了他“崇墨贬儒”的倾向。1894年前后,他就曾与梁启超、夏曾佑等发起过“排荀运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贬儒”观念。当他历经世事,心智较成熟之际,救世理念促使他运用“兼爱”理想抨击纲常名教,为墨家正名。
谭嗣同引“兼爱之旨”大胆针砭时弊,指出了“士大夫之才窘”“文字之祸烈”“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7]341等种种乱象。针对历来把墨子兼爱思想说成是“乱亲疏之言”的观点,谭嗣同发出了“墨子何尝乱亲疏哉”的质问,并辩护道:“亲疏且无,何况于乱?不达乎此,反诋墨学,彼乌知惟兼爱一语为能超出体魄之上而独任灵魂,墨学中之最合以太者也。”[7]312“最合”二字不仅阐发了兼爱和以太的统一性,且进一步表现出他对墨家“兼爱之旨”的推崇。他对儒家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及对墨家“兼爱之旨”的推崇,正是为了冲决各种阻碍“通仁”的网罗,达到“一则通,通则仁”的境界。
四、结语
相比同时代的其他士人,谭嗣同的思想体系较为特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庞杂,梁启超就曾形象地形容他“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10];二是兼及改良和革命的成分。而在其庞杂的思想体系中仍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墨学在谭嗣同的思想体系中不占主要地位,谭嗣同对墨学阐述最多的无疑是其“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近各孔、耶,远探佛法”[7]289的中介功用,但墨学到底如何发挥这种中介功用,谭在篇幅有限的《仁学》中并未给出明确答案,相关研究也未对这一问题深入探讨。
不过,我们或可从谭嗣同一段关于“仁”和“以太”的论述中窥得墨学这种中介学说的运作机制。谭曾经集中阐发过各家关于“仁”的学说与“以太”的联系,他认为“以太”可以有多元化的表述: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1]293-294。
由此观之,谭嗣同在论述“仁”的时候并非独尊一家,而是涉及到了孔、佛、耶、墨各家关于“仁”的学说,这种广泛涉猎、博采众长的做法无疑就是其所推崇的墨家“格致”派的特征,“格致”是一种手段,也是墨学作为中介学说的本质。此外,谭嗣同在其著述中也对庄、列、老等其他诸子学说有所涉及,但在关于“仁”———即《仁学》核心义理的阐发上,除了孔、释、耶三种主要思想外,只选取了墨家的“兼爱”,足以看出墨学这种中介学说在其心中的地位要远高于孔学以外的其他诸子学说。谭嗣同在两次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提到了他对待传统学说的态度,即:“诸子百家,其言道有不相入者,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7]
529他对墨家也持这种批判继承的态度。在谭嗣同的视界中,墨学可分为“格致”和“任侠”两派,二者是沟通诸家的中介,其“兼爱”理念与“以太”的本质最为相契,甚至可以与孔子的“大同”理想相媲美。谭嗣同对墨家“任侠”与“格致”两派的划分更多地只是一种认知,他对墨学的推崇则集中体现在“崇墨贬儒”的取向上。
不过,谭嗣同虽在多方面对墨学推崇备至,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自己的理性思考,他不赞同墨子“尚俭非乐”的主张,并创造性地提出“崇奢黜俭”的思想,实是对墨家思想的超越。谭嗣同对墨学的认知有其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关于谭嗣同对墨学的认知与推崇甚至是超越,也只有放在当时的时代脉络中才能更好地理解。
相关刊物投稿:《中国文艺家》主要刊发研究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艺术门类的理论文章,包括:文学艺术的一般理论研究,文学、戏剧、曲艺、影视、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建筑、雕塑、摄影等部门艺术理论和创作实践研究,外国文艺理论、文艺思潮、文艺流派的研究等。主要栏目:文学作品、书画鉴赏、影视评论、曲艺杂谈、语言文学、民族文化、创意设计、文艺教学、文化产业等。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0331.html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璇峰~鍐欎俊鎭紝鍑轰功/涓撳埄/鍥藉唴澶�/涓嫳鏂�/鍏ㄥ绉戞湡鍒婃帹鑽愪笌鍙戣〃鎸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