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本论文结合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在深入了解鲤声剧团的历史与现状、剧团的内部构成、演员的生活、鲤声剧团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经济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客观剖析鲤声剧团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由此揭示目前鲤
摘要:本论文结合田野调查和理论分析,在深入了解鲤声剧团的历史与现状、剧团的内部构成、演员的生活、鲤声剧团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经济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客观剖析鲤声剧团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由此揭示目前鲤声剧团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试图从鲤声剧团这个特殊的个案研究来看国家体制内戏剧剧团的生存状态与莆仙戏甚至中国戏曲的前途。
关键词:鲤声剧团;莆仙戏;传统文艺;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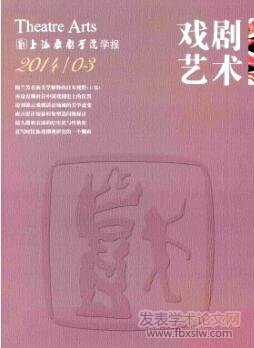
戏剧论文投稿刊物:《戏剧艺术》(双月刊)创刊于1978年,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专业理论刊物。《戏剧艺术》刊登戏剧理论和戏曲研究成果,介绍外国戏剧理论与作品,发表舞美、戏剧导演与表演艺术、戏曲教学、影视艺术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仙游鲤声剧团作为一个县级剧团,自1950年代以来,产生了两位全国知名的剧作家,培养、造就了林栋志、朱石凤、林元、傅起云、王国金、许秀莺、谢宝燊、王少媛等一大批优秀莆仙戏艺术家,为莆仙戏这个古老剧种的抢救、保护、继承、创新、发展积极努力,成绩显著。二十世纪末,剧团又有一朵梅花惊现,剧团几度进京演出,每次都引起了巨大反响。近十年间,老一代艺人退休,中年艺人力不从心,但新一代演员却极度缺乏。鲤声剧团演员的集体老化是大家公认的,没有哪个剧团的中年演员如此之多,而且在艺术方面并无任何建树,许多莆仙戏的特技已经失传。众多知名艺人同台的精彩演出正是过去鲤声剧团吸引观众的重要原因。如今鲤声剧团在当地的声望也大大降低,只能沦落如民间剧团一样,连下乡上演草台戏维持生计的机会也要同民间剧团竞争。这一从繁荣到衰落的历史过程值得我们深思。本文将在深入了解鲤声剧团的历史与现状、剧团的内部构成、演员的生活、鲤声剧团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经济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客观剖析鲤声剧团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由此揭示目前鲤声剧团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试图经过对鲤声剧团这个特殊的个案研究,来看国家体制内戏剧剧团的生存状态与莆仙戏甚至中国戏曲的前途。
一、国家体制下的鲤声剧团(1950—1985年)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文革”十年不计在内),是鲤声剧团的鼎盛时期。但鲤声剧团除了自身拥有莆仙戏丰富的遗产之外,若没有外在的国家体制、文艺政策等的推动,恐怕也是力有所不逮。
在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各地国营剧团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了政府的财政补贴。而民营剧团则受到政府限制,数量甚少,而且得不到任何补贴,在市场上显然缺乏竞争力。为国营剧团排除了竞争对象之后,国家还在国营剧团里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为每个演艺人员提供了终生保障,使得演员彻底摆脱了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这种安全感给艺术创作和演出带来了最大的动力。特别是老艺人在戏班里经历艰辛的岁月之后,如同枯木逢春,获得新生。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鲤声剧团成员的待遇较社会其他行业人员来说,是极为优越的。优秀人才愿意留在剧团里,新生力量也乐于加入。但是,艺术生命是有限的,这种做法的后遗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慢慢凸显出来。尤其是像鲤声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剧团,离退休人员大大超过能在舞台上从事演出的人员,这种现象限制了剧团的生存空间,造成剧团步履维艰。
鲤声剧团初建时并没有剧本,演出只凭老艺人记忆,大部分服装也都是租借来的。1953年春节会演,鲤声剧团通过演出《三国演义》《南唐》等历史剧和《百花亭》《千里送》等民间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展现了老艺人们精湛的演艺水平,因此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通过这次会演,群众对莆仙戏这个古老的剧种与鲤声剧团的声誉,都有了更多的认识。戏曲会演结束,鲤声剧团机缘巧合地遇上陈仁鉴蒙冤出狱。陈仁鉴为了帮鲤声起家,根据其下乡连演大棚戏《三国》配合着夜场演出的需要,赶编连台戏《三求婚》连下集剧目。剧团下乡,日场《三国》连下集,夜场《三求婚》连下集。由于《三求婚》的戏剧性很强,群众很喜欢。解放初期,群众的娱乐欲望巨大,但生活内容扁平,看戏名列娱乐头条。于是鲤声剧团在广大农村上演,村村争聘,月月排满。随着经济好转,剧团的设施逐步充实,阵营也日益扩大,需要的艺术人才也逐渐增加。紧接着,陈仁鉴又为鲤声剧团会演编写了大名鼎鼎的《团圆之后》一剧。《团圆之后》推出以后,深受福建省文艺界好评,鲤声剧团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了,一度被收为省属剧团。
从此,莆仙戏这种古老的剧种,深受文化部重视,文化专员在仙游初步收集到传统剧目三千多册,还有不少剧目流散于民间。他们了解到,名老艺人林元在筹备《琴挑》剧目出席华东戏曲会演;老艺人傅起云能绘上二百二十多个千姿百态的脸谱;名老艺人朱石凤、林栋志、陈金攀精通多种行当的表导演技能。他们在鲤声剧团欣赏了道具设计师傅琪为目连戏设计的三百多种戏剧道具;听取了名老乐师、名老鼓手郑牡丹传授的七百多个莆仙戏的丰富曲牌和变化无常的打鼓、吹鼓点。通过深入了解,深刻认识到莆仙戏这一古老剧种蕴藏着无限财富,并要求仙游在抢救古老剧目中,还要抢救老艺人的珍贵艺术财富。从此仙游鲤声剧团在全国戏剧界中树立起较高地位,赢得好口碑。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戏剧界推行“推陈出新”的文艺政策,我们可以从陈仁鉴的剧目年表中看出,他无疑也是认真贯彻这种官方主导的文化策略的。无论是为鲤声剧团奠定群众基础的《三求婚》,还是被评论界誉为“化腐朽为神奇”的典范——一悲一喜的《团圆之后》《春草闯堂》两大名作,都来源于传统戏,是对传统剧目脱胎换骨的改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使得莆仙戏的传统特色在不断的演出中得以继承,较好地保存了剧种个性。这种保存贯穿于陈仁鉴创作生命的始终,他的绝大部分剧目都来自传统戏,几十年如一日的收集整理改编,在文献方面的贡献也是难以估量的。我初步统计一下,陈仁鉴根据传统剧整理、改编、重写的剧目在72%左右,其他新创作或移植的剧目只有28%。
陈仁鉴是由政府设置的莆仙戏第一代专职编剧,此前的莆仙戏是没有专职文人参与的。所以,莆仙戏虽然源远流长,舞台表演艺术发达,剧目丰富,但戏曲文学却是薄弱环节,甚至在汗牛充栋的古本中找不到一段文学化程度较高的唱词。而在实际演出中,幕表戏的倾向也是不同程度存在的。陈仁鉴到编剧小组后,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剧作家们为了满足全县剧团的演出需要,记录、整理、改编和移植了大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使莆仙戏剧本逐步走向文学化、正规化。同时,也促使舞台演出艺术更趋严谨、规范。陈仁鉴时期是莆仙戏和鲤声剧团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剧作为传统戏剧体系的内部调整,内容始终和观众的喜好保持着天然的联系。这种密切的情感联系使得戏剧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良好的基础。
在鲤声剧团初建时期,元老级的艺人都是些比较保守的莆仙戏老艺人,他们在表演上恪守成规。因此在组建之初,鲤声剧团南戏古风长存、文化积淀丰厚,是保持传统表演艺术特色最多的典范。由于老艺人掌握着深厚的莆仙戏的传统精华,陈仁鉴又常年和演员生活在一起,深谙莆仙戏传统,他炉火纯青的编剧技艺和演员的精彩演出水乳交融,深受广大群众追捧。“文革”时期,剧团被解散。“文革”后恢复的鲤声剧团,由原来全县三个剧团合并而成,演员阵容虽不如从前,但还是比较强大,不但能演古装戏,还能演现代戏。1979年,这个新组建的鲤声剧团晋京献演《春草闯堂》,一炮打响,轰动京华。陈仁鉴时代,可以说是“天才的演员与天才的作者”强强联手的年代,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堪称完美。
陈仁鉴所做的正是推动平民戏剧发展的启蒙工作,成就巨大,功不可没。他仰赖莆仙戏这方热土而成功,而莆仙戏也因其剧作成就而彰显独特价值。毫无疑义,是陈仁鉴和上一辈的莆仙戏老艺人们的出色表现为鲤声剧团开晋京献演之先河,并奠定了莆仙戏在中国剧林之中的特殊地位,使兴化方言地区之外的观众对莆仙戏憧憬万分。陈仁鉴与莆仙戏的关系正是所谓的人因戏显、戏因人名。
1978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解放思想、发扬民主,促使有时代使命感的作家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思索转化为创作实践。郑怀兴正是这样一位剧作家。他并没有走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从历史和现实中寻找题材,创作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痛是触目惊心的。中国戏剧在遭遇一个严重的、近乎毁灭性的断层之后,中国社会盛行着极左思潮的批判,全民对此达成共识。无论是观众还是创作者被压抑的激情都猛然迸发出来。郑怀兴的剧作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中诞生的。他的成名作《新亭泪》非常具有时代气息,因此共鸣之声不绝于耳。此剧奠定了他在中国戏曲创作界中的重要地位。鲤声剧团也因为演出此剧声名再起。从此,郑怀兴源源不断的创作精神同其成名作一脉相承。其剧作还赢得官方的许多赞誉。新编历史剧《新亭泪》、现代戏《鸭子丑小传》都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1986年年底,鲤声剧团应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邀请,带着《新亭泪》《鸭子丑小传》《晋宫寒月》赴京展演。毫无疑问,演出十分成功,鲤声剧团再次载誉首都,受到北京戏剧界的极高评价。首都戏剧界还为郑怀兴召开了剧作研讨会。郑怀兴的创作硕果累累、好戏连台,受到尊崇,被称为戏曲界的“三驾马车”之一。
这个时期,人们在经历十年的“文化饥渴”之后,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报复”性的需要。人们沉醉在对旧日梨园的美好追忆中。当年名角的复出,让观众和传统戏剧重新走在一起,度过了愉快的蜜月佳期。当时仙游县城戏剧出现五多:农村剧团恢复组建多,演出古装戏剧目多,看戏观众多,基层社队办艺校多,公社大队自筹资金、投工献劳建戏院多(1978年至1981年,全县社队兴建影剧院130多座)[1]。在这样狂热的戏剧氛围下,郑怀兴的原创,确实给古老的剧种带来了勃勃生机。每当一个新戏上演之后,县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个戏,热闹极了。1987年,郑怀兴新创作的现代戏《阿桂相亲记》在城关剧场演出连满二十几场,不少农民坐着手扶拖拉机进城来看这个戏[2]。此时,鲤声剧团的艺术力量也通过以老带新传帮带和文化艺术交流、接受名家的指教等形式,在不断茁壮成长。剧团下乡,当地的乡村干部非常欢迎,热情接待,乡亲们都把演员当作贵客招待,让出最好的房子给剧团住。那时演员的待遇也还是不错的,是底薪加工分。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如前所述,是受人尊重和欢迎的,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激励。
郑怀兴的勤奋和天赋给剧团带来了荣誉和发展。但不可否认,这种生机其实隐含着危机,那些原创多少是以背离传统为代价的。无论时代怎样,戏曲作为民间的一种艺术样式,不适宜承担过多的思想性,它的重要价值以及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取向,是其独特的演出格局和丰富多彩的表演技巧。对于思想性的偏重,必然导致对戏剧本体的疏离甚至荒废。在20世纪80年代传统戏剧的短暂繁荣之后,这种对传统艺术层面缺乏关照的剧目必然与群众产生距离,转而成为调演汇报等一些主流场合的应景之作。在“文革”之后因传统戏剧开放而突然膨胀的演出市场冷清后,历史转进90年代。这时整个表演艺术的生存环境与艺术生态的陡然严峻,使得鲤声剧团的艺术阵容也因此大受影响,演出水平下降,令人寒心,郑怀兴一度写电视剧去了。
戏剧行业要想在整体上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准,除了需要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外,更需要表演者与观众之间产生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审美趣味的共鸣。力主沉浮,郑怀兴似乎也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从他的创作历程特别是近期的作品来看,似乎有从原创回归传统的迹象——包括对传统剧本的整理以及对本土题材的选择等等,他认识到莆仙戏的许多表演艺术急需抢救、继承下来,而演出传统剧目是最佳途径。例如对传统剧目《叶李娘》的改编和对《蒋世隆》裱褙式的整理。当时还是鲤声剧团成员的王少媛因成功扮演《叶李娘》中的叶李氏而摘得梅花奖桂冠。2005年,他还创作了以本土宗教三一教为题材的《林龙江》,这些都是他为保留传统和吸引本土观众所做的努力。
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鲤声剧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部一直希望能够启动剧团体制的改革,90年代中期新一轮的剧团体制改革又开始了。但是这二十多年来,国营剧团并没有摆脱对政府的习惯性依赖。9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市场的发展,莆仙两地又自发地出现了许多民营剧团。民营剧团如雨后春笋,从80年代末期的十多个猛增至如今的一百二十几个,加上季节性的班子,最多时可达一百五十几个。鲤声剧团的观众也开始大量分流。
解放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有能力组织和引导观众走进剧场,力图将剧场艺术正规化,因而各种名目的剧场繁多。仙游县城曾有一座著名剧场,鲤声剧团创作的许多新剧目,如《团圆之后》《春草闯堂》《新亭泪》《鸭子丑小传》《晋宫寒月》都是在这个剧场首演的。大约80年代末90年代初,莆仙戏开始转向农村市场,回归广场文化、农民文化,这个剧场就被县政府卖给开发商,拆掉盖起商场了。原来剧团上山下乡,许多简陋的乡村剧场里都卖票演出,后来这些乡村剧场卖的卖、拆的拆,没拆的也租出去当各种加工场了。剧团下乡,再也没有剧场可演了,只能在庙前宫边上演为菩萨看的戏了。演员的地位如此一落千丈,再也不能安心在剧团工作了。连扮演春草的主要演员都闹着改行,年轻人哪能待得住?于是,许多年轻演员纷纷通过各种关系调离了剧团,留下来的是那些走不了后门的人[3]。计划经济时期,仙游县的一个蔗糖厂名闻全国,支撑着整个县的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糖厂倒闭了,县财政也开始陷入困境,县里给剧团下拨的经费只够给老艺人发退休金。鲤声剧团曾经担当顶梁柱的演员都已年老,且身体状况不佳,后备力量一时也没能跟上,艺术力量可想而知。鲤声剧团在当地的声望遂逐渐降低,只能沦落如民间剧团一样。演员变得散漫,演出也常常是漫不经心,如此惨淡经营,演出水平自然大大下降。原先以承载传统莆仙戏而著称的鲤声剧团,甚至连行当都不能齐备了。鲤声剧团已是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鲁缟,再不能担负起原创的生产任务。
为重新振兴鲤声剧团,郑怀兴对《叶李娘》这个传统剧目的剧本做了改编。在尽量保留表演空间的基础上,于情节上做了一些改动,所增加的场次里,也尽量与原作的风格保持一致,富有表演空间。这个戏演出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成为多年以来最能体现莆仙戏表演艺术风貌的剧目之一,受到了戏剧界行家的好评,在全省二十一届戏剧调演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王少媛的表演艺术水平,使她荣获了第十七届梅花奖,成为莆仙戏获此殊荣的第一人。通过这个戏,王少媛在短短的三年中从一个三级演员变成了一级演员[4]。王少媛获得梅花奖,鲤声剧团重获一线生机,各级领导又开始重视鲤声剧团,一个排练场兼小剧场开始兴建了。
改编《叶李娘》以后,郑怀兴认识到莆仙戏的许多表演艺术急需抢救、继承下来。这光靠呼吁不行,要做实际的工作。于是,整理一些富有表演艺术的传统剧目被提上日程。莆仙戏的“瑞兰走雨”的表演很有特色,它是莆仙戏传统剧目《蒋世隆》中的一折。莆仙戏这个本子有自己的特色,民间演出本的味道很浓,整理出来除了可供日常演出外,还具有戏曲史研究的意义。郑怀兴采取类似裱褙古画的方法,力求做到修旧如旧。庆幸的是,谢宝燊先生在50年代曾从老艺人那儿记录下来《蒋世隆》的不少唱段和曲牌,成为整理的最好参照。《蒋世隆》复排时请老艺人朱石凤老师傅来执导,把传统的表演艺术一招一式都传授给了年轻演员,还采用一桌一椅的传统舞美。这个戏参加了全省二十二届调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许多专家都盛赞这一举动,观众也非常喜欢。
目前鲤声剧团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财政方面,经费严重缺乏,鲤声剧团每年除财政拨款和演出收入90万元外,应付在职和退休员工工资尚差40万元左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系列旨在限制演艺人员流动的法规,实际上取消了剧团的淘汰机制。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鲤声剧团里享受社会保障的离退休人员和正在从事创作生产的人员比例是失调的,政府的财政拨款也仅够支付离退休老艺人的工资。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改善艺术生产和演职人员的生活条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团里演员的工资只能靠下乡演出获得。这种现象限制了剧团的生存空间,使鲤声剧团步履维艰。况且在各方面的冲击下,剧团每年的演出次数大大减少,收入也大不如前了,甚至连参加比赛的经费都得向政府借助。
演出队的工资主要靠下乡演出获得,而面对市场的竞争,鲤声剧团显然很吃力。2003年演出时间为200多天,2004年只有180多天,到2005年预计只有140天左右了(这是7月时根据前半年非常糟糕的情况预计的。2005年下半年开始承包,情况有所不同)。鲤声剧团的年最高纪录达694场,滑坡趋势很明显。由于鲤声剧团地处仙游县,而大部分的演出市场在莆田。如果按照车费每人10元计算,总计700元;货运费约500元,再加上35人(男演员12人,女演员9人,后台8人,其余6人)的庞大演出队伍,这样大的开销让鲤声剧团力不从心。每逢发不出工资的日子,就必须靠仙游县财政补贴,但仙游县财政不归莆田市管,财政也非常困难,债务累累。
三、鲤声剧团和莆仙戏的未来
传统或现代的中国民间曲艺表演不但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配合着宗教节令。在这些节令中,从最早的驱邪祈福、报赛田社的祭祀及一般神祇的信仰、庙神的庆典,乃至于喜庆婚丧的仪式,戏曲曲艺表演都是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与艺术活动。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最迟到宋代,中国民间把戏曲表演与民间社火、寺院紧密结合的现象已经相当明显。显然,如果追究到戏曲的宗教源头,则二者的关系更毋庸赘言。
莆田信鬼尚祀重浮屠的宗教民俗文化绵延不绝。宋代黄岩孙《仙溪志》记云,“俗敬鬼神”,“地有佛国之号”,“婚姻不衍于礼,丧葬不俭其亲”,犹有古之遗风。这便是宋代兴化人宗教民俗文化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又是戏曲赖以生存的土壤。宋代兴化优戏便与此民俗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兴化风俗,无论家有喜事或丧事,或神佛生日,或里社节日,都必演戏。喜事如庆寿、考试、房屋落成、生意兴隆、娶妻生子等,要演戏还愿,答谢神佛。老人高寿逝世要演彩戏;非正常死亡,要演目连戏。家家有事,日日有戏,正如刘克庄《闻祥应庙优戏甚盛》诗所写的“优从祠十里鼓箫忙”。宋代兴化人信鬼神、重浮屠,祭祀还愿,锣鼓喧天,“优戏甚盛”,简直到了泛祭滥祀的程度,就连同时代的刘克庄亦为之感叹:“谁歌此诗送且迎,共挽浇风还太朴”[5]。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元明清,至今遗风犹存,莆仙戏仍然活跃在宗教民俗的活动中,莆田市目前尚有一百五十多个民间职业剧团。
戏曲与宗教民俗的结合,就其内容而言,具体表现为善恶报应的观念。莆仙戏中的好人必得到神与社会的双重护佑,坏人必受神与社会的双重惩罚,这正是早期南戏的叙事模式。这种阴阳同理的双重叙事模式在莆仙戏中表现得犹为突出,并一直延续下来。可见,民俗宗教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戏曲的叙事模式[6]。信鬼神、重浮屠的民俗宗教文化是莆仙戏产生、生存、发展、延续的文化土壤。
民间的戏曲表演常常与地方和私人的祭神活动有关,演出的地点也多在庙前。一方面寺院经常是一个聚落的中心,另一方面在此演出含有娱神的意义。即使庙前没有空地,也得在附近选择一块适当地点,使戏班遥对神祇演戏;就是私人性质的喜庆演戏,也会在空地上搭了帐篷,帐篷里的桌上端放着诸神神像,戏台就设在神像的眼前。演出时除了扮仙酬神之外,并以放鞭炮、烧纸钱来增强仪式的功能。
一般来说,专业剧团的演出可分为剧场和草台。剧场演出是指在各地戏院做卖票式的巡回演出,是属于纯艺术性的表演。1988年以前,鲤声剧团曾经在剧场里有过辉煌的时期,北到京沪杭,南到汕头。民间的草台演出,除了庙里原有的戏台之外,还在晒谷场或旧祠堂前搭建戏棚。几乎每个村都有戏台,所以少有新戏台的出现。舞台由水泥砌成,或用木头搭起。在舞台的大约三分之二处,用布景隔成两个后场。伴奏队通常在舞台的右边。草台并没有固定的化妆间。有时在小学教室,有时在祠堂里,甚至在卧室里。
地方戏经费的征集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地方上信徒按自家人数出丁(男)口(女)钱,每丁口的钱数不一,然后统筹给祭奠的炉主,由他负责聘戏来演出。这种征钱的方式,在早前十分盛行,近年来则仅为较偏僻的农村所沿用。根据笔者的调查发现,来鲤声剧团聘戏的大多是冲着“鲤声”这个金字招牌来的,虽然鲤声剧团的成员早已更新换代。鲤声剧团的戏金比较高,不是任何团体都愿意或请得起的,特别是在非年节的淡季。上述所提到的大济村,是解放以来第一次请到鲤声剧团,这对他们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一般戏班的营业情况,除了靠演技取胜外,还需要有良好的社会关系,比如和戏馆也就是中介的关系。到远地表演的机会不多,因为从远地邀请戏班来演,除了戏金增加之外,还需支付长程的车费,因此聘戏人通常就近聘戏。
民间戏曲是传统艺术形式的一种,它的表演过程不自觉但真实地展现出地方文化生活的某些基础。一方面它体现地方既存的社会结构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它也被本土社会心理情绪所认同。简而言之,地方戏曲之所以有自己的特色,是受到地方文化的支持和滋养的。
莆仙戏也不例外。莆仙戏历史悠久,因此它本身的剧种特色也是无与伦比的。当然,如果仅从演出市场来看,现今的莆仙戏也许不比史上任何时候差[7],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被称为“活化石”的只是传统的莆仙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莆仙戏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剧种特色,沦为了现代“杂剧”。
莆仙戏音乐家谢宝燊认为,其实民间剧团是有好演员的,但是民间莆仙戏走的路子有问题。民间的莆仙戏除了保留方言之外,搀杂了太多其他剧种的艺术——比如京剧、闽剧。吸收不是不好,只是它变得不纯粹了,宋元古老的艺术就渐渐丢失了。也许这正是对自身文化信仰的丧失。当一种艺术形式不再为滋养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它也正在失去自己本身。所以民间莆仙戏演剧的红火只是一种表象,它不能表示莆仙戏的真正繁荣,我们反而从这里看到了危机的明显表征。
莆仙戏和中国其他地方剧种一样,前景确实令人担忧。作为南戏的遗产,一方面,子孙在继承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人为的原因已经丢失了不少深厚传统,比如承载许多表演技艺和体现表演水平的戏剧被禁演;另一方面,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断层后,演艺水准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剧团长期处于僵化的体制之中,不仅很难吸引新生力量,更导致了人才的流失。这些都决定了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莆仙戏的艺术水平不进且退的可能。我们已经丧失了保护和抢救莆仙戏这个南戏剧种的最佳时机,只依靠政府“抢救、保护和振兴戏曲”是完全不够的。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需要保护的遗产太多了,中国经济无法承担这样大的包袱。除非像昆曲那样入选世界遗产,但申请本身也是耗财耗力的工程。
民间职业剧团的蓬勃发展似乎让莆仙戏的前景不至于那么暗淡,它用事实告诉我们,危机其实是公有制剧团的生存危机。鲤声剧团如今命悬一线,危机重重。在21世纪的今天,在调查期间,笔者依然强烈地感觉到,鲤声剧团依然还处在政府理所当然要帮其解决剧团困难的幻想中。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2085.html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