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内容提要: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黄金岁月是贬居江湘时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角色定位使他们经常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离开江湘以后,他们唱和的频率与热度稍减,却依然不时藉诗鸿寄托闻声思念之情。尽管后来穷达有别、荣枯异路,且元稹饱受非议,刘禹锡却始终
内容提要: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黄金岁月是贬居江湘时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角色定位使他们经常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离开江湘以后,他们唱和的频率与热度稍减,却依然不时藉诗鸿寄托闻声思念之情。尽管后来穷达有别、荣枯异路,且元稹饱受非议,刘禹锡却始终感念旧情,在微讽的同时不废友谊,并为其早逝一掬伤心之泪。
关键词:刘禹锡,元稹,道义相勉,气节相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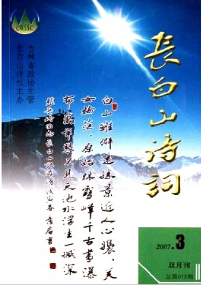
一、同居江湘:以道义相勉、气节相励的天涯沦落者
刘禹锡与元稹唱和的时间略后于白居易,大约在元和五年(810年)。当时,刘禹锡谪居朗州已阅五个春秋,而元稹刚由监察御史贬为江陵士曹参军。遭贬的原因,《旧唐书·元稹传》有载。①约略言之,此时的元稹恪尽职守,刚正不阿,敢于弹劾权贵,仵怒执政,终因与宦官刘士元的“争厅”纠纷而遭致朝廷不公正的处置,经历了仕途的又一次挫折。据《旧唐书·宪宗纪上》,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的准确时间是元和五年二月。
执政者借机发难的险恶用心以及唐宪宗袒护宦官的偏狭胸襟,使元稹在痛定思痛之际,开始体会到此前惨遭流徙的刘禹锡等“八司马”的无辜,不自觉地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视角来衡量他们曾经的作为,从而产生了与他们唱和的冲动。
于是,主动惠诗给时任朗州司马的刘禹锡。原诗已佚,刘禹锡的奉和之作则幸存,那就是《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无事寻花至仙境,等闲栽树比封君。金门通籍真多事,黄纸除书每日闻。②
“院长”是唐人对监察御史的敬称。首句巧妙化用渔人寻花误入桃花源的典故,为自己的日常生活进行写照。朗州先后有过武陵郡、常德府等历史名称。其下辖桃源县有桃花源,相传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即以此为“外景地”。诗人藉此既点明自己身居朗州,又暗示自己的贬谪生活也有其惬意之处——闲来无事时可漫游仙境、宠辱偕忘。次句转写元稹,以闲淡之笔致慰藉之情。“栽树”,用东吴李衡种橘致富、泽被后人事。
见于《三国志》卷四十八《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③意谓元稹如能效法李衡,做些“栽树”之类的营生,或许也可富甲一方,绝不逊于受封食邑的公侯。这当然略带一点调侃意味,却是本于一个善良的愿望:让元稹解颐一笑,冲淡内心忠而见逐的怨愤痛苦。
三、四两句依旧发语平淡,犹如闲话家常,但其中亦有深意。
从字面上看,这两句是说朝廷中才俊之士众多,因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有关官员任命的消息。但透过字面,寻绎它的言外之意,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其一,党争激烈,政局动荡,导致人事更迭频繁,官员走马灯似的不停转动,全然无力控制自己的政治命运和人生轨迹。其二,此时正值朝廷“多事”之秋,各种变数令人难以预测,因而行事说话都得慎之又慎。“真多事”,既渲染了诗人的惊讶,也表达了诗人的感慨。
其三,对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的讯息早有耳闻,不待对方来函相告,便已尽悉始末,因而深知其冤屈,但同为迁客,彼此心照,这些都已无须言说。这么多层深意包蕴于中,难怪清人何焯会认为刘禹锡此诗“较之乐天‘举目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蕴藉多矣。”(见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的确,较之白居易的直白,刘禹锡此诗显得格外含蓄。看似无一字讥弹朝政、也无一字慰勉元稹,但讥弹与慰勉之意却渗透在字里行间,如淡水着盐,粗看难觅,细品方知。
相形之下,白居易的这两句诗不过由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中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脱化而来,却比杜甫原句还更浅切直露,几乎流于叫嚣,因而就令人觉得余味不足了。刘禹锡在奉和元稹的第一首作品中之所以不像白居易那样直接为元稹鸣冤叫屈,也不直接对其表示同情,原因之一是,他发现此时的元稹内心虽不免“负气”,情绪总体上还算平稳,并无痛不欲生的失常表现。
其《酬乐天书怀见寄》一诗末云:“怀我浩无极,江水秋正深。清见万丈底,照我平生心。感君求友什,因报壮士吟。持谢众人口,销尽犹是金。”④《酬乐天登乐游园见忆》一诗首云:“昔君乐游园,怅望天欲曛。今我大江上,快意波翻云。秋空压澶漫,澒洞无垢氛。四顾皆豁达,我眉今日伸。”⑤
无端得咎的愤慨之情似已渐趋平复,至少在表象上是这样。自然,这样措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刘禹锡自己谪居朗州已过五年,逐渐接受了残酷命运的不公正安排,开始能相对平静地面对“逢恩不原”的现实。刚抵达朗州时,因为政治地位的落差远过于元稹,宪宗又颁下“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封杀令,他的心情也是不无激愤与抑郁的。
《武陵书怀五十韵》中的“邅回过荆楚,流落感凉温。旅望花无色,愁心醉不惛”⑥等语即为明证。不过,时间推移到元和五年后,他的心态已经基本调整到位。重回朝廷建功立业的意愿依然强烈,却很少在诗中作激情的表达,语言趋于平和与温婉。写于元和五年的《送李策秀才还湖南,因寄幕中亲故兼简衡州吕八郎中》同为五十韵的抒情长诗,却几乎不见怨愤之辞。“一聆苦辛词,再动伊郁情。
身弃言不动,爱才心尚惊”,那纯属抒写怜才之情,并非闻言兴感,自悲身世。篇末“勉君刷羽翰,蚤取凌青冥”云云,固然是送别诗的套话,情调却是开朗、俊爽的。这样,他在与元稹唱和时自也不可能出语愤激了。刘禹锡与元稹的第二首唱和诗是《赠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诗奖之》,创作时间稍后于《酬元九院长自江陵见寄》:文章似锦气如虹,宜荐华簪绿殿中。纵使凉飙生旦夕,犹堪拂拭愈头风。⑦
“文石枕”,指用当地出产的一种有纹理的玉石制作的枕头。一、二句显系以物喻人,借描绘文石枕的形貌,从才与德两方面对元稹予以高度肯定。“文章似锦”,语义双关,一石二鸟。“气如虹”,亦是双关语,但以之称美元稹固然贴切,用来形容文石枕,则稍觉牵强。这是“以物就人”,不得不然。
“宜荐”句既是交代寄枕的理由,也是继续表彰元稹。元稹曾为“头风”所苦。三四句强调文石枕在秋风乍起时可以发挥其“愈头风”的功用,当是对元稹此时的身体疾患有所耳闻。而这又见出他对友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切。元稹回赠壁州鞭并附诗予以酬谢。诗题为《刘二十八以文石枕见赠仍题绝句以将厚意因持壁州鞭酬谢兼广为四韵》:枕截文琼珠缀篇,野人酬赠壁州鞭。用长时节君须策,泥醉风云我要眠。
歌眄彩霞临药灶,执陪仙仗引炉烟。张骞却上知何日,随会归期在此年。⑧元稹把酬诗增广为七律,是因为刘禹锡已连续赠以两首七绝的缘故,非如此不足以报。在这首七律中,元稹首先赞美了文石枕和刘禹锡的赠诗。“珠缀篇”,呼应前云“文章似锦”,谓刘诗也是镶珠缀玉,美不胜收。
“用长”二句一就壁州鞭着笔,一从文石枕落墨,谓两物为各自所需,适得其所。结篇处用《博物志》所载“张骞泛槎天河故事”,暗示归途非遥,后会有期。刘禹锡遂又奉答以《酬元九侍御壁州鞭长句》。这是刘、元唱和诗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刘、元之间的唱和也于此际臻于高潮。诗云: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赠比双金。初开郢客缄封后,想见巴山冰雪深。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
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壁州”,古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通江县。“壁州鞭”,指以壁州出产的竹根制成的马鞭。“文石枕”与“壁州鞭”,一有助于安眠,一有助于健行,诚所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也。开篇处的“碧玉孤根”即具有象征意义,足以引发读者的丰富联想,想见其性之高洁、其境之幽独。
刘禹锡由元稹赠送的竹鞭联想到在“巴山冰雪”中傲然挺立、不可稍屈的制鞭之竹,通过对制鞭之竹的吟咏来显示自己宁折不弯的傲岸态度。颈联“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为一篇之警策,亦可视其为“诗眼。”这是咏竹,也是赞扬元稹的品格、写照自己的节操:性本“端直”,所以不愿卑躬屈膝;心耐“岁寒”,因而不畏风霜雨雪。
它不仅使满篇生色,而且成为千古流传的咏竹名句。尾联以策马同归朝廷相期,显示出诗人对前途即便不是充满信心,也并不灰心。“归去”,指归京、归朝而非归乡、归隐。诗人悬想两人并辔行经绿荫夹道的武关时,以“壁州鞭”敲击马镫,神情安逸,诗兴遄飞,递相赓和。他试图以这一愿景来鼓舞元稹,向其传输共同抗衡逆境、走向未来的正能量。
二、锦书遥寄:天各一方的闻声相思者
元和十年(815年)春,刘禹锡与元稹同时奉召回京,迎来命运的转机。刘、元二人的诗歌酬唱也因此进入新的阶段、抹上新的色彩。刘禹锡与柳宗元在中途会合后结伴同行,且歌且饮。元稹独自返京,行程较刘、柳为快,先期抵达蓝桥驿,题诗留予后至的刘、柳及李景俭。那便是《留呈梦得子厚致用》:泉溜才通疑夜磬,烧烟馀暖有春泥。
千层玉帐铺松盖,五出银区印虎蹄。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⑩在距离朝廷越来越近时,元稹的心情是激动的,同时也不免有点忐忑。因为朝廷将如何安置这群逐臣,对他来说是一个既想早日揭晓又怕太快揭晓的谜——天意高难问,阍者多弄权;升黜皆有可能,未必左右逢源。“暗落金乌山渐黑,深埋粉堠路浑迷”两句形象地传写出其心中的迷惘。
他将这种心情诉诸刘禹锡等人,是料定可以得到他们的共鸣。这首诗是为酬答白居易从杭州寄来的新诗而作。因为元稹出牧的越州与杭州相邻,元白又一直齐名并称,唱和频繁,所以刘禹锡将这首酬答诗也寄予元稹。这说明虽然他对有关元稹的舆论也有所耳闻,却疑信参半,他本身又笃于旧情,所以无意与元稹中断联系。
不过八年来,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唱和诗传世,又表明在舆论大哗之际,他对与元稹的交往还是审慎的。既然是“兼寄”,诗的主要笔墨还是落在白居易身上,只有颈联“鳌惊震海风雷起,蜃斗嘘天楼阁成”或许兼概元稹。
后于此诗的《浙东元相公书叹梅雨郁蒸之候因寄七言》则是单独为元稹而作的:稽山自与岐山别,何事连年鸑鷟飞。百辟商量旧相入,九天祗候老臣归。平湖晚泛窥清镜,高阁晨开扫翠微。今日看书最惆怅,为闻梅雨损朝衣。輳訛輥此诗或作于长庆四年(824年)夏。诗中看不出刘禹锡对元稹已产生某种隔阂,也看不出他受到舆论的影响已开始质疑元稹的人品。看到的只是他对元稹的牵挂以及期望。
毕竟他们分别谪居于朗州和江陵期间曾相互以道义相勉、气节相砥,那些不利于元稹的舆论在刘禹锡看来也许只是因妒生恨的流言,不可能动摇他对元稹的基本判断。诗的中间两联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颔联写朝廷百官都期待着元稹这位“旧相”“老臣”归来,刷新政治,重振朝纲。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诗人并没有对元稹失去信心,或许他把元稹为人鄙薄的一些做法视为一种不得不然的韬晦之计,一种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的可以理解的行为。同时,也是因为舆论渐渐呈现出分化的趋向,肯定元稹治国理政才干的也不乏其人。“百辟商量”“九天祗候”云云,应该并不是诗人的主观臆想,而有一定的舆情基础作为支撑。颈联描写越州景色,而就令人神往的稽山镜水着笔。
“窥清镜”“扫翠微”,不只是静态地刻划景物,更动态地展示了人物的神情举止。诗人希望元稹每当“平湖晚泛”时都能把清澈的湖水当成镜子一样自照,借以正衣冠、知是非、明得失。着一“清”字,苦心毕见。这以后,刘禹锡许久没有与元稹单独酬唱。宝历元年(825年)谪守和州时,刘禹锡与时任浙西观察使的李德裕唱和,有两首五言诗兼酬元稹,那便是《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并浙东元相公所和》及《浙西李大夫述梦四十韵并浙东元相公酬和斐然继声》。
大和三年(829年)重入庙堂后,刘禹锡与退归洛阳、处于“中隐”状态的白居易唱和,亦有两首五言诗兼酬元稹。对照他与白居易唱和之频繁,不能不说他与元稹在文字交往上多少有些疏离。反之亦如是。
三、荣枯异路:感念旧情的不忘初心者
刘禹锡再次与元稹唱和是在大和四年(830年)元稹外放为武昌军节度使时。据《旧唐书》本传,元稹担任左丞后,“振举纪纲,出郎官颇乖公议者七人。然以稹素无检操,人情不厌服。”輷訛輥可知他树敌甚多。加之牛李党争此时越演越烈,李宗闵同平章事后,与牛僧孺联手将李德裕排挤出京,而元稹因与李德裕相善,也被他们作为摧抑的对象。
《旧唐书·李宗闵传》云:“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党,皆逐之。”輮訛輦同书《李德裕传》亦云:“宗闵寻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輯訛輦这样,元稹入阁未及三月,便又出为“检校户部尚书,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军节度使”輰訛輦。元稹自长安赴武昌时途经蓝桥驿。
十五年前,他与刘禹锡、柳宗元等“江湘逐客”分别由江陵、朗州、永州等谪居地承召回京时,也曾驻足于蓝桥驿。而今,故地重临,往事历历在目,他情不自禁地想起“江湘逐客”中依然健在的刘禹锡,便赋写了《蓝桥怀旧》一诗。该诗已佚,但刘禹锡的和作尚存,那便是《微之镇武昌中路见寄蓝桥怀旧之作凄然继和兼寄安平》:今日油幢引,他年黄纸追。
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宿草恨长在,伤禽飞尚迟。武昌应已到,新柳映红旗。輱訛輦“安平”,指“八司马”中的韩泰(字安平)。因为韩泰也是十五年前投宿蓝桥的亲历者以及元稹“蓝桥题诗”的见证者,所以刘禹锡将这首和作寄给韩泰过目。首联是对元稹的慰藉之辞。
“今日油幢引”,足见如今的元稹威风八面、雄镇一方。但这实非元稹所愿,他还有更大的理想与抱负(或者说更大的野心),那就是执掌中枢、号令天下。对此,刘禹锡心知肚明,所以接云“他年黄纸追”,意谓不久之后,朝廷便又会诏令元稹回京主持政事。这显然是安慰在“蓝桥怀旧之作”中流露了失意情绪的元稹。颔联则是语重心长的微讽。
“江湘逐客”,大多命运悲惨,或病逝于贬地,如柳宗元;或蹭蹬于仕途,如刘禹锡。惟有元稹出将入相,位极人臣,而犹自因“出”与“入”的得失耿耿于怀。这让刘禹锡忍不住要议论两句。“同为三楚客,独有九霄期”,以称羡的口吻进行婉讽。为什么在众多的江湘逐客中,唯独他能够平步青云?个中缘由,刘禹锡不想揭破它,却又不能不提及它,意在促发元稹的反省与自律。
颈联喻写同侪身受重创而心怀长恨的现实际遇,委婉提醒元稹在知足的同时莫忘初衷、莫弃旧谊,对命运未能逆转的同侪援之以手。“伤禽飞尚迟”,喻指自己及韩泰因有“前科”而不得展翅高飞。这不是向元稹乞怜,而是如实描写自己与元稹的不同处境。其中或许也有希望汲引之意,但更多的还是提醒元稹:较之或长逝或沉沦的同侪,你应当知足常乐,不要总是心存得陇望蜀之想。这仍然是一种讽喻。
尾联悬想元稹应已抵达武昌军营,“新柳”与“红旗”相映,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景象。这里,诗人暗用陶侃“武昌柳”故事,期望元稹能像陶侃一样明察秋毫、整肃军纪。综观全诗,刘禹锡对元稹“节行有亏”的人格瑕疵并非无所察觉。以他的政治智慧和生活阅历,应该早就发现了元稹行为中的不检点之处。只不过有可能他觉得元稹寻求宦官的庇护或许也有其无奈,充其量只是为了自保,尚未堕落到与宦官沆瀣一气、陷害忠良的地步。
因此可以说其政治品格不够坚定,却很难说其政治道德已彻底败坏。何况谪居沅湘之滨时,他曾与同样流徙在穷乡僻壤的元稹一再赠诗互勉。可以说,在他最艰难的时期,元稹给予了他最温暖的慰藉。他无论如何不愿相信一个曾经不顾安危、犯颜直谏的热血斗士会堕落为见利忘义、出卖同道的冷血政客。正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改变对元稹的态度,愿意在“天下汹汹”之际继续维持既往的友谊。然而,元稹并没有能长享富贵,不久便病卒于武昌。据《旧唐书·元稹传》载,“(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于镇,时年五十三。”
輲訛輦当不满其晚年为人的朝官纷纷额手称庆时,刘禹锡却真诚地一掬伤悼之泪。噩耗传来之际,刘禹锡是否像白居易那样当即赋诗哀悼,因无作品留存不得而知,但在元稹病逝后的几年间,他多次写诗缅怀却是确凿的事实。他们曾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虽处逆境、初衷未改的政治上的知己,尽管不属于同一政治派别,却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诉求,至少在抑制藩镇、排斥宦官等环节上他们的政治主张毫无二致,又都表现出不屈服于强权的铮铮铁骨。这是他们惺惺相惜并在迁谪沦落的日子里互致拳拳的基础,也是他们的唱和诗甫一发足便步入黄金期的原因。
但随着元稹政治命运的逆转,两人的身份出现了不对称、不平衡,唱和诗的基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相互鞭策、相互慰勉,而只是泛言相思了。以相思之情为主旋律,或许是因为他们既希望维系患难时建立的友谊,又很难找到别的能引发共鸣的合适话题。所以,虽然从字面上看,两人并没有因各自地位的升沉而关系疏远,但情感的浓度与烈度却有所下降,这是无须遮掩的事实。
其实,如果刘禹锡也愿意像元稹那样改变既定的政治立场,依附宦官以求进取,也未尝不能谋得境遇的改善。事实上,他的岳父薛謇与宦官头目薛盈珍关系密切,倘若他有心卖身投靠,或亦可官运亨通,至少能早日脱离“谪籍”。但他却不愿曲径通幽,因为那意味着改变初衷、放弃自己的政治操守。
惟其如此,他对时人所讪谤的元稹的“变节”行为肯定深有所憾,但笃于友谊的他,在友谊本身尚未受到亵渎、且舆论虚实不明的情况下,不可能与元稹中断诗鸿往还,但主题转移以及频率减低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待得进入唱和的第三阶段,元稹为人为事的瑕疵已经无法遮掩,而其仕途益加显达,呈现出与当年同贬江湘者迥然有别的人生轨迹。此时的刘禹锡虽无意效割席之举,却难捺内心的不忿,终于在唱和诗中对其婉言寄讽了。
但依然心存希冀——或许对方能幡然醒悟,改弦易辙。因此,诗中仍不失温情而非冷若冰霜,见出诗人在持守节操的同时恪尽交友之道。当元稹暴卒后,刘禹锡则以更包容的态度,谅解了他曾经的迷失与过错,一再感念旧谊而发为歌吟。梳理与辨析这一由密转疏、由热趋冷、曲尽其致的唱和历程,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特殊视角透见刘禹锡曲折有致的创作轨迹,而且可以看到在中唐纷纭复杂的时势下士人各不相肖的政治态度选择及与此相关联的诗歌风貌演变。
文学方向评职知识:《长白山诗词》(双月刊)是由长白山诗社主办的诗歌类期刊。主要栏目:时代风采、田园区、诗林逸兴、寄赠唱和、咏物寄意、感事抒怀、人生百态、旨归真情、屐痕处处、散题杂咏。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0429.html

2023-2024JCR闂佽崵鍠愮划宥咁熆濡櫣鏆︽い鎺戝缁犲綊鏌i幋锝嗩棄闁绘劕锕弻锝呂熼崹顔炬闂佽鏋婚幏锟�

SCI 闂備浇宕垫慨鎶芥嚄閸洖纾块柕鍫濐槸閸戠娀鏌涢幇闈涙灍闁绘帟顕ч…璺ㄦ崉閻氭潙浼愰梺璇茬箣缁舵岸寮婚弴銏犲耿闁哄洨濮存俊鑺ョ節濞堝灝鏋涙繛灞傚妿閸掓帒鈻庨幋鐐叉櫝闂侀潧鐗嗛崐鍛婄閹灐褰掓晲婢跺鏆犻梺鍛婄懃缁绘﹢寮诲☉銏犖ㄧ憸宥嗙濠婂牊鐓曟繛鍡楃箳缁犵粯顨ラ悙鏉戝鐎规洘鍎奸ˇ鑼棯椤撴稑浜�

SSCI缂傚倸鍊风拋鏌ュ磻閹剧粯鐓曟繛鍡楃Т閸斻倗绱掗幇顓ф畼缂佽鲸甯楀鍕偓锝庝簽娴犳潙顪冮妶鍡楃闁哥姵鐗曢锝夋偨閸涘﹤浜滈悗鐟板婢瑰棙绂嶉弽顓熲拺缁绢厼鎳庨悡鎰箾閸欏鐭嬮柣蹇旂懇閺岋綁鎮╁▎蹇撴殭妞ゅ浚鍓氶妵鍕籍閹炬潙顏�

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ㄥ┑鍌涙綄閸ャ劎绡€婵﹩鍓氶ˉ婵嬫⒑閹肩偛鍔橀柛鏂垮缁旂喓鈧綆鍠氶崣鎾绘煕閵夋垵鍟▓鎻掆攽閻橆偄浜鹃梺璺ㄥ枔婵绮堥崱妞绘斀闁绘ǹ绮鹃崗宀勬煟椤撶喓鎳呯紒杈ㄦ尰閹峰懘宕妷鎰剁磿缁辨帒螖閳ь剟鎯岄崒鐐靛祦閹兼番鍔岄崡鎶芥煟濡缚瀚扮紓宥咃躬閻涱噣骞囬弶璺ㄥ€為悷婊冪Ф濞戠敻鍩€閿燂拷

sci闂傚倷绀侀幉锛勫垝瀹€鍕垫晩闁瑰墎妫梚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偡閵夆晛瀚夋い鎺戝閺嬩胶鐥鐐村櫡濞存粌缍婇弻锟犲炊閳轰焦鐎鹃梺绯曟櫅閸婂潡寮诲☉銏犵闁绘劖娼欓锟�

EI闂傚倷娴囬妴鈧柛瀣崌閹銈﹂幐搴哗缂備礁顦ḿ锟犲蓟閿濆惟闁靛鍎烘禒褰掓⒑閻撳海浠涢柛銊ョ仢閻g兘宕奸弴鐔锋疅闂侀潧顧€缁犳垿鎮為幖浣光拺闁告稑锕ら柌婊堟煙閸戙倖瀚�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嚌閸撗€鍋撳鐓庡⒋妞ゃ垺顨婇幃銏ゆ惞閸︻厾鍘犻梻浣筋潐瑜板啫顬婄猾顪�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嚌閸撗€鍋撳鐓庡⒋妞ゃ垺顨婇幃銏ゆ惞閸︻厾鍘犻梻浣筋潐瑜板啫螣閸э拷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嚌閸撗€鍋撳鐓庡⒋妞ゃ垺顨婇幃銏ゆ惞閸︻厾鍘犻梻浣侯攰娴滎剟鎮ч悮姝�

EI闂傚倷绀侀幖顐︽偋韫囨稑绐楅幖娣妼閸ㄥ倿鏌熺捄銊ュ帯XSourceList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晪濠碘槅鍋呴〃濠囧箚閸モ晝绀婄紒璺虹獜ci闂傚倷绀侀幖顐ょ矓閼哥數浠氱紓鍌欑劍濡炵晫绮婚弽褜鍤曢柣銏犳啞閸嬪嫮鈧懓瀚竟鍡樼閺嵮€鏀芥い鏃傚亾閸も偓濠电偠顕滅粻鎾诲春閳ь剚銇勯幒鎴敾閻庢熬鎷�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晪濠碘槅鍋呴〃濠囧箚閸モ晝绀婄紒璺虹┋d-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ㄩ柣鎾崇瘍閻熸嫈鏃堝礃椤忓棛鍘犻梻浣烘嚀閻°劎鎹㈠澶婄闁告侗鍨崑鎾斥枔閸喗鐏嶅┑鐐插级閿曘垹顕i幖浣哥妞ゆ柨鍚嬮悗顒勬⒑缂佹﹩娈旈柣妤€妫涚划濠囨晝閸屾氨顔愰柣搴㈢⊕钃遍悘蹇曞缁绘稒绺介崨濠冮敪闂佸磭鎳撻崯鎾嵁閸ヮ剦鏁囬柣鏃堫棑閸旑垶姊绘担鍛婂暈閻㈩垼浜獮蹇涙晸閿燂拷

CSCD闂傚倷鐒︾€笛囧礃婵犳艾绠柨鐕傛嫹2023-2024闂傚倷鐒︾€笛囧礃婵犳艾绠柨鐕傛嫹

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ㄥΔ锝呭枦缂嶆牠鏌″搴″箺闁抽攱妫冮弻鏇$疀閺囩倫銏ゆ煟鎼粹槅鐓奸柡灞剧洴瀵粙顢橀悩鐢电崶闂備線娼уΛ鎾箯閿燂拷2023

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ㄩ柣鎾崇瘍閻熸嫈鏃堝礃椤忓棛鍘犻梻浣烘嚀椤曨參宕戝☉婊呬海闂傚倷绀侀幖顐ょ矓閼哥數浠氱紓鍌欑劍濡炵晫绮婚弽褜鍤曢柣銏犳啞閸嬪嫮鈧懓瀚竟鍡樼閺嶎厽鈷戦柛娑樷姇椤忓嫀娑樜旈崨顔煎壋婵°倧绲介崯顖炲磿鎼粹偓浜滈柡鍐ㄦ搐娴滃湱绱掓径娑欏

2023濠德板€楁慨鐑藉磻濞戙埄鏁嬫い鎾跺枑濞呯姵淇婇妶鍕厡闁崇粯姊归妵鍕箻鐠鸿桨娌紓浣稿€稿ú銊ф閹烘挸绶為悗锝庝簽娴犲憡绻濈喊妯侯潚闁搞儜鍐ㄦ暏缂傚倷绀侀鍫濃枖閺囩喍绻嗛柛銉墯閻撴盯鏌涢鐘茬仼闁哄閰i弻娑㈠Ω閿旂瓔妫冮梺璇″灠鐎氫即銆佸▎鎾村殐闁冲搫鍞銏♀拺闁圭ǹ娴烽埥澶愭煟濡や礁濮嶇€规洟娼чオ浼村醇閻斿皝鍋撻崸妤佺厱闁规崘灏欑拹鐗堢箾閼测晛鈻堥柟顔筋殔閳藉鈧湱濯崥鍛磽娴g懓鏁鹃柟鍑ゆ嫹

2023濠德板€楁慨鐑藉磻濞戙埄鏁嬫い鎾跺枑濞呯姵淇婇妶鍕厡闁崇粯姊归妵鍕箻鐠鸿桨娌紓浣稿€稿ú銊ф閹烘挸绶為悗锝庝簽娴犲憡绻濈喊妯侯潚闁搞儜鍐ㄦ暏缂傚倷绀侀鍫濃枖閺囩喍绻嗛柛銉墯閻撴盯鏌涢鐘茬仼闁哄閰i弻娑㈠Ω閿旂瓔妫冮梺璇″灠鐎氫即銆佸▎鎾村殐闁冲搫鍞銏♀拺闁圭ǹ娴烽埥澶愭煟濡も偓缁绘ɑ淇婇悽鍛婂€烽柡澶嬪焾閸ゃ倕鈹戦鏂よ€跨痪顓犌瑰玻鍧楁偐缂佹ê鈧灚绻涢幋婵堟瀮妞ゆ捁娅g槐鎺楀箟鐎n偄顏�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晪濠碘槅鍋呴〃濠囧箚閸ャ劊鍋呴柛鎰╁妿椤﹀崬鈹戞幊閸婃劙宕戦幘缁樼厪闁搞儜鍕灎閻庢鍠氶弲顐ゅ垝濞嗘垶宕夐柕濞垮労濞诧拷

2023闂傚倷鑳剁划顖炪€冮崨瀛樺亱闊洦渚楅弫鍕煕閵夘喖澧痪顓涘亾濠电偠鎻徊浠嬪箹椤愶负鈧倿鎮℃惔妯活潔闂佺懓鐏濋崯顐︾嵁濡ゅ懏鐓涢悗锝庝簻閺嗭絿鈧鍠氶弲顐ゅ垝濞嗘垶宕夐柕濞垮労濞差參姊绘担鍝勫姦闁哄應鏅犲畷浼村冀椤愩倗顦梺璺ㄥ櫐閹凤拷

2023-2024JCR闂佽崵鍠愮划宥咁熆濡櫣鏆︽い鎺戝缁犲綊鏌i幋锝嗩棄闁绘劕锕弻锝呂熼崹顔炬闂佽鏋婚幏锟�

SCI 闂備浇宕垫慨鎶芥嚄閸洖纾块柕鍫濐槸閸戠娀鏌涢幇闈涙灍闁绘帟顕ч…璺ㄦ崉閻氭潙浼愰梺璇茬箣缁舵岸寮婚弴銏犲耿闁哄洨濮存俊鑺ョ節濞堝灝鏋涙繛灞傚妿閸掓帒鈻庨幋鐐叉櫝闂侀潧鐗嗛崐鍛婄閹灐褰掓晲婢跺鏆犻梺鍛婄懃缁绘﹢寮诲☉銏犖ㄧ憸宥嗙濠婂牊鐓曟繛鍡楃箳缁犵粯顨ラ悙鏉戝鐎规洘鍎奸ˇ鑼棯椤撴稑浜�

SSCI缂傚倸鍊风拋鏌ュ磻閹剧粯鐓曟繛鍡楃Т閸斻倗绱掗幇顓ф畼缂佽鲸甯楀鍕偓锝庝簽娴犳潙顪冮妶鍡楃闁哥姵鐗曢锝夋偨閸涘﹤浜滈悗鐟板婢瑰棙绂嶉弽顓熲拺缁绢厼鎳庨悡鎰箾閸欏鐭嬮柣蹇旂懇閺岋綁鎮╁▎蹇撴殭妞ゅ浚鍓氶妵鍕籍閹炬潙顏�

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ㄥ┑鍌涙綄閸ャ劎绡€婵﹩鍓氶ˉ婵嬫⒑閹肩偛鍔橀柛鏂垮缁旂喓鈧綆鍠氶崣鎾绘煕閵夋垵鍟▓鎻掆攽閻橆偄浜鹃梺璺ㄥ枔婵绮堥崱妞绘斀闁绘ǹ绮鹃崗宀勬煟椤撶喓鎳呯紒杈ㄦ尰閹峰懘宕妷鎰剁磿缁辨帒螖閳ь剟鎯岄崒鐐靛祦閹兼番鍔岄崡鎶芥煟濡缚瀚扮紓宥咃躬閻涱噣骞囬弶璺ㄥ€為悷婊冪Ф濞戠敻鍩€閿燂拷

sci闂傚倷绀侀幉锛勫垝瀹€鍕垫晩闁瑰墎妫梚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偡閵夆晛瀚夋い鎺戝閺嬩胶鐥鐐村櫡濞存粌缍婇弻锟犲炊閳轰焦鐎鹃梺绯曟櫅閸婂潡寮诲☉銏犵闁绘劖娼欓锟�

EI闂傚倷娴囬妴鈧柛瀣崌閹銈﹂幐搴哗缂備礁顦ḿ锟犲蓟閿濆惟闁靛鍎烘禒褰掓⒑閻撳海浠涢柛銊ョ仢閻g兘宕奸弴鐔锋疅闂侀潧顧€缁犳垿鎮為幖浣光拺闁告稑锕ら柌婊堟煙閸戙倖瀚�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嚌閸撗€鍋撳鐓庡⒋妞ゃ垺顨婇幃銏ゆ惞閸︻厾鍘犻梻浣筋潐瑜板啫顬婄猾顪�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嚌閸撗€鍋撳鐓庡⒋妞ゃ垺顨婇幃銏ゆ惞閸︻厾鍘犻梻浣筋潐瑜板啫螣閸э拷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嚌閸撗€鍋撳鐓庡⒋妞ゃ垺顨婇幃銏ゆ惞閸︻厾鍘犻梻浣侯攰娴滎剟鎮ч悮姝�

EI闂傚倷绀侀幖顐︽偋韫囨稑绐楅幖娣妼閸ㄥ倿鏌熺捄銊ュ帯XSourceList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晪濠碘槅鍋呴〃濠囧箚閸モ晝绀婄紒璺虹獜ci闂傚倷绀侀幖顐ょ矓閼哥數浠氱紓鍌欑劍濡炵晫绮婚弽褜鍤曢柣銏犳啞閸嬪嫮鈧懓瀚竟鍡樼閺嵮€鏀芥い鏃傚亾閸も偓濠电偠顕滅粻鎾诲春閳ь剚銇勯幒鎴敾閻庢熬鎷�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晪濠碘槅鍋呴〃濠囧箚閸モ晝绀婄紒璺虹┋d-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ㄩ柣鎾崇瘍閻熸嫈鏃堝礃椤忓棛鍘犻梻浣烘嚀閻°劎鎹㈠澶婄闁告侗鍨崑鎾斥枔閸喗鐏嶅┑鐐插级閿曘垹顕i幖浣哥妞ゆ柨鍚嬮悗顒勬⒑缂佹﹩娈旈柣妤€妫涚划濠囨晝閸屾氨顔愰柣搴㈢⊕钃遍悘蹇曞缁绘稒绺介崨濠冮敪闂佸磭鎳撻崯鎾嵁閸ヮ剦鏁囬柣鏃堫棑閸旑垶姊绘担鍛婂暈閻㈩垼浜獮蹇涙晸閿燂拷

CSCD闂傚倷鐒︾€笛囧礃婵犳艾绠柨鐕傛嫹2023-2024闂傚倷鐒︾€笛囧礃婵犳艾绠柨鐕傛嫹

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ㄥΔ锝呭枦缂嶆牠鏌″搴″箺闁抽攱妫冮弻鏇$疀閺囩倫銏ゆ煟鎼粹槅鐓奸柡灞剧洴瀵粙顢橀悩鐢电崶闂備線娼уΛ鎾箯閿燂拷2023

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鍌ㄩ柣鎾崇瘍閻熸嫈鏃堝礃椤忓棛鍘犻梻浣烘嚀椤曨參宕戝☉婊呬海闂傚倷绀侀幖顐ょ矓閼哥數浠氱紓鍌欑劍濡炵晫绮婚弽褜鍤曢柣銏犳啞閸嬪嫮鈧懓瀚竟鍡樼閺嶎厽鈷戦柛娑樷姇椤忓嫀娑樜旈崨顔煎壋婵°倧绲介崯顖炲磿鎼粹偓浜滈柡鍐ㄦ搐娴滃湱绱掓径娑欏

2023濠德板€楁慨鐑藉磻濞戙埄鏁嬫い鎾跺枑濞呯姵淇婇妶鍕厡闁崇粯姊归妵鍕箻鐠鸿桨娌紓浣稿€稿ú銊ф閹烘挸绶為悗锝庝簽娴犲憡绻濈喊妯侯潚闁搞儜鍐ㄦ暏缂傚倷绀侀鍫濃枖閺囩喍绻嗛柛銉墯閻撴盯鏌涢鐘茬仼闁哄閰i弻娑㈠Ω閿旂瓔妫冮梺璇″灠鐎氫即銆佸▎鎾村殐闁冲搫鍞銏♀拺闁圭ǹ娴烽埥澶愭煟濡や礁濮嶇€规洟娼чオ浼村醇閻斿皝鍋撻崸妤佺厱闁规崘灏欑拹鐗堢箾閼测晛鈻堥柟顔筋殔閳藉鈧湱濯崥鍛磽娴g懓鏁鹃柟鍑ゆ嫹

2023濠德板€楁慨鐑藉磻濞戙埄鏁嬫い鎾跺枑濞呯姵淇婇妶鍕厡闁崇粯姊归妵鍕箻鐠鸿桨娌紓浣稿€稿ú銊ф閹烘挸绶為悗锝庝簽娴犲憡绻濈喊妯侯潚闁搞儜鍐ㄦ暏缂傚倷绀侀鍫濃枖閺囩喍绻嗛柛銉墯閻撴盯鏌涢鐘茬仼闁哄閰i弻娑㈠Ω閿旂瓔妫冮梺璇″灠鐎氫即銆佸▎鎾村殐闁冲搫鍞銏♀拺闁圭ǹ娴烽埥澶愭煟濡も偓缁绘ɑ淇婇悽鍛婂€烽柡澶嬪焾閸ゃ倕鈹戦鏂よ€跨痪顓犌瑰玻鍧楁偐缂佹ê鈧灚绻涢幋婵堟瀮妞ゆ捁娅g槐鎺楀箟鐎n偄顏�

闂傚倷绀侀幉锟犳晪濠碘槅鍋呴〃濠囧箚閸ャ劊鍋呴柛鎰╁妿椤﹀崬鈹戞幊閸婃劙宕戦幘缁樼厪闁搞儜鍕灎閻庢鍠氶弲顐ゅ垝濞嗘垶宕夐柕濞垮労濞诧拷

2023闂傚倷鑳剁划顖炪€冮崨瀛樺亱闊洦渚楅弫鍕煕閵夘喖澧痪顓涘亾濠电偠鎻徊浠嬪箹椤愶负鈧倿鎮℃惔妯活潔闂佺懓鐏濋崯顐︾嵁濡ゅ懏鐓涢悗锝庝簻閺嗭絿鈧鍠氶弲顐ゅ垝濞嗘垶宕夐柕濞垮労濞差參姊绘担鍝勫姦闁哄應鏅犲畷浼村冀椤愩倗顦梺璺ㄥ櫐閹凤拷
闂備浇宕垫慨鏉懨洪妶澶婂簥闁哄被鍎查弲鏌ユ煟閹邦剚鎯堢紒鈧崘鈺冪闁糕剝顨堥崙鍦磼鐠囧弶顥㈤柡宀€鍠栭、妯款槻闁诲繗灏欑槐鎺撴綇閵娧呯杽閻庤娲橀悷锕€岣块鍫濈骇闁割煈鍣ḿ锟�/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箰婵犳艾绠伴柟闂寸閺勩儵鏌ㄩ悤鍌涘/闂傚倷鐒﹂幃鍫曞磿閺夋嚦娑㈠礋椤栨俺鍩為柣搴㈢⊕閿氱紒鍓佸仱閺屻劑鎮ら崒娑橆伓/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鐭楅柍褜鍓熼幃妤€顫濋鐐╂灆閻庢鍣崜鐔煎极閹剧粯鏅搁柨鐕傛嫹/闂傚倷鑳舵灙缂佽鐗撳畷婵嗙暆閸曞灚鏅㈤梺缁樻濞咃綁鎯岄幘缁樼厵閻庣數枪娴狅箓鏌涢埡浣糕偓鍧楀蓟濞戙垹绠抽柟鎼灡閺侀箖鏌i姀鈺佺仩缂傚秴锕獮濠囨晸閻樿尙鐤€濡炪倕绻愬Λ娑㈠箟閸ф鈷戦柛娑橈功閹冲嫰鏌涢妸銉e仮濠碘剝鎸冲畷姗€顢欓懖鈺婂敹闂備焦鎮堕崕婊呬沪閼恒儺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