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留言稍后联系!

本文摘要:[摘要]藏传佛教演变为卫拉特人集体信仰时,古老的萨满信仰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通过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适度融合,仍旧保留有一些萨满文化要素。这一融合过程不单在仪式、仪轨等领域相互吸收各自信仰文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基于蒙古人文化
[摘要]藏传佛教演变为卫拉特人集体信仰时,古老的萨满信仰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通过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适度融合,仍旧保留有一些萨满文化要素。这一融合过程不单在仪式、仪轨等领域相互吸收各自信仰文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基于蒙古人文化心理特征,以蒙古人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并建构本民族的佛教文化,以期创建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蒙古宗教”。
尽管传播并发展“蒙古宗教”确实也遇到过一些藏族僧人的非议,加之清朝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对“蒙古宗教”的产生构成无形的阻力,这一点可以从顺治朝两位蒙藏高僧之间的冲突中管窥一二。不过,我们抛开清朝的国家政策因素不说,就单论内齐托音一世、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两位卫拉特高僧为蒙古族佛教文化的成长与繁荣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去称颂的。
[关键词]藏传佛教,卫拉特,本土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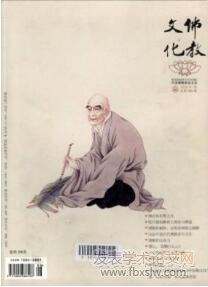
研究者们对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时间,一直持有不同的观点,然16世纪末17世纪初宗喀巴之教①传入蒙古诸游牧部落②,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强力传播和普及以后,最终演变成蒙古人普遍尊崇的藏传佛教教派,且为适应蒙古游牧社会环境而巧
妙的与传统的萨满教(B?γem?rγ?l)教理融合,继而形成藏传佛教文化圈中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蒙古佛教文化。
1247年,元太宗窝阔台次子西凉王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高僧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凉州会面,研究者们习惯称其为“凉州会盟”[1]抑或“凉州会谈”[2],等等。尽管很难确定该事件即为蒙古人接触西藏佛教僧侣抑或藏传佛教的最初事件,但是,该事件已然成为蒙古贵族们了解藏传佛教,甚至逐步对其生起无上信仰的标志性事件。由此,源自雪域的藏传佛教与蒙古汗国和元王朝国祚相伴始终,也成为16世纪末期蒙古诸部上层逐步皈依格鲁派并利用格鲁派希冀创建“政教二道”行国政权时的宝贵历史记忆与政治资本。
一、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布进程
关于卫拉特蒙古人皈依藏传佛教的时间问题,研究者们一直莫衷一是。但作为蒙古族的重要支系部落,于蒙古汗国创立伊始,卫拉特的贵族们就已享有“亲视诸王”[3]的皇亲礼遇,与黄金家族建立起牢固的世袭姻亲关系,故有元一代卫拉特部政
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中的传布及其“本土化”演变治地位是相当高的。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落之前,包括卫拉特部在内的诸森林、游牧部落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一直以萨满教为主,但统一以后的蒙古人在其拓展疆域的进程中,对被征服民族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一般采取比较温和的包容态度。如忽必烈继任汗位之前的历代蒙古大汗对汉传佛教也产生过浓厚的兴趣,甚至在忽必烈的漠南幕府中还有为其经略汉地而充当谋士的海云、刘秉忠等汉地禅宗佛僧。
由此可见,在来自西藏的高僧大德们得到蒙古贵族们信任并蒙信藏传佛教之前,汉传佛教(至少是汉地佛僧)同样受到过蒙古贵族们的尊崇(亦包括深受中亚、汉藏佛教濡染的西夏及回鹘佛僧)。据1953年发现于蒙古国的蒙汉双体《释迦院碑记》(亦称《蒙哥汗纪念碑》)的汉文铭文记载,在蒙哥执政时期,曾有“外剌(即“卫拉特”的汉文译写之一)[4]随营居奉佛驸马八立托(依据蒙古文碑铭转写为“Baratüke)、公主一悉基”参见蒙古国学者敖·那木南道尔吉著,胡斯振、恩和巴图译著:《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亦有学者将驸马“八立托”拉丁转写成“Barst?γe”;将公主“一悉基”写成“一悉眚”,参见王大方、张文芳编著:《草原金石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
为感念蒙哥汗恩典而专门建寺立碑,以表“国泰民安,法轮常转”参见蒙古国学者敖·那木南道尔吉著,胡斯振、恩和巴图译著:《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可见这位卫拉特出身的驸马及其夫人均为佛教徒,且是汉传佛教的信徒。亦有学者认为,贵由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0γulqaimi?)既是卫拉特人,也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参见李泰玉编:《新疆宗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杨富学著:《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395页。
又据瑞典史学家多桑认为斡兀立·海迷失为卫拉特人,而伯希和认为是蔑儿乞人,参见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项英杰校:《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48页。,加之以蒙哥汗在位时宠幸汉地佛僧,且主持过著名的“佛道辩论”蒙哥汗执政时期著名的“佛道辩论”中不仅有汉地禅宗长老们参与过与道教的辩论,其他诸如被称作“西番(吐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畏兀儿僧)”等佛教僧侣亦参与过佛教一方的辩论。
详见元朝释祥迈撰:《辨伪录》卷3,收录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册第2116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71页。事件来看,彼时的卫拉特贵族们受汗室影响,或许同样是尊崇佛教的。不仅如此,其尊崇的佛教也比较多元化,因为蒙哥汗不单尊崇汉僧,像克什米尔、吐蕃、西夏及回鹘佛僧也深受大汗赏识。尽管很难获知到底有多少卫拉特人虔心皈依过佛教,不过作为黄金家族“亲视诸王”的卫拉特贵族们与同一时期的黄金家族的旨趣应该是相同的。而且历史迹象也表明,佛教只是在包括卫拉特贵族在内的小部分蒙元上层中被认知及赏识,对底层的蒙古普通百姓而言,佛教依旧是非常陌生的事物,相反本土宗教萨满教仍旧在蒙古民众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13世纪初,蒙古人从信奉藏传佛教的西夏人和回鹘人那里初步了解过藏传佛教,这种最初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应是由征讨与吐蕃相邻的回鹘及西夏时开始的,而在回鹘和西夏人那里,不仅盛行汉传佛教,源自吐蕃的藏传佛教也十分昌盛。13世纪30年代,皇子阔端坐镇西夏故地河西时,为包抄和经略南宋西部土地而与当时的西藏有过第一次不愉快的接触。
其麾下将领朵尔达(Durda)率蒙古军试探性地进军至拉萨北部的热振寺一带,震慑了吐蕃政权崩塌以后形成的各地方割据政权以及后弘期出现的藏传佛教诸教派。朵尔达用兵吐蕃,对当地僧俗界震动很大,而彼时的吐蕃已无昔日强大的军事实力,无法与蒙古军正面对抗,不仅如此,后弘期形成的藏传佛教诸教派在吐蕃群众中已扎下深厚的基础,继而在虔诚的宗教信仰基础上与松散的吐蕃各地方割据政权建立起良好的依存或同盟关系。
可以说,彼时的吐蕃各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诸教派内部均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因此僧俗双方合作搭建起稳固的依存关系才能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诸教派而言,依附某强大的世俗政治集团,对巩固和拓展教派的生存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正源于此,阔端王的先遣部队探明到吐蕃局势以后,为更好地经略藏地,也不得不与这些教派取得联系,继而为其长远的政治战略服务。1247年,西凉王阔端与萨迦派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在凉州商谈吐蕃的归附问题,不久后阔端与萨班达成协议,成为较早皈依抑或扶持西藏某一教派的蒙古汗室成员。
但是,最初的蒙古汗室成员对藏传佛教诸教派却没有特别的定见,除了萨迦派,彼时的诸如噶玛噶举、蔡巴噶举等教派同样在蒙古地区传法,也纷纷得到过汗室成员及贵族们的扶持。由于忽必烈在继承汗位之前就与萨班之侄萨迦五祖八思巴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并接受其灌顶而皈依萨迦派,继位以后又授予八思巴以国师、帝师称号及统领元朝释教之职,由此萨迦派遂成为元朝皇室及贵族们极力崇信的藏传佛教教派,其影响力盖过其境内一切宗教派别。
随着黄金家族崇信萨迦派,并对萨迦派僧人委以重任,作为“亲视诸王”的卫拉特贵族们也自然而然的对萨迦派僧侣敬重有加,但元代史书却极少提及卫拉特贵族们是如何敬奉萨迦派喇嘛的历史记载。直至元亡明兴,蒙古人败退至蒙古草原以后,明代汉文文献始出现卫拉特贵族与藏传佛教产生联系的相关记载。
元末,曾经主政西藏的萨迦地方政权已完全被新兴的帕竹噶举地方政权取代,后又得到明廷的承认和支持。尽管撤回至草原的蒙古贵族们与雪域高原断绝了政治及宗教上的联系,但对希冀重新统一蒙古各部的统治阶层而言,利用藏传佛教或者抬高僧人地位,或许可以在分裂割据状态下的蒙古草原重塑个人声望。
可以说,元朝历代皇帝尊崇西藏僧人的历史,对后世蒙古贵族们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故藏传佛教在撤回至草原的蒙古贵族内部依旧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15世纪初,卫拉特部以强大的政治集团的形象逐渐在内陆亚洲舞台上展露锋芒,并在之后的若干世纪里与周边其他蒙古部落及民族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卫拉特部与东蒙古(即漠南和漠北蒙古,明代汉文史籍合称为“鞑靼”,蒙古文拉丁转写为“Tatar”)的长期竞争中,不仅探索出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又受制于蒙古人正统观念的影响,其在脱欢、也先治理东西蒙古时期就非常重视藏传佛教僧侣的地位及作用,且常以喇嘛作为使者,向明朝通好。如史载,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十二月甲子,明廷“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剌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剌失力僧衣一袭……”[5]卷37,713再如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瓦剌太师也先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剌麻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璎珞海螺呪施法食诸品物……”[5]卷137,2722。
景泰三年(1452年)十一月,又为其“国师三荅失里、番僧撒灰帖木儿等”[5]卷223,4819—4820喇嘛请赐佛教用品。但由于戒备也先的缘故,明廷回绝了也先的多次请求。这些史料说明,元亡以后的蒙古人还未彻底与藏传佛教失去联系,至少在卫拉特脱欢和也先统治东西蒙古时期还可以通过信仰佛教的吐鲁番畏兀儿人以及毗连安多地区的明朝关西七卫(蒙古七卫)察合台后王嫡系统治上层明廷在嘉峪关外设置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7个卫所。后沙州卫内迁,其故地另置罕东左卫。均与察合台后王嫡系有关的蒙古卫所。
那里与藏传佛教僧侣取得联系,而且入明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地区仍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以及故元遗僧留下来弘法,甚至上述地区的统治者本身也是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格鲁派跃升为卫拉特蒙古各阶层主尊的藏传佛教教派之前,在卫拉特各部中发挥影响力的教派或许为噶举派和萨迦派。元末,曾经由元朝皇室扶持的萨迦派地方政权被帕竹噶举地方政权所取代,萨迦派影响力遂开始减弱。
格鲁派在藏地兴起以后,噶玛噶举派与新兴的格鲁派之间常有矛盾及冲突,并在随后的时间里,各自又得到过蒙古贵族们的扶持(如移驻青海的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倾向于扶持噶玛噶举派)。而《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定一方面要打压萨满教传统势力,另一方面也有压制格鲁派以外的其他藏传佛教教派的目的。。史载,正统十一年八月,“河州卫番僧加失、领真在罕东卫住坐年久,为其都指挥班麻思结奉使往瓦剌(明代汉籍把“卫拉特”记作“瓦剌”)也先处约为婚姻,交结甚密……”[5]卷144,2846。
表明在也先汗时代,统一过东西蒙古的卫拉特贵族们运用其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在新兴的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之前依旧非常重视僧侣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尽管我们可以肯定,这时期的藏传佛教也只在蒙古上层中有一定影响以外,与元朝的情况相同,对底层蒙古百姓而言,这时期的藏传佛教对蒙古人依旧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直至17世纪初,卫拉特人萨满信仰仍旧根深蒂固。
可以说,卫拉特贵族们崇敬藏传佛教僧侣,一方面是出于信仰因素驱使,另一方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东西蒙古之间的长期竞争所造成的。加之明廷依元制不仅大力扶持西藏的帕竹噶举地方政权(甚至一些皇室成员也皈依了藏传佛教),也十分顾虑蒙藏间频繁的宗教往来会带来边疆的不安定。因此,适度控制蒙藏之间的人员往来,对明廷来说是建国以来的既定政策。而退居草原的蒙古贵族们也想方设法开通进藏朝圣的通道,与明朝或战或和,不仅要获取与明朝互市的权利,也在争取同样尊崇藏传佛教的明廷的好感以外,通过藏传佛教希冀实现在蒙古各部中的正统地位。
不过斗转星移,也先汗被击杀以后,东蒙古迅速崛起。于阿勒坦汗威震蒙古、安多及康巴地区时,藏地新兴教派——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寻找到了自己新的政治盟友,并开始在蒙古地区弘传格鲁派教法。由于格鲁派得到了强大的土默特万户们的大力扶持而得到快速发展,故与其有竞争关系的其他蒙古部落也积极争取与格鲁派建立联系,并以互赠梵封、喇嘛尊号为荣。
16世纪末17世纪初,格鲁派迅速在喀尔喀、察哈尔等东蒙古部落中传播开来,甚至在新兴的后金领土上也有格鲁派僧人积极弘法天命六年(1621年),曾在漠南蒙古科尔沁部传教的西藏喇嘛斡禄打尔罕囊素(?rl?γdarqannanγsu)投奔后金,成为较早在后金传教的藏族喇嘛。
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贵族土尔扈特人赛英台奈思麦根台曼奈[6](即著名的卫拉特高僧内齐托音的父亲墨尔根特木纳)首倡在卫拉特各部中引入格鲁派,但起初苦于东蒙古豪强长期扼守进藏通道(由新疆东部经青海入藏的通道),故一时很难与西藏宗教界取得联系(一些史料也证明,约于16世纪末,卫拉特贵族们已于格鲁派高僧有了断断续续的联系)。于17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格鲁派才在卫拉特人中有了比较顺畅的发展势头,其标志性事件为卫拉特贵族们主动送子出家为僧,其中就有蔑尔根特莫尼之子内齐(NeiCˇi)托音一世和拜巴噶斯义子咱雅班第达纳木海扎木措等闻名蒙藏地区的卫拉特活佛们。
他们不仅把宗喀巴教法在整个卫拉特蒙古人地区普遍弘传,且在常年的弘法过程中,尤其对藏传佛教的“本土化”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1640年卫拉特部和漠北喀尔喀部联合颁行《蒙古(喀尔喀)·卫拉特法典》,其一项重要内容即以法律文本形式巩固了藏传佛教及其僧侣阶层在卫拉特及喀尔喀蒙古人中的神圣地位,亦是统治阶层由上而下通过强制手段将藏传佛教世界观转变为蒙古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
由此源自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成为卫拉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僧人们又主动的将被法典保护的藏传佛教教理与卫拉特人本土的萨满文化有机融合而使其更易被卫拉特人所接受,继而形成藏传佛教文化圈中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的蒙古佛教文化。在这一藏传佛教的“本土化”实践中出自卫拉特的两位蒙古高僧对卫拉特人,甚至对整个蒙古族宗教信仰由萨满到藏传佛教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二、内齐亦有学者认为应发音为“NaiJˇi(阳性词)、乃济(名词)”,而“NeiCˇi、内齐(动词)”为阴性词;由于在该传记蒙古文原文中“Cˇ”和“Jˇ”两个音素的书写形式几乎相同,故对该喇嘛名称的读法说法不一,本文将依循后一种读法。托音一世对格鲁派的“本土化”传播
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蒙古地区并发展成主尊教派的进程中始终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可以说,维护萨满教的传统势力对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一直设有各种障碍由清朝宋伯鲁编纂的《新疆建置志》(卷3)记载有清末土尔扈特裕勒都斯(今巴音布鲁克)草原上的格鲁派僧人人数为1100余人,宁玛派抑或萨迦派喇嘛人数为800余人。这些数据说明,尽管《蒙古·卫拉特法典》将格鲁派定为卫拉特人法定的主尊教派,但强制性手段未必能把包括萨满在内的其他宗教或藏传佛教其他教派尽除于外,而这也进一步说明,直至清末,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在卫拉特人(这里所指为土尔扈特人)那里仍有一定影响力。
汉文史料及当代部分研究者习惯把藏传佛教各教派名称依照僧人所穿戴的衣饰或某一特定的色彩符号区分成“红教、白教、花教、黄教”,等等,以致部分研究者不甚了解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的区别,笼统地认为17世纪初的察哈尔林丹汗和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尊崇的教派即为红教(亦有研究者把萨迦派、宁玛派、噶玛噶举统称为红教),但翻阅蒙藏文史料会发现,林丹汗更倾向于尊崇萨迦派,并向萨迦派的沙尔巴呼图克图接受过灌顶,而驻锡于青海的喀尔喀绰克图台吉尊崇的应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这一点我们从《蒙古·卫拉特法典》所制定的条例内容中可以探知在宗喀巴之教被确立为卫拉特各阶层“国教”之前,萨满巫师们与格鲁派僧侣之间一直存有很大的矛盾与冲突。
而独尊格鲁派的规定不仅源于卫拉特蒙古人虔诚的信仰心理需要,也在于蒙古各部之间的政治博弈。16世纪末,蒙古右翼土默特和鄂尔多斯万户的贵族们先行皈依了格鲁派,不久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于土默特阿勒坦汗的家族中。蒙古右翼贵族们皈依格鲁派的举动很快引起了蒙古其他部落贵族们的注意,并产生相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阿勒坦汗去世后不久,漠北喀尔喀的阿巴岱汗前往土默特部拜谒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达赖喇嘛授予其“佛法大瓦齐赉汗”(Nom-unyekeoCˇirqaγan)[7]的称号,日后其家族中诞生多罗那他的转世灵童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扎纳巴扎尔。与此同时,曾在土默特部传教的安多阿兴(蒙古文a?ing,藏文)喇嘛也前往察哈尔、巴林、喀喇沁等部弘法,同样受到部落贵族们的敬重而格鲁派在漠南东部蒙古中有了一定的影响。
三、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对藏传
佛教的“本土化”传播相比把漠南蒙古作为大本营来一心传播宗喀巴宗教的卫拉特高僧内齐托音一世,同样作为贵族出身的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不单是位佛学造诣精湛的格鲁派高僧,亦是位出色的卫拉特喇嘛政治活动家。但在这篇拙文里,笔者对该喇嘛政治身份的讨论着墨不多,主要探讨他对卫拉特抑或蒙古族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及“本土化”实践中的贡献问题。
四、余论
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此源自雪域高原的藏传佛教传入蒙古草原时也经历过与萨满信仰之间的相互排斥与融合过程。《咱雅班第达传》记载,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要求卫拉特人烧掉翁滚(Ongγon),若有人祭祀翁滚就罚他马、羊,用狗屎熏巫师、巫婆,等等参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咱雅班第达传》(西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第六卷,蒙古文),兰州: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1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25页。
尽管如此,萨满教并未在卫拉特人中销声匿迹,而是通过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适度融合,仍旧保留有一些萨满文化要素,例如敖包祭祀、祭湖(青海湖)等仪式在传统上均为萨满信仰的典型祭祀活动,而如今僧人们也参与这些祭祀仪式。这一融合的过程不单在仪式、仪轨等领域相互吸收各自信仰文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要素,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基于蒙古人文化心理特征,以蒙古人易于理解的方式传播及建构本民族的佛教文化,以期创建佛教文化圈中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蒙古宗教”。尽管传播并发展“蒙古宗教”确实也遇到过一些藏族喇嘛的非议,认为藏文经文的法力大于蒙古文经文而不太支持蒙古语诵经的推广[21]。
加之清朝的宗教政策一定程度上对“蒙古宗教”的产生构成无形的阻力,这一点可以从顺治朝两位蒙藏高僧之间的冲突中管窥一二。即便如此,我们抛开清朝的国家政策因素不说,就单论内齐托音一世、咱雅班第达纳木海嘉木措两位高僧为蒙古族佛教文化的成长与繁荣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去称颂的。
[参考文献]
[1]王希隆.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95.
[2]樊保良,水天长.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
[3]王桐龄.中国民族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520.
[4]王石庄.《元史》名词术语汉蒙对照词典:上册[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329.
[5](明)孙继宗.明英宗实录:卷37[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713.
[6][俄]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M].马曼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0.
[7](清)善巴台吉.阿萨喇克其史(蒙汉合璧,蒙文影印件)[M].乌云毕力格,译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187.
[8][意]图齐,[西德]海西希.西藏和蒙古的宗教[M].耿昇,译.王尧,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384.
佛教论文投稿刊物:《佛教文化》(双月刊)是由赵朴初先生创办,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宗教文化期刊。主要面向佛教界、文化界、艺术界人士及社会大众,旨在通过对佛教文化艺术的研究与创作,对当下佛教文化现象的展示与解读。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1524.html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