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19世纪上半叶,中国说唱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74年司登德编译北京地区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将子弟书第一次介绍给西方。此期俗曲编译较早期之《花笺记》翻译更具学术自觉,北京说唱被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
[摘要]19世纪上半叶,中国说唱文学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1874年司登德编译北京地区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将子弟书第一次介绍给西方。此期俗曲编译较早期之《花笺记》翻译更具学术自觉,北京说唱被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20世纪中叶,中国说唱逐渐进入西方学界的系统研究谱系,论著渐多。近30年来,海外学者们从文学史书写、性别文化、口传理论、族群认同等多维度研究中国说唱,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也逐渐增多,且呈现出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这种“他者”的侧目与关注可以让我们对中国说唱的学术研究有更丰瞻的理论视野与学术对话,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
[关键词]说唱文学海外汉学文化理论文选视阈文学史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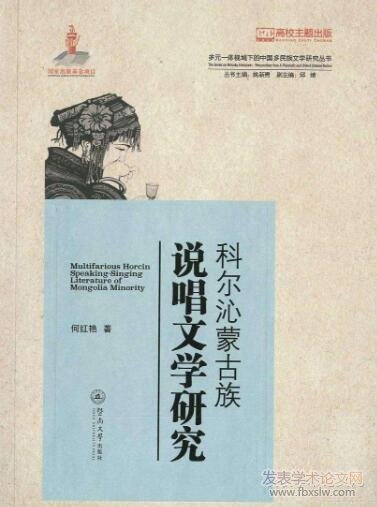
文学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季刊)创刊于1984年,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的国内唯一以研究和介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专业学术刊物。
一、引言
说唱文学主要指历代流传于民间的各种传统说唱及其文本,这些文本多为民间书坊刊刻或个人抄录的小册,分为抄本与刻本,明清时期达至鼎盛。主要包括弹词、大鼓、木鱼书、宝卷、子弟书、词话、俗曲等。说唱文学是民间文化中的潜流,源源不断地流淌于悠悠岁月与广袤的地域之中。其所呈现的庶民热闹场景与学术研究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在传统社会中,它们比起小说等文体“卑贱”更甚、殊难入流。自五四时期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如刘复、李家瑞、傅惜华等关注民间说唱并挖掘整理,其功甚伟。国内学者浸润于本土文化,自有其研究脉络。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中国通俗文学、民间说唱的研究虽然有言语不通、地域殊绝等诸多隔阂,却能从“他者”处只眼关照,颇具特色。
近些年海内外的中国说唱研究互动渐增,一些研究论著陆续译成中文。遗憾的是,海外学者的中国说唱研究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整体关注,即使涉及相关议题,也多分散于不同畛域的文类中。因此,文章尝试对近二百年之海外研究进行回顾与阐述:一方面,在历史长河中关照其总体研究脉络与时代流变,另一方面,以典型个案尤其是当代海外学者的研究实例分析其研究视阈与学术方法。关于日本学界对中国说唱之研究,已经有学者进行了梳理,[1]此处主要以北美和欧洲为主体进行论述。
二、东风初尚:早期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概述
1824年,欧洲人首次把广东地区民间说唱文学——木鱼书《花笺记》,译成英文,题名“ChineseCourtshipInVerse”,由东印度公司印制,译者为东印度公司的排印职员汤姆斯(PeterPerringThoms,1791-1855)。该书每页上为中文原文,下为韵文体译文,属于目前所知最早的说唱译本。译者从中国诗歌史的角度分析《花笺记》的诗节、韵律及思想。[2]西方早期一些汉籍目录多以“诗歌”标注该类文本,如威廉·肖特(WihelmSchott)为普鲁士王家图书馆及艾约瑟(JosephEdkins)为牛津大学图书馆所编书目。[3]1868年《花笺记》以纯英文版付梓。封面题“Hwatsienki.TheFloweryScroll.AChineseNovel”,译者为约翰·包令爵士(SirJohnBowrng,1792-1872)。
不同于上个版本,此版将花笺记意译为“TheFloweryScroll”,强调该书的文体类型是中国小说。在序言中,包令谈到有鉴于Thoms韵文版本的不完美与缺失,遂以散文体风格重新翻译说唱,即以小说体的形式呈现中国文化的“民族风格”。[4]上述两个译本呈现出中国说唱文学在西人眼中的不同学理脉络与人文意涵。说唱文学如木鱼书兼有韵文唱词与散体叙述,将其纳入“诗歌”则与《诗经》以来的悠远诗体相契合,呈现其古“格”;将其纳入小说则与宋元以降的小说创作对接,彰显其民“韵”。约翰·包令认为中国人大多使用统一的文字与表达形式,诗歌是精英文士的文化表述。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用精英文人较少涉猎的小说来为《花笺记》的地域性与民间风格“正名”。译文中大量的脚注既是对词汇的注解,也是对中国“民族风格”的诠释。
西方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关注在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已初显端倪。1880年,一位俄国学者在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后饱含深情地写到:“中国文献不属于已经消亡的人类古代文献之列。虽然,在创造性、典型性和科学性方面中国文献逊色于希腊和罗马文献;但是,仅就所保存下来的成果而言,可以肯定,中国文献在规模的宏大和内容的丰富程度方面更胜一筹。”[5]
(P1)这位学者就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教授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1818-1900),中文名王西里。这段文字出自他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本簿册,该书在中国有两个不同的译名:一般学术著作多称之为《中国文学史纲要》;2014年该书中文版正式付梓,称为《中国文献史》。《中国文学史纲要》中除论述传统诗文外,还专门提到了中国的说唱文学——弹词。瓦西里耶夫称之为“诗体小说”,包括《再生缘》《来生福》《锦上添花》等,这些都是他亲自在中国购得的民间说唱文献。19世纪中国很多小说、戏曲仍不受传统学界重视,遑论说唱文学了。而瓦西里耶夫认真收集相关唱本并研究之,实属难得。[6]将说唱文学称为“诗体小说”者,瓦氏并非孤例。1853年,法国学者安托尼·皮埃尔·路易·巴赞(AntoinP.L.Bazin,1799-1863)的《现代中国》(ChineModerne)一书列有中文书目,其中将《花笺记》等说唱称为“诗体小说”。[7](P535)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是西方翻译中国说唱俗曲的发展时期。此期俗曲翻译延续了从《花笺记》所开始的“民族特质”之追求,将民间俗曲进一步解释为人类重要成员的“精神状态”(司登德)与“民族的诗歌”(韦大列)。司登德(G.C.Stent,1833-1884)曾随英国使节卫队入驻北京,中文熟稔、知识渊博。先后编有《中英北京方言辞典》(1871)、《中英简明字典》(1874)等。他对北京地区的民间文化、民谣俗曲兴趣浓厚,先后搜集并翻译了两本俗曲集:《二十四颗玉珠串》(TheJadeChapletinTwenty?FourBeads:aCollectionofSongs,Ballads,etc.,fromtheChinese,1874)、《活埋》(EntombedAlive,andOtherSongsandBallads,etc.,fromtheChinese,1877)。在《二十四颗玉珠串》序言中,他提到很多唱本来自街头艺人的表演,痴迷于唱词的他将这些艺人延至宅舍,并请自己的中文老师逐字记录。他这样评价这些俗曲:
这些人民的诗歌芬芳自香,散发出深邃而广远的自然情思,至今仍被忽视。……它们是人类大家庭重要成员的精神特质之呈现。[8](Piv)
司氏所辑两种英译俗曲对于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非常重要,至今却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一些学者在顺带提及上书时,仅将其作为“民歌”一笔带过。笔者仔细研读《二十四颗玉珠串》与《活埋》,发现它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歌,其中所搜集的大部分为清代北京地区流行的说唱文学,包括子弟书、大鼓、单弦、马头调、莲花落等。《二十四颗玉珠串》收录24首、《活埋》收录28首,两书共计辑录翻译52种北京俗曲。唱叙的故事包括昭君出塞、杨贵妃与唐明皇、赵云救阿斗、窦娥六月飞雪等,这些俗曲唱本很多都是从长篇说唱文学中节选而来。如《二十四颗玉珠串》中翻译了子弟书《长板坡》,这是目前所知最早被译成英文的子弟书。《长板坡》又名《麋氏托孤》,现存刻本为光绪十八年(1892)会文山房本。
司氏译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至迟1874年,子弟书《长板坡》已经在北京地区广泛传唱,这比其刊刻年代提早了近20年,对于研究子弟书在北京地区的表演、传播颇多助益。另外《活埋》中选有马头调《阔大奶奶逛西顶》。此曲讲述一位阔妇人穿戴华丽参加北京西顶庙会的活动,极富京城风情与市井趣味。清代一些书坊书目中列有此曲,如《时道下曲马头调上单下单目录》收录此曲,并在旁批注“瞧玩艺,小曲,上单,三百”,可知清末刊本中此曲售价为三百文。“百本张”抄本《马头调合选》也选录该曲。结合司氏译本,多少可以探知当时其在北京风靡的盛况。
司登德对俗曲的编译不仅仅出于热爱。序言中还列出了英国、印度、匈牙利、挪威等各国的学者及作品,彰显出其广博的阅读视野与理论基础。司氏对俗曲民谣之关注并非孤例,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BaronGuidoVitale)将自己在北京调查所得译成《北京的歌谣》(PekineseRhymes,1896),他十分强调搜集过程的艰辛与这些歌谣的真实性,并认为:“根据这种歌谣和民族的感情,新的一种民族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9](P425-427)英国人金文泰(SirCecilClementi,1875-1947)将《粤讴》翻译成英文CantoneseLove-Songs,即《广东情歌》。金氏精通梵文、拉丁文,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翻译该书,文风典雅俊丽。他在导言中将粤讴与西方文学中的史诗进行比较,认为这些民间诗歌更接近希伯来古诗,如《圣经》中之“雅歌”,而与希腊诗歌不一样。[10]他还将粤讴与奥维德之《爱经》、班扬之《天路历程》进行词汇与主题的比较。虽然在今人看来,广东情歌与奥维德等西方诗作情境殊绝,甚少可比性,但是从中可以看到金氏希望将中国民间歌谣与西方文学经典比肩而谈的拳拳之心。同年,荷兰学者高延(J.J.M.deGroot,1854-1921)在《中国各教派受苦史》(1903)中介绍了几种福建地区的宝卷文本。多年后,魏莎(GenevieveWimsatt)翻译孟姜女故事大鼓(1934);美国人WilliamC.Hunter翻译了俗曲马头调《王大娘补缸》(1937)。
至20世纪中后期,中国说唱逐渐进入海外学者的系统研究。1965年,欧洲学者VenaHrdlickova撰文《中国说唱艺人的职业训练与艺人行会》(TheProfessionalTrainingofChineseStorytellersandtheStorytellers?Guilds),对传统话本及说唱艺术的口头传承特征及职业训练、说唱艺人的手抄本、表演本等颇多研究;[11](P227)俄罗斯学者司徒洛娃对宝卷多有研究,撰有论文《关于明代宝卷的流传问题》(1972)等;加拿大学者石清照(KateStevens)在20世纪70年代以京韵大鼓研究为其博士论文之题目;[12]法国学者雅克·班巴诺(JacquesPimpaneau)著有《歌者、讲故事者与武术艺术家》(1977)。至此,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说唱的研究终于绽放出愈加自觉的学术姿态。
三、文学史与文化理论:宏观视野与微观烛照
20世纪末至今,海外学界对中国民间说唱之研究更加丰富多姿,从文学史的总体关照到各个说唱文类的细致分析层出不穷,在理论深度与文化广度上多有突破与灼见。20世纪晚期以降,欧美有多种中国文学史版本面世,这些文学史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视域与书写姿态,尤其是两本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及《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13年,《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面世,其下册第五章以“说唱文学”为题,专章探讨了传统的说唱文学如变文、诸宫调、宝卷、道情、鼓词、子弟书、弹词、木鱼书、竹板歌、女书文学等。该书认为,“说唱文学”(prosimetricandversenarrative)乃是尚未获得权威地位的文学类型,属于俗文学(popularliterature)。[13]
(P391-392)2016年,《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被翻译成中文,该书卷帙浩繁,共55章。除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传统文体外,第七编还专门分析了民间文学尤其是说唱文学,主要包括第47章“敦煌文学”、第48章“口头程式传统”、第50章“地区文学”等。该书对于说唱文学的介绍不仅比剑桥文学史增加了篇幅,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该书对口头程式传统与说唱文本进行了区分,并将之与欧洲文类进行对比。与西方口头传统(史诗等)相比,中国口头传统与讲唱传统在书面文化发展后繁盛,与文本的关系更为密切。[14]
(P1121)这几章的执笔人虽然来自欧洲、澳洲及北美等不同地区,但是具有完整而新颖的理论认知。他们一方面强调口头文学的先在性与独特性,认为乡村说书人的口头故事和文人的复杂叙事之间存在审美和语言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提到,中国的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是在相互联系中定义自身,在这两种二元分立传统的互动中可以窥见中国口头程式文化的核心重要性。[14](P1095)
性别文化是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国说唱尤其是弹词时的关注点。17世纪以来,江南弹词创作极为丰厚,其中篇幅繁浩者多为闺阁女性创作,这些作品既是说唱体文学,也被称为“弹词体小说”,其独特的阃中书写引来海外学者的瞩目。如哈佛大学胡晓真于199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LiteraryTanci:AWoman?sTraditionoftheNarrativeinVerse”探讨了明清以来弹词文学的女性叙述特征与女性意识,对于长篇弹词中的“父女关系”等均有细致分析;[15]高彦颐(DorothyKo)教授的著作《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oftheInnerChambers:WomenandCultureinSeventeenth?CenturyChina)将弹词女作家与远方友人的书信往来称之为“卧游”,[16](P237)并将视野扩展至整个江南社会文化生态,将女性创作与明末民间书坊、大众阅读、女性教育等关联起来,建构出独特的江南女性生存语境。
晚近著作则有李惠仪(Wai?YeeLi)《帝国晚期中国文学中的女性与国难》(WomenandNationalTraumainLateImperialChineseLiterature),2014年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该书并非专门的说唱研究著作,但是其中一个章节专门以弹词《天雨花》为中心分析这部长篇说唱唱本的明清鼎革书写与女性书写。女主人公左仪贞以独特的方式反抗传统社会秩序,呈现出变革时代与国难格局下女性独特的夫妻观、闺友观,其中不乏一定程度的女权意识与自我焦虑。面对动荡政局与社会失序,女性作者与女性形象呈现出自己的诗性反思与回应。[17]
(P203-230)LiGuo所著《晚清及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女性弹词小说》(2015)以《再生缘》《笔生花》《影梦缘》《侠女群英史》《风流罪人》五部弹词为中心探讨女性形象的建构及其叙述倾向。史蒂文森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文学中的荡妇形象:形象、文体、颠覆及传统》(2017)一书收录了艾梅兰的论文《反转作者:两部清代弹词中女性笔下的荡妇形象、羞耻与嫉妒》,探讨弹词中的荡妇形象与作者创作中的创新意识。[18]
对于弹词等说唱文学的研究除了性别视野,还有不少学者走出书斋与理论围城,将足迹踏至远方的土地。美国学者马克·本德与丹麦学者易德波两位教授乃其中典范。马克·本德(MarkBender)的博士论文“ZaiShengYuanandMengLijun:Performance,Context,andFormofTwoTanci”(1995)对弹词《再生缘》《孟丽君》的文本、表演等进行了细致分析;2003年其英文专著《梅与竹:中国苏州说唱传统》(PlumandBamboo,China’sSuzhouChantefableTradition)出版。该书分为三章,第一章总体介绍弹词的源起、特点、术语、审美概念、韵白等。第二章主要探讨弹词口头领域,运用“口头理论”“大脑文本”“表演理论”民俗学理论等分析弹词的口头表演特色及其与书面文本的关系,并以《三笑》和《珍珠塔》为例详细分析。第三章则集中于《再生缘·双女成亲》的表演,分析不同表演者对表演风格、现场声音的掌控,从而对俞调、蒋调等流派作出了自己的理解。
阴阳观念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素。马克·本德在分析弹词表演时巧妙运用阴阳概念,使说唱的表演研究浸润了浓厚的文化质素与哲学意味。他认为,阴阳与弹词中的男女档有关,但并非源于表演中的实际性别,而是基于角色及与双档关联的多重叙述,阳在双档中代表主要叙述如男性角色、强权女性,阴代表女性或小人物。其他如认为关子书为阳、弄堂书为阴等,认为说书者之“阳”驾驭观众之“阴”,但两者相互依赖、动态互联才是高妙境界等,也都呈现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19](P144-146)丹麦学者易德波(VibekeB?rdahl)教授主编的《永远的说书人——现代中国口传文学研究》(1999)是英文中有关中国说唱文学的第一本论文集。
该书连同《导言》共计收录20篇论文及5篇说唱表演的口述纪实,其中对于扬州说唱的表演、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等也有诸多精彩论述。对扮演叙事者角色的说书人从其名词衍化过程到以说书人为主题的绘画研究,以及佛经与宗教故事中的叙事者展开深入讨论,尤其书末压轴的扬州说唱名家表演纪实,显示出对说唱演员之艺术表现以及表演艺术之理论与实际的重视。[20]易德波专著《扬州评话探讨》也从舞台技艺、表演术语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查与研究,并探讨了说书艺术的“真口头性”和“假口头性”等问题。[21]其研究一直致力于探讨“口传”与“书写”的互动关系,如她与玛格丽特主编的《中国通俗文学中口传与书写之互动》(2010)及其专著《武松打虎:中国小说、戏曲、说唱中的口传与书写传统的互动关系》(2013)均涉及不同文体中口传与书写的多维视角。[22]
大众文化是西方当代文化理论中重要的理论现象。在笔者看来,大众文化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大众文化是指工业生产与现代媒介催生下的各种文化现象,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流行文化,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批评的大众文化;广义的大众文化则不限于工业生产与当代文化,主要是指与“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对立或互补的文化现象,在欧洲可以上推至15、16世纪前后。剑桥大学教授伯克(PeterBurke,1937-)是较早对欧洲大众文化进行研究的学者,他提到,德国学者赫尔德搜集整理民谣,其追随者重视人民,相信“风俗习惯、民谣民谚等都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表达了特定的民族气质”;发现大众文化是一场文化原始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古代、遥远和流行均处于平等地位中。[23](P10-13)
由此可知,在这一意义上,大众文化乃是对传统社会中非主流文化的一种全新发现。不少国外学者以此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社会与说唱文学。1967年,上海嘉定墓葬出土文物中发现大量唱本,其中包括成化七至十四年(1471-1478)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16种,如《花关索出身传》《花关索认父传》《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传》等。这些唱本不仅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花关索故事、包公故事的认识,而且对研究民间“词话”这一说唱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澳大利亚学者马阑安(AnneEMclaren)教授的著作《中国大众文化和明代说唱》(ChinsesPopularCultureandMingChantefables)对以成化词话为中心的明代通俗说唱及文化仪式、社会观念、说唱修辞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书后附有花关索词话影印数页。
该书认为,说唱词话文本应置于16世纪文化知识逐渐大众化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这种方法需要类似于“文学人类学”的深入调查,这些是传统的文学分析无法体现的。他认为这些文本不仅仅是民间流行的文化的简单载体,而且代表了白话通俗文本中的“非文学”类型(non?literarytype),并在复杂的口头仪式中找到了其自身的意义。[24](P11-12)
姜士彬(DavidJohnson)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将民间说唱、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形式汇入大众文化的研究视野。该书主要以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以来的民间宗教如白莲教、天后信仰和通俗文学如评话、戏曲、圣谕宣讲等为中心,探讨帝国晚期多样的社会百态与庶民心理。如作者认为评话“为那些文化水平不高难以阅读经籍的读者提供了娱乐与教诲双重功用”。[25](P121)在分析文本时,作者擅长从社会经济、文化传播、社会阶层、民间信仰、大众教育等诸多层面剖析,让人看到文本之外丰富的社会形态与文化视野。
伊维德(WiltL.Idema)教授认为,海外尤其是英语世界中的学者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三个主要领域分别是弹词、宝卷和子弟书。[26]诚如伊氏所言,除上文所谈及的弹词外,宝卷、子弟书也是很多学者的关注重点。不少学者均有宝卷专著问世。欧大年(Overmyer)教授对传统宗教、明清宝卷等多有研究,其专著《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以夯实的文献与调研基础研究了元明以来的民间宗教文本,对于孟姜女故事在宗教文本中的演变也多有着墨。
同样是关注宗教文本与宝卷唱本,英国学者杜德桥(GlenDudbridge,1938-2017)以故事和传说将不同时期的文本绾结在一起,出于宗教信仰而入于民间价值,因此其宝卷及相关说唱研究对于文学学者而言受益良多。杜氏所著《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27]以碑刻、宝卷、小说等为轴,将唐宋至晚清的妙善传说进行了细致爬梳甄别。故事之传说乃是很多学者尤其民俗学者的学术着力点,大量学者通过田野考察研究传说的口头价值与叙事意涵。日本学者泽田瑞穗于1941年在河北乡下考察口头的妙善传说并完成相关文章。与上述研究视阈与方法不同,杜德桥强调要回到写本研究,即“以书籍为本的研究”。[28](P20)他极为看重不同文本对同一题材的书写:
我们得深入探索隐约界于宗教、文学与娱乐之间的各种民间作品,包括故事本子、剧本、经文、唱本等。这些作品不论其本身是否重要,往往道出了神话和祭仪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在自觉性的文学创作中只含蓄地暗示出而已。[28](P5)
此种学术思路彰显出现代学术研究的丰富视野与多元维度。数百年来,民间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研究突破传统文本之局限,视野不断延伸至地域口头传说。而杜氏则重新审视文本之魅力。杜德桥深厚的民间宗教与文献知识学养,使其在研究说唱时吐辞不凡,行文绵密深长。如其论文《华岳三娘与广东唱本〈沉香太子〉》(TheGoddessHua?YuehSan?nianandtheCantoneseBalladCh?en?hsiangT?ai?tzu)。
[29]该文在分析木鱼书《沉香太子》时不是单纯对其文本形式和地域风情进行分析,而是将其置于唐宋以来的华岳三娘与沉香传说的纵向脉络中,着重将其与之前的华岳三娘传说包括宝卷《沉香太子》、弹词《宝莲灯》等进行对比。他通过分析点出宝卷弹词等相关传说呈现的三大特点:代际模仿;神性因素的复杂;处理失去的家庭关系。木鱼书《沉香太子》现存三个版本,刊刻书坊与年代不同,但是文本内容却一致。木鱼书在处理这一具有宗教、神话色彩的故事时显然与弹词等故事相殊,具有创新性的改编。以《宝莲灯》为代表的传统故事呈现的是家庭关系的失去与拯救,即沉香幼时失去母亲,长大后劈山救母,母子夫妻俱得团聚。木鱼书则对女性关系更感兴趣,沉香之父刘锡进京赶考,沿途因缘际会,分别有了两位妻子:瑞仙与三娘。三娘与华山不再有直接关系,传统故事中仙与凡爱恋生子而被惩罚幽禁的叙述也不见踪影,新的故事主题与结构形式逐渐彰显。
杜氏拨开唱本中的层层云雾,揭示出木鱼书在讲述故事时的主题轴线:仙与凡的重新设定、母与子的伦理反思、真与假的人生况味。沉香没有救母,三娘重返天庭。这暗示了人神分离的宗教观念。人神团聚的神话终被打破,从与人类的联系中退出,而以寺庙与塑像,作为神与人间的联系媒介。最终复归于平静的宇宙、政治与家庭秩序。[29](P627-646)当沉香徘徊于养母(瑞仙)与生母(三娘)之间的伦理困境时,三娘以一句“生娘唔大养娘大”轻松为其揭开难题。另外如易装出行、金兰结拜等均显示出宗教体裁的世俗化与地域化。前人对于木鱼书《沉香太子》的重设历史语境也几乎没有关注,在唐宋笔记中,该故事主要涉及汉、唐之间的神话谱系转化,而木鱼书将其后推至宋代,没有了齐天大圣等神系人物,却出现了包公认瑞仙为义女等情节。这些唱本中似乎无足轻重的“无意识”书写,在欧氏笔下却与皇权更迭、权力设置等相关联,具有独特的人文意涵。
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是近些年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视阈。尤其在历史研究领域,相关论著不断。21世纪初,哈佛大学欧立德(MarkC.Elliott)教授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满族之路:八旗子弟和清代的民族认同》,书中对满族族群身份认同的重新思考颇受海内外学人倚重。这对于以八旗子弟为创作主体的说唱文学——子弟书而言,或可在文史互证中得以重新认知。美国学者赵雪莹(ElenaSuet?YingChiu)在此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其论文“TheOriginsandOriginalLanguageofManchuBannermenTales”对子弟书的起源与满族语言进行了探讨;其专著《子弟书:清代满族说唱与文化交融》(BannermenTales(Zidishu):ManchuStorytellingandCulturalHybridityintheQingDynasty)201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该书是海外第一部子弟书研究专著,探讨了子弟书的表演场域、文本传播等诸多问题。八旗子弟的说唱文本呈现出满族与汉族两种文化的交融与互渗。该书共分5章,分别论述子弟书的起源及其社会文化语境、子弟书的表演、满汉双语子弟书、汉语书写的子弟书、子弟书的传播等。作者熟谙满语,兼之满族后裔身份,故能对子弟书中的满语形式有独特认识。
子弟书以其独特的创作群体(八旗子弟)与“子弟书写”在中国说唱文学中傲然独立。近十几年以其为主题的学位论文、期刊文章日渐增多,成为说唱研究中的“新宠”。但一些文章重复引用清代史料中的八旗文献以呈现所谓旗人风俗,缺乏新见。ElenaSuet?YingChiu新著以“满族身份认同”为核心,从细处着墨,每有新意。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现藏德国柏林图书馆。《寻夫曲》全文为满汉合璧,即每句诗词都用满汉文进行书写。她通过对原本仔细甄别,发现该书封面仅题汉字“寻夫曲”,右上角的满文字样乃是稍晚添加。因此,她推测早期子弟书并非满汉共存。[30](P61)对满汉双语子弟书5种唱本的分析是全书的亮点。这5种除上文所提《寻夫曲》,还包括满汉兼子弟书《螃蟹段儿》、汉字书写间杂满语音译的3种子弟书《升官图》《查关》《哭城》。上述5种“双语”文本显示出满语在18世纪及19世纪的独特价值。《升官图》故事人物源于明代小说《金瓶梅》,讲述西门庆与潘金莲第一次见面情事。唱本中大量使用清代满语音译官职,作者认为似棋盘游戏中的“副文本”,从而将古典小说与官场职位“戏谑”地组织在一起。[30]
在族群认同理论的烛照下,该书将视野从文字文本拓展至对18、19世纪两种文化与民族身份的思考。一方面是满族文化的杂糅(hybridization),另一方面是对延续满族身份优越性的确认(superiorityofManchuidentity)。在其他学者笔下,满族身份认同随着汉文化的同化、国族力量的衰微而渐趋消逝,作者却认为,八旗子弟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独特的习性”应被考虑进渐趋复杂的族群身份认同之中。子弟书代表了八旗日常生活中社会文化的诸多因子,这些均可促成其族群意识。作者细致地指出,鹤侣氏等所做的系列侍卫论子弟书,虽然其文字书写为典型汉字,且有来源于古诗词的文人之叹,但其中的职位沦落与满族悲情恐非满族子弟难以深入体谅。这些侍卫子弟书可以被视为族群认同在持续与变迁中的一种表达与状态,以表述性的方式呈现了文化之融合并在清代保持了满族的身份认同。作者借用欧立德的观点,提出子弟书的书写与表演体现出了区别于骑射传统的标准之路,传递出一种表述性的满族之路。[30]作者从大陆、台湾、日本等地搜集的抄本与刻本图像亦为本书增色不少。
四、从文献搜集到选本考量: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的文献整理与当代文选视阈
早在16世纪,一些中国书籍通过传教士或商人便出现在欧洲。其中通俗文学如戏曲等文本在西方颇受珍视,这与其在东方之情形完全不可比拟。东方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这些作品乃是自娱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而在西方却因缘际会、辗转相生,成为万里之遥舶来的贵重之物。正如龙彼得(PiervanderLoon,1920-2002)所指出的那样,在明代被带到欧洲的书籍都是普通甚至俗劣的版本,任何中国学者都不屑于收集,相反,在西方图书馆却把他们奉为珍品。
《风月锦囊》(1553年刊本)由葡萄牙传教士GregorioGonzIvez委托在里斯本的西班牙大使JuanDeBoria于1573年献给西班牙国王。[31](P7-8)于是,一本在中国极为普通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风月之书在欧洲华丽转身,一跃而成为传教士进献的东方礼物。1605年,一位阿姆斯特丹书商CornelisClease在法兰克福书市上出售一批中文书籍,据称这些书是首次从中国运来,纸墨珍贵。之后,汉籍文献便在荷兰私人藏书目录中出现。这些书乃是由中国商人先运往印尼群岛,在那里被荷兰船员买去。[31](P1-8)另外如《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等“坊刻本”在中国明末以来江南各地大量刊印,价格便宜,在欧洲却需要高价拍卖,最终于1679年购置入德国的图书馆。1700年前被带到欧洲的还有300多本汉籍,现藏于欧洲各个图书馆。17世纪之后,这类文献主要由荷兰人提供。[31](P7-8)
海外的中国说唱唱本等通俗文学资料长期湮没于历史风尘之中,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海外学者们的爬梳整理与不懈努力,终使珍贵古籍重见天日。柳存仁(LiuTs?un?yan)“ChinesePopularfictioninTwoLondonLibraries”(1967)一书乃是英语世界中较早对欧洲所藏中国通俗文学文献进行调查与目录整理的著作。该书中文版名为《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于1982年出版,但是中文版仅有书目,删掉了英文中前几章的评论。在英文版的书目之前,作者对中国的民间书坊、刊刻版式等进行了介绍,有助于西方读者认识汉籍。
柳存仁整理的小说书目中,夹杂有弹词《探河源传》《绣像八仙缘》以及木鱼书《花笺记》的4种版本,作者把这类书叫做“说唱书”(Ballads)。20世纪70年代,德裔美国学者艾伯华(WolframEberhard,1909-1989)到德国图书馆调查研究,发现该馆所藏广东木鱼书38种,他于1972年出版《广东唱本提要》;1974年将其调查所得闽台歌仔册250余种编成《台湾唱本提要》。
20世纪90年代,英国等地所藏中国民间文献逐渐浮出水面,海外学者细心访查并将珍贵文献披露于世。龙彼得以自己在欧洲所见三种俗文学珍本编写了《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1995)。[32]这些资料分别来自英国和德国,包括剑桥大学所藏明万历刊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二卷,该书1715年以来一直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乃是JohnMoore(1646-1714)主教所藏4本中国书籍之一,之后由英王乔治一世赠与剑桥大学。另外两种乃是德国萨克森州立图书馆藏明刊《精选时尚新锦曲摘队》《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31](P1-8)英国学者杜德桥私藏有不少民间说唱文献,这些文献对于他的相关研究可谓相得益彰,另外,他将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普陀山1878年版妙善宝卷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1908年版同名宝卷等亲自查阅后与中国国内相关文献互为参证,最终完成了妙善传说的学术专著。
对于说唱文献进行全面调查与研究并非易事,需要长期奔走各国并不断勘验版本。在此方面成果最丰富者当属俄国学者李福清(B.Riftin)教授。李福清对中国俗文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对评话、木鱼书、子弟书、鼓词和弹词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李福清教授于1995年底在英国及荷兰调查当地收藏的汉籍,发现了22种日本学者所编的《木鱼书目录》未著录的作品,更有意义的是,他发现了木鱼书《花笺记》的残本,并随后在《汉学研究》第17卷第1期发表论文《新发现的广东俗曲书录─以明版〈花笺记〉为中心》(1999),证明了《花笺记》是明代的版本。此外,他还著有《德国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1995)、《俄罗斯所藏广东俗文学刊本书录》(1994)、《中国章回小说及俗文学书目补遗:据俄罗斯所藏资料著录》(1993)、《四十年海外汉籍的调查研究》(2006)等论文。还有的俄罗斯学者擅长利用本国的丰富藏本进行整理研究。如司徒洛娃将列宁格勒所藏的珍贵宝卷整理成《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院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宝卷”简介》一文。各国汉学家对中国唱本的热爱与执着探寻成就了欧藏唱本的最初风采,也确立了若干著录的规范。
当代海外学者在文学选本与译本中也愈加重视民间文学与说唱文学,呈现出愈加精细的分类标准与学术方法。梅维恒(VictorH.Mair)和马克·本德(MarkBende)2011年出版了《哥伦比亚中国民间与大众文学选集》(ColumbiaanthologyofChineseFolkandPopularLiterature)。该书精选了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民歌与说唱,将民间与大众文学分为6个部分:民间故事与口头传统、民歌传统、民间仪式、史诗传统、民间戏剧、南北方职业说唱传统,说唱在其中占据重要比例。该书还将所选说唱文学分为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包括了单弦牌子曲、子弟书、鼓词、京韵大鼓、快板书、山东快书、扬州评话、杭州评话、靖江讲经、弹词、木鱼书、白族大本曲。其中弹词所选唱本最多。
该书的编选原则是尽量避免官方或主流文学形式,对地域方言文学较为重视,以此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选集》互为补充。这些民间文本对于海外读者尤其是高校汉学专业学生全面理解中国文学的诸多维度如不同阶层、文化水平与历史阶段将有帮助。[33]从19世纪初期汤姆斯对《花笺记》的简单介绍到21世纪梅维恒等人对中国民间说唱文本的分类编译,选本的翻译与编纂渐趋体系化。
伊维德教授对中国戏曲、俗曲研究颇为精湛,其著名观点“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早已为国内学者熟谙。他将学术研究与文学翻译结合,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居功甚伟。2008年,他将孟姜女故事的10种民间说唱版本译成英文《孟姜女哭倒长城:中国传说的十种版本》(MengJiangnvBringsDowntheGreatWall:TenVersionsofaChineseLegend)。国内学者路工在20世纪50年代编有《孟姜女万里寻夫集》,包括各种民谣、说唱计36篇。伊氏在编选时并未全部从该书简单照搬并翻译,而是凭借丰厚的学养编选了10种唱本。比如,路氏文集中并未将闽南歌仔册收入囊中,颇有遗珠之憾。伊氏则将闽台流传的孟姜女歌仔册收入并英译,颇具慧眼。
其编选原则明显兼顾文献与田野两部分:前5个版本是明清至民初唱本;后5个版本是20世纪中叶后学者在民间搜集的唱本,包括甘肃《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河南平顶山《孟姜女哭长城》、湖南《姜女下池》、女书《孟姜女》、浙江民谣《孟姜女》。该选本不仅编选有方,且序言对孟姜女故事的历史、发展、学术研究及英语翻译进行了全面梳理,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伊氏在对比分析孟姜女故事的文献时,指出歌仔册《姜女歌》中的灵幡等书写可能源自该故事在葬礼中表演,与灵魂升天仪式相关,姜女爱情又与闽南流行的爱情信仰——泗州佛相关,[34](P62-P63)他还将其与两湖地区丧鼓中的孟姜女唱本进行了对比。
说唱孟姜女故事之唱本较早者有1680年刊《佛说贞烈贤孝孟姜女长城宝卷》。之后在19世纪更是刊刻丰富,这些刊本孰前孰后学界向来观点不一。有学者认为,1868年版孟姜女唱本因与孟姜仙女宝卷(1854年刊本)唱词相同而断定前者源自后者。[35](P48-65)而伊氏则敏锐地指出,现存最早版本不一定反映大众文学领域中的起源日期,或许宝卷抄袭借鉴前者也未可知。
[34](P80)同年,伊氏还翻译了宝卷中的两个唱本《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宝卷》(PersonalSalvationandFilialPiety:TwoPreciousScrollNarrativesofGuanyinandherAcolytes)。2009年翻译《董永与织女》,2010年翻译《梁山伯与祝英台》。此外,他还翻译了台湾歌仔册《台湾文学:英译系列》(TaiwanLiterature,EnglishTranslationSeries,2013)。近些年,伊维德先生对民间说唱中的动物主题颇多关注。[36](P469-489)诚如学者所云,伊维德是翻译中国说唱文学最多的西方学者。[37]
包公故事是中国流传极广的通俗文学类型。其故事文本中所呈现之法律意识、规则想象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极佳园地,海外学者如韩南等对包公文学颇多关注。学者在研究包公故事与公案题材时,较多着墨于元杂剧、明代白话小说、清代侠义小说。[38]伊维德则将包公故事中的说唱词话作为选本进行编译,体现出独到的学术视野。2010年,他将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包公唱本《包待制出身传》《包龙图陈州粜米传》《仁宗认母传》《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包龙图断白虎精传》等译成英文《包公与法律规则:八种明代说唱词话》(JudgeBaoandtheRuleofLaw:EightBallad?StoriesfromthePeriod1250-1450)。该选本以朱一玄编《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为主要中文依据。《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将明代刊本中已经遗失或不清的字迹以方格表示,这对于伊氏翻译颇具挑战。英译中伊氏用英文将其全文补足,并以括弧标注,因此该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译者的创造性与文化解读。
该书的序言将包公故事之渊源分流、包公文化与法治的文本呈现、说唱在包公故事传统中的地位等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篇长长的序言已然不是简单地编选介绍与故事梗概,而是深入分析包公叙事与规则意识的研究大作。北宋名臣包拯(999-1062)在正史中的记载与民间的叙事颇多出入。宋室南渡后,艺人将包公说唱传至杭州等地。元杂剧《鲁斋郎》等逐渐形成了包公在大众传播中的文学形象。一些学者认为,元杂剧包公戏反映了元代文人的“反蒙意识”,实际上这些文本在明代演出前被大大修改,臧懋循的元曲选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元代舞台上的包公形象?循此思路,伊氏指出,大量学者关注包公戏剧、小说,也有人关注词话中的其他故事如关索,却对词话中的包公关注不够。[39](pix)这些词话横扫两个多世纪(13-15世纪),与明代晚期刊刻的小说《百家公案》及包公杂剧呈现出不同的民间趣味。
伊氏指出词话中有关法律规则叙述的4个特征:一是包公与皇室的法律冲突;二是凶杀案件的被害者多为商人;三是神话色彩浓厚的转世与神灵审判;四是包公的多位重量级保证人使其审案有更多的制度保障。有些观点已见于其他学者的论述,[40]其中第一个特征颇值得关注。伊维德对词话与戏剧中的包公故事进行了认真比对甄别。如“陈州粜米”两个文本差别较大。词话开篇出现的重要人物是皇帝宋仁宗,去陈州粜米的是4个皇亲国戚,因这4人腐败而致民怨沸腾,当地百姓至皇宫“告状”。
在杂剧中皇帝根本没出现,而是范仲淹、韩琦、吕夷简等阁臣一起商量派谁去粜米,从而引出刘衙内之子与婿两个贪官。皇亲犯罪与官员子弟犯罪自然呈现对犯罪主体身份的不同认知。伊氏对比后指出,在词话中包公与皇帝及皇室成员的冲突是一个重要主题,他坚持法律与机构对皇帝和臣民一样重要。包公词话开篇都会颂扬圣明如“喜得太平无事日,风调雨顺国安宁”。[41](P126)但是,包公只有在犯罪伏法与惩罚恶人时才会证明其能力,这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矛盾与张力。伊氏认为这证明皇帝的美德也无法抑制臣民之贪欲。在杂剧小说中包公是王权的工具,在词话中,包公的主要敌人是皇室成员。[39](pix)
五、结论
近些年海外学界对中国说唱文学的研究在学术分类、研究方法及学理思路等层面多有深化与丰富。其特点主要有二:第一,随着文化理论的丰富而研究渐趋深入。如“口头传统”“性别文化”“大众文化”“族群认同”等理论运用于说唱文学的类型研究与文本分析,彰显出海外学者得理论研究风气之先的学术风范。第二,说唱文学选本与译本逐渐增多,且有明确的学理思路与分类标准。海外学者的研究与方法逐渐对国内学者产生影响,这种相互间之思想碰撞、学术批评可以增进更广泛的学术对话,重新认知与建构精英与庶民共存、经典与民间共生的中国文学史框架。且对于中国说唱文学学科体系之建立、中华文化之多元传播洵为重要。
17世纪德国学界巨擘莱布尼茨在罗马见到了在华耶稣会士闵明我,从此对中华文明之向往流溢于楮墨之间:“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Tschina。我认为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也许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距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他们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合乎理性的生活。”[42](P1)如今,这种文化的碰撞不再仅限于瓷器与丝绸等器物,而是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文本触摸与深度研究。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2191.html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