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 要:小说对历史风貌的展现,主要体现在对富有历史印记的意象选择上。 满族作家雪静的《旗袍》关注的是慰安妇问题,女主人公李曼姝勇敢地讲出慰安妇经历,指认侵华日军暴行,保护了历史建筑八角楼,与她再度穿上旗袍互文,迸发出与民族精神关联的美感。 作
摘 要:小说对历史风貌的展现,主要体现在对富有历史印记的意象选择上。 满族作家雪静的《旗袍》关注的是慰安妇问题,女主人公李曼姝勇敢地讲出慰安妇经历,指认侵华日军暴行,保护了历史建筑“八角楼”,与她再度穿上旗袍“互文”,迸发出与民族精神关联的美感。 作品敢于对当下种种负面的社会现实做出强有力的批判,彰显了女性作家强烈的身份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小说结构独特,构建了两个时空; 两个空间相隔遥远,却又在“八角楼”这一时空结合体中交汇。 作品使用“回忆录”讲述方式,正好契合“慰安妇”问题在抗战与当下的“对照”语境中展开。
关键词:雪静; 《旗袍》; 满族文化; 慰安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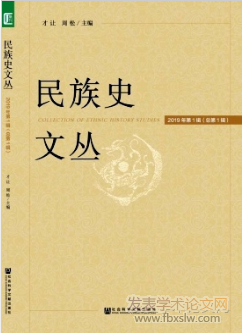
小说中的历史书写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较为常见,已成为观察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在当代满族作家笔下尤为普遍。 当代满族作家赵大年(《公主的女儿》《西三旗》)、叶广芩(《采桑子》《状元媒》)、朱春雨(《血菩提》)、雪静(《旗袍》)的作品中都倾向于通过历史书写来展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内蕴。 雪静(1960-)迄今出版了《梦屋》《夫人们》《粉领》等十余部长篇小说,对女性命运进行了独立思考。 [1]雪静作品一直受到评论关注。 ①《旗袍》关注的是慰安妇问题,由于横跨抗战及当代两个时段,又注入了更多的满族历史与文化,因此在雪静的作品中更具复杂性。 以《旗袍》为观察点,可以发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品在历史、性别、民族对接与文本建构的贡献。
一
从《旗袍》命名可以看出,雪静极为重视“旗袍”意象,而此意象也必然隐含着解读作品的密码。 旗袍由满族服饰发展而来②,后成为“国粹”。 《旗袍》中,由于涉及到抗战期间的国族问题,因此旗袍就带有民族认同色彩。 上世纪三十年代,满族格格叶玉儿在仆人哈哥庇护下,从伪满洲国日本人的魔掌逃出。 后哈哥被射杀,她被日军所掳,沦为“八角楼”的慰安妇。 在“八角楼”与日军抗争过程中,遭到了以吉野为首的日军的变态报复。
叶玉儿受尽屈辱蹂躏后,侥幸逃离“八角楼”,流落韩国,并改名李曼姝,努力忘记曾经的噩梦。 新世纪,80多岁的李曼姝回国,却面临是否讲出这段遭遇的抉择。 抗战期间涉及“慰安妇”的作品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秋子》都具有巨大影响。 [2]当代文学中,直面“慰安妇”问题的作品不多,不愿揭开历史伤疤可能是原因之一。
雪静重新叙述这个题材时,将上世纪30年代日军侵华时的中国历史与本世纪初的中国现实相结合,在往昔与现实的双线结构中追溯历史。 《旗袍》中的李曼姝(即叶玉儿)形象,是以往文学史中不曾有过的典型。 以往涉及抗战期间“慰安妇”题材的作品,各有不同重心。 《旗袍》追溯满族民族历史,发掘满族文化对李曼姝人生抉择的影响,独树一帜。 究其原因,除了作家满族身份,还有抗战期间形成的满族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伪满洲国)。 雪静本名高晶,满族,生于承德。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雪静的小说蕴含着一种民族依恋和民族反思之情。 《旗袍》传达的便是满族这一民族所崇尚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观。
雪静在小说中选择了满族文化与民族气节的代言者——旗袍。 类似隐喻,在当代小说中屡屡出现。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以玉器隐喻回族文化对忠贞、诚朴的追求。 [3]旗袍是满族的服饰,更是满族文化象征的一种遗存,小说以旗袍为题,可见其用意。 旗袍作为“中国女性的标志服装”,在小说中多次被提及。 不同颜色的旗袍与人物命运相结合,展现出不同处境中满族民族本性的自豪与自爱。 李曼姝对祖国的感情,体现在对旗袍的热爱中。 在抗争成为“八角楼”慰安妇的过程中,她拒绝穿日本和服,并以旗袍明志,认定“旗袍是满人的服装,具有中国女人的风情……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满族人”。 旗袍既是满族的文化象征,也是彰显中国女性民族气质的“国服”。
在日军的蹂躏下,她精神不曾屈服,铿锵有力地宣称:“碎了一件旗袍算什么? 碎了红旗袍,我还有绿旗袍黄旗袍蓝旗袍灰旗袍……我的哈哥给我做的旗袍够我穿一生一世了。 旗袍是我们满族女人的标志,它跟我们身体里的血液一样,世世代代流淌不息,没有谁能改变它的气味和颜色。 ”她对旗袍的热爱,贯穿一生。 多年后,年迈的李曼姝重归故国依旧十分动情地感慨:“我这一生最没穿够的衣服就是旗袍啊! ”可见,“她已经把穿旗袍上升到爱国的高度了”。 小说描写,她把穿旗袍作为了寻找自己的仪式:“李曼姝的情绪渐渐平静起来,她似乎更加明白了回来的目的。
她起身打开自己的行李,翻出一件旗袍,这么多年从未穿过的旗袍却让她窘迫地穿了起来,她站在穿衣镜前打量自己,微驼的后背,火鸡样起皱的脖子,再也没有穿它时的风采了。 可现在李曼姝是为自己穿旗袍,而不是为别人穿旗袍。 ”同样,女记者郭婧也通过旗袍感知女性之美与魅。 郭婧为了保护承载历史记忆的“八角楼”,勇敢站出来,支持李曼姝,“为了八角楼,我失去了总编的赏识,失去了叶奕雄的爱,但我不后悔”。 可以说,《旗袍》讲述的是两个女性的壮举,她们捍卫了女性的尊严与民族记忆,并因此美丽焕发,熠熠生辉。
李曼姝不再遮蔽,勇敢地讲出慰安妇经历,指认侵华日军暴行,保护了历史建筑“八角楼”,与她再度穿上旗袍“互文”,迸发出与民族精神关联的美感。 一段尘封的历史,重见天日。 可以说,小说对历史风貌的展现,主要体现在对富有历史印记的意象选择上。 作品中,雪静一方面通过描写现存历史遗址来表现现实生活,另一方面运用具有鲜明满族民族特色元素的历史意象来唤起满族民族身份认同的意识。 李曼姝的经历是文本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这段历史中既有泪痕血泊,又有家国仇恨。 《旗袍》借助旗袍的隐喻,彰显出女性的勇敢与奋不顾身,使历史叙述带有了民族文化印记。
二
与“旗袍”类似,“八角楼”也是《旗袍》的关键词。 “八角楼”在《旗袍》中不是普通地名,而是承载了历史记忆,并对今天产生冲击的“文化现场”,甚至是不同“话语”的交战场所。 “八角楼”是罪恶的渊薮。 李曼姝就是在“八角楼”被迫当慰安妇,这是“扒了皮我也认识它的骨头”的地方。 “八角楼”所携带的记忆,到了当代却受到质疑,并且遭遇到可能被拆除的命运。 《旗袍》的多重意蕴体现在文化“重建”,尤其是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历史遗产的继承。 与其他作品不同,《旗袍》选取的“文化触点”更具有话题度。 “八角楼”所蕴含的,是一段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沉重记忆,但惟其如是,才需要保存。 雪静在作品中的议论直击痛点:“八角楼慰安馆就是侵华日军肆虐本城的最好证明。
在大规模的城市建筑中,往往会忽略历史的痕迹,尤其是一些带来耻辱的历史,人们大多不愿提及,甚至想从记忆的深处抹去,但人们并不知道抹去的不单单是历史,还有历史对后人的提醒,而一个不愿意回忆历史的民族是绝对没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往往是后人的一种参照。 ”无疑,历史是绝不能被遗忘的,尤其是二战的历史,追忆历史是为了警示当下。 “慰安妇”抗战记忆与历史文物保护,似乎不搭的两个话题,神奇地“撞击”到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 《旗袍》郑重提醒:“如果为了世俗的利益就放弃历史,放弃对历史的审视,悲剧很可能重演,灾难很可能让人类重温。
”对历史真实性的思考与对当下现实世界的关注,都是作者基于自身体验所体现出的历史观。 从另外角度而言,“八角楼”是抗战历史,也是满族与中华民族受辱与不屈不挠反抗的象征,因而,它的存在意义,可想而知。 但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现实利益又驱动满族后裔叶奕雄毁坏“八角楼”。 “八角楼”的存亡,直接体现“历史真实”与现实利益的交锋。 而故事的满族背景,则打开另一层解读空间。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雪静正是以自身民族边缘化的视角对满族文化逐渐消逝作出的深刻思考。
女记者郭婧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屈辱史而奋力保护“八角楼”; 以叶奕雄为代表的房地产开发商们,则觊觎“八角楼”“风水好”的地理位置。 “八角楼”在小说中是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铭记者,而围绕“八角楼”展开的故事情节更是小说文本的重要内容:悲戚的慰安妇,利益熏心的开发商,扑朔迷离的官场,真假难辨的情场,荡气回肠的爱国情怀,永不妥协的女记者……雪静在冷静严酷的书写中揭示了个人利欲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割裂与背离。 小说中的女记者郭婧,是连接八角楼历史与现实的重要人物,代表着作家理想。
为维护文化名城历史原貌,进而让国人不忘国耻,她“穷尽心思”地完成了对李曼姝的采访,最终揭露了“八角楼”作为慰安馆的真实性,证实了“八角楼”作为铭记历史的文物地位。 与郭婧相意见不同的是她的情人叶奕雄,他认为:“八角楼是招财的宝地,把这样具有商业气息、可以给本城带来经济利益的风水宝地弄成什么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的慰安馆,我看你们这些决策者脑子都有毛病了。 慰安妇本来就是中国的耻辱,也是本城的耻辱,你们还要把耻辱揭开来给当今的人看,你们是让当今的人学习战争的耻辱呢? 还是学习战争的残暴? ”在叶奕雄看来,八角楼是反映中国女性“丑”的象征,应该拆除并开发。
小说通过对叶奕雄常在手中把玩的“壶”意象的描写,传达出他作为满族贵族后代的身份。 但叶奕雄身上早已没有了对本民族根基文化的坚守,有的只是对利欲的追求。 在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大浪潮中,为攫取“八角楼”开发的暴利,他不惜与情人郭婧翻脸,甚至还去诱骗市长夫人。 通过李曼姝与叶奕雄两代满族贵族后裔对自身民族文化的不同态度,作品反映出满族人在时代转型中所表现出的多重价值追求,并对其民族文化变迁与民族心理演变的原因进行反思与探求。
在欲海纵横的社会转型期,对传统民族文化历史的传承与保护,是少数民族作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小说通过对“八角楼”“壶”等具有深意的历史意象的描写,不仅对满族文化进行审视,而且对整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失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同时,作品还暗含着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思索,两个喜爱旗袍的女性在历史追溯中相识相知,她们以一种坚韧的勇气和毅力,不仅敢于揭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块伤疤,而且还敢于对当下种种负面的社会的现实给与强有力的批判,彰显了女性作家强烈的身份意识与社会责任感。 而以叶奕雄为代表的势力,则只看现实利益,置历史文化于不顾,是文本批判对象。
从而,《旗袍》带有了反思批判的锋芒,尤其是对于忘记历史苦难,予以了严厉抨击。 一座城市的建设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明史。 “对于我们这座具有悠久历史内涵的城市来说,是历史内涵重要,还是商业利益更重要? ”“当历史的证据无法在世人的眼前呈现的时候,当今的人们靠什么去反思呢? ”雪静正是在历史文化与现实利益的双重拷问中,探讨人性,反思历史。 “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常常是荣辱史,敢于正视历史才符合辩证法”。
“八角楼”作为日本侵华的证据印记,一方面以一种传统价值观刻画着历史; 另一方面,在迅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又面临着多元价值的冲击。 在对历史的缅怀与现实的迷茫中,《旗袍》建立了历史书写的感伤情调。 而雪静对于历史现实的真实体验,正是对历史背景中下个体“人”的命运的关注与揭示,这种将个人与历史相融合的写作技巧,真实的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内核。 正如小说中所言:“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了,历史可以使人明智,不忘国耻就是牢记历史的教训,激发人们为民族奋斗的精神。
”雪静正是从自身民族身份出发,旨在重铸满族精神,在对满族历史的回溯中,既强调了满族文化的深厚性,又彰显了满族勇武的爱国情怀。 在雪静看来,郭婧“就像堂吉诃德一样,用自己单薄的身体去撼动城市建设的风车”,是一位带有悲剧感的英雄。 同时,作为一名女性作家,雪静对女性在心理情感上的探讨也揭示了满族女性的智慧、柔美与坚韧的品格,她们如婀娜精美的旗袍一样,“最有满族人的风韵,那斜衩开的襟子,就像拉满的弓箭”,是满族文化中最美的精神内核。
雪静对历史的观照多源于她对现实的质问与思考。 在《旗袍》中,她将个体的精神演变与时代的欲望相交织,在个体与历史的对话中,突出当下的现实存在。 “当今中国,经济腾飞。 城市的发展注定寸土必争,黄金地段的老建筑常会在经济利益的权衡之下沦为商业的牺牲品。 而对过去的保留,就是对现在的肯定,对未来的展望。 一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光明前景的城市才是我们心中理想的城市。
”关照现实才是《旗袍》的旨归。 雪静小说中的现实意识重在凸显个体生命的价值。 “文学和写作也一样,如果不能构成对生命、对存在、对自身处境的超越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意义。 ”[4]雪静的现实反思主要表现在她对社会转型时期“物欲至上”价值取向的揭示。 小说中的叶奕雄同样是满族贵族,但却以自身利益至上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在他的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始终的个人欲望,而不是日本侵华这样的主流历史。 这一方面消解了小说的宏大叙事,让个人欲望及其追求成为塑造人物形象及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又揭示了21世纪初期社会中兴起的新价值追求,由此折射出个体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
三时空问题在写作中地位特殊,“时间强调历史内涵,故而作家可以通过对时间的操纵展示历史面貌; 空间强调历史背景,因此作家可以通过对空间的选择表现历史寓言。 ”[5]大规模时空变迁,必然带来历史对比,而抚今追昔,则具有“可阐释”意味。 《旗袍》使用“回忆录”讲述方式,正好契合“慰安妇”问题在抗战与当下的“对照”语境中展开。 小说结构独特,每章分为AB两节,构建了两个时空: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另一个则是六十余年后的21世纪初的中国。 两个空间相隔遥远,却又在“八角楼”这一时空结合体中交汇,揭开了“八角楼”作为屈辱的象征和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双重内涵。
《旗袍》中的时空建构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作者对小说时间的操纵,并由此来探寻作者讲故事的方式及其所理解的世界。 在雪静笔下,“历史——作为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现实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历史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题的和神秘的东西变成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 ”[6]178因此,历史虽是小说的主体,但个人心灵史才是小说最为重要的内容。
雪静将个体经验置身于历史中予以呈现,既让读者跟随时间线索感受历史的主体事件,又引领读者深入人物内心,参与人物内心记忆中的模糊性,从而使文本呈现出一种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文学内涵。 在《旗袍》中,雪静着重塑造个体生命在历史洪流中的内心世界,通过个体生命经验对历史的感知来勾勒历史,还原历史的真实,带有强烈的“叙述主观历史”的倾向。
《旗袍》以女记者郭婧的第一人称叙事展开,但对历史的讲述却是以她所采访的对象李曼姝的回忆为主。 “小说家介入历史,更重视个体,生命以及记忆的复杂内容,他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出于某种政治、时尚或道德的约束对这种内容进行简约。 ”[7]16《旗袍》通过年迈的李曼姝的记忆与叙述将八角楼的历史呈现出一种破碎感,也意味着时间和记忆对于历史真实性的不确定影响。
在此,作者一方面将宏大的历史事件消解于繁琐的日常生活中,突出个体在历史建构中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又有意打破时间顺序,通过复调叙事将现实与历史勾连起来,不仅在回忆中复现历史,而且还在时空对比中呈现不同人物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并通过这种不同时空的对比叙事来完善小说故事内容。
在雪静看来,“对比是人类最基本的思考方式,是叙事的基本结构,也是小说意义呈现的基本方式。 ”[8]109《旗袍》中的时空经营既包含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的“纵向对比”,也有同一时期人物的“横向对比”。 李曼姝与叶奕雄是“纵向对比”的典型,两代人都是贵族,有血缘之亲,但在面对民族文化及其历史过往时,一个敢于铭记历史,批判丑恶; 另一个则利益至上,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身份。 郭婧与叶奕雄是同一时期的“横向对比”,一个是利欲雄心的商人,一个坚守执着的记者。
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人物,价值观念相异,命运也不同。 无论是从逃避过去到敢于正视自己的李曼姝,还是执着坚定寻求真理的郭婧,亦或不择手段追求利欲的叶奕雄,他们都在个人的独特经历中阐述着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体现了人物在不同历史空间中的价值追求。 而小说正是通过这种对比手法来凸显《旗袍》历史书写中的时空观,并对“八角楼”作为“慰安馆”这一历史事件进行揭露与批判。
文学中的空间建构在文学叙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不仅是小说故事场景的地域、历史、民族、文化的积淀,而且还是作者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空间相比,文学中的空间“通过一种诗学的过程获得了情感甚至理智,这样,本来是中性的或空白的空间就对我们产生了意义。 ”[9]68可见,小说中的空间叙事也是表现小说主题,揭示小说思想内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一名具有深厚民族意识的作家,雪静对于小说空间的选取也颇有深意。 这与她的创作动机、内心作用密切相关。 作家的艺术创作动机往往都是“社会的、非个人的。 它们既来自环境,也来自艺术家独特的人格。
艺术家的人格,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教养、趣味和风尚的烙印,打上了他所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制度的烙印,有时甚至打上了他本国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的烙印。 但是,除了上面这些强烈地影响艺术家的外界影响之外,还有心理的力量在他头脑中起作用。 ”[10]186作为一名满族小说家,雪静身上流淌着满族这个独特少数民族的灿烂文化与深厚民族历史的骨血。 虽然社会不断发展,但雪静骨子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结却并未消减。 她以少数民族身份与女性身份两重维度来构建文本的历史时空,书写属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小说文本,使其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与文学内涵。
当然,《旗袍》中的时空建构不仅局限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21世纪初两个时间性的平面历史中,也不只单纯体现在八角楼、官场等场景的空间变换中,而是立体的将不同时代的人物与历史相结合,体现了历史文化的厚重,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雪静将历史的线性时间与人物心理时间相交织,拓宽了小说的叙事艺术,使小说的历史叙事超越过去,并与当下整合,形成一种广阔的审美境界。
民族文化方向论文范例:高位推动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四
面对社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文明的冲击,传统文化的阵地正逐渐失守。 这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尤甚。 作为满族作家,雪静通过文本的历史书写方式来,促使读者不断提升传统文化意识,进而缓解传统文化与当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而传统价值观的失落是她所忧思的重要内容。 《旗袍》是雪静基于对日本侵华历史的批判和对经济至上的现实反思而创作的,是她在历史洪流中对于现实生存与价值取向的思索,蕴含着作者深刻的历史情怀与现实拷问。 在小说中,雪静试图寻求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她对历史的批判与现实反思深沉而悲悯。 但小说是对内心的勘探,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这一直是小说的重量之所在。
[11]因此,她并未一直沉溺于历史书写,而是将历史与当下衔接,以个体的空间体验为主线,并将个体置身于历史空间中,既延续了时间与记忆,又表现了自我与现实,在扩大小说叙事空间的同时,为作品呈现一种悲壮的历史文化氛围。 《旗袍》主题关涉的内容颇多,主次、进退、显隐不容易拿捏,因此,人物只能“标签化”。 即便如此,仍然可以说,雪静的《旗袍》完成了她作为一名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肯定与传承的责任与使命,无论在叙事空间还是小说主题上都为少数民族文学实践开拓了视野,并对满族文化的发展之路进行了探索,体现了她对于本民族历史现实的独特思考。
参考文献:
[1]雪静.作家要保持独立的精神空间[N].文学报,2009-06-27.
[2]王学振.文学中的慰安妇题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2,(4).
[3]张世维.浅析《穆斯林的葬礼》中玉器对情节的推动[J].镇江高专学报,2015,(2).
[4]张学昕.文学叙事是对生命和存在的超越[J].当代作家评论.2009,(5).
[5]王俊.《蘑菇圈》的历史书写[J].阿来研究,2018,(2).
[6]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前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格非.塞壬的歌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8]王新新.对比:一种小说解构的探讨[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9,(5).
[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0]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社,2004.
作者:王明娟1 王晓燕2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4806.html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