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纪昀站在文体纯洁性的立场上讥讽《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然而随着时代推移,此语多被后人借以概括《聊斋志异》兼熔两重文体的写作特色。 纵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可以发现,其中部分篇目将史传文学色彩与非虚构叙事手法整合为一。 通过对具体
摘要:纪昀站在文体纯洁性的立场上讥讽《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然而随着时代推移,此语多被后人借以概括《聊斋志异》兼熔两重文体的写作特色。 纵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可以发现,其中部分篇目将史传文学色彩与非虚构叙事手法整合为一。 通过对具体作品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蒲翁在叙事策略、叙事时间线、叙事视角以及相关的论赞品评等方面颇有史家风范。 具体来说,蒲氏善于利用取材于真人真事的事件,融入作家的文学想象,既以事为本、于史有征,又由正而奇、由文而幻。 从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特点出发阅读《聊斋志异》,可以对 “一书而兼二体”之说阐发新见。
关键词:聊斋志异; 一书而兼二体; 史传文学; 非虚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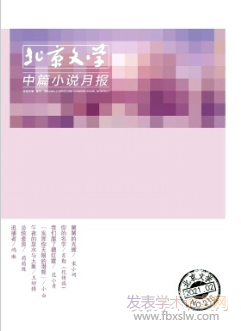
一、引言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问题,向来众说纷纭、人言人异。 自唐朝起便有学者认为小说缘起于史传,《新唐书·艺文志》:“传记、小说、外暨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 ” [1]935嗣后,刘知几对文言小说进行分类,并指出“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 [2]253胡应麟同样认为某些小说“纪述事迹,或通于史; 又有类志传者”。 小说缘起史传之说虽然存在着因材料缺乏而难以确证其完全真实性的问题,但纵观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轨迹可以发现,这一文体带有很强的史传文学特色,特别是早期小说的“志人”“志怪”内容更是如此。
史学方向评职知识:史学论文如何发表正规
作者:周琦玥
随着文学自觉的增强与作者对创作技法的追求,加之文学创作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日臻完善,其史传文学色彩逐步淡去。 但后世仍有部分作品自觉赓续了这样的特色,《聊斋志异》便是如此。 蒲松龄充分借鉴和继承史传文学传统,并在其基础上融入诸多文学想象的成分,恰如孙锡嘏所言:“文理从《左》《国》《史》《汉》《庄》《列》《荀》《扬》得来。 而窥其大旨要皆本《春秋》彰善瘅恶,期有功于名教而正,并非抱不羁之才,而第以鬼狐仙怪,自抒其悲愤已也。 ”
[3]602除却文理上对前代史传作品的效仿,蒲松龄以“异史氏”自称,对文中所涉人物、事件的品评,与司马迁以“太史公曰”形式的论赞也颇为相类。 这样的处理方式继承了史传文学的评论传统,在体例上因袭史书风格,正所谓“此书即史家列传体也,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 [3]587
蒲松龄这样的写作方式也招致了一定的非议,其文体上的杂糅性特质更是为纪昀所诟病,《阅微草堂笔记》对《聊斋志异》评论便涉及到对“一书而兼二体”特色的暗讽: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 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 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 《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 《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 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 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 伶玄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 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 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 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 使出自言,似无此理; 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 又所未解也。 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4]408
纪昀的批评乃是从文体纯洁性的立场与视角所发,所谓“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 《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的深层含义,乃是严格区分以“志怪搜异”为要旨的“小说”和以“述往事,追来者”为旨归的“传记”。 具体考论其批评,核心观点在于认为《聊斋志异》文体不纯,其中不仅有类似于《搜神记》的简略叙述,也有篇幅较长类似于古代传奇故事。 所以《聊斋志异》既是“笔记体”,又是“传奇体”,进而导致“使出自言,似无此理; 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的内部矛盾。 纪昀此说应和者颇尠,“一书而兼二体”之语虽为后人广为引用,但此言原本所带有的暗讽意味渐已减弱,变为单纯的叙述文辞。
前人对《聊斋志异》叙述特色的考察,多集中于蒲松龄创作过程中对史传文学手法的继承,以及该书“笔记体”与“传奇体”二者得兼的艺术特色。 然而纵观《聊斋志异》近五百篇故事我们发现,作为文言小说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所收录的众多作品体例不尽相同,既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融入文学想象所撰成的带有史传文学特点的作品,又有切近历史真实、以白描手法详尽记载虽看似奇诡但却实有其事的非虚构写作。 选取相关篇目予以厘析,可以廓清《聊斋志异》中两类不同创作倾向下创造的叙事成果,进而为“一书兼二体”的成说提供新读解,也为《聊斋志异》叙事学特色的多样阐释提供新的可能。
二、既有史实,杂以想象:《聊斋志异》部分篇目的史传文学特色
极尽推崇史学叙事,将其提升到“六经皆史”高度的章实斋,以“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之语为历史著作叙事方法对古文辞之术的影响作了绝佳注脚。 [5]767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影响,绝不裹足于提供创作所需的人物、情节、环境等素材,更因其记叙层面的成熟为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 此外,史传虽是叙述历史事实的“写远”之作,但并不排斥“追虚”,也即合理想象的熔铸。 刘勰曾指出“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 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 [6]151,“伟其事”“详其迹”的重要材料来源,便是民间传说、作者想象等与“秉笔直书”“董狐之笔”不同的文学想象成分。 恰如钱钟书所言:“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庶几入情合理。 ” [7]272-273柯林武德对史家的这种有意为之评论道:“正是这种活动(有意虚构)沟通了我们的权威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之间的裂隙,赋给了历史的叙述或描写以它的连续性。 ” [8]1133除却补上历史著述中受制于材料欠缺而形成的阙环之外,这种以史为据,但又杂有文学趣味和入情合理想象的创作范式,也使得史传文学作为特殊文体具有了发生、发展的土壤,成为一支不容小觑的文学力量,为尘封既久的“青史”带上了一抹文学的色彩与温度。 这也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带来重要影响,小说作者往往以“稗官野史”自称,即使是以“花样全翻旧稗官”作为自我标榜的著作,仍是在“旧稗官”基础上的“新翻”。 因此“野史”的“史”内涵,是小说作家无法规避,也不可能彻底割裂的文化资源,更不乏自觉将史书特色与文学意趣融为一炉的小说出现。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中深受前代史籍影响,将“史官式”技巧与创作实践相融合。 蒲松龄选择部分与真实存在的事件与人物有关的材料作为创作蓝本,而在进行叙述时融入虚构笔法进行类似于史传文学的“虚实相生”叙事,继承了史传的虚构艺术,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尚奇”叙事风格,于“狐鬼花妖”之作中“钩爪锯牙,自成锋颖”,达到了文言小说的新高度。 恰如蒲立德称《聊斋志异》一书:“其事多涉于神怪; 其体仿历代志传; 其论赞或触时感事,而以劝以惩; 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 其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俾畸人滞魄,山魈野魅,各出其情状,而无所遁隐。 ” [3]578
(一)线性叙事时间与全知叙事视角
“史传孕育了小说文体,小说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如果不顾及它与史传的关系,那就不可能深得中国小说的壺奥。 史传所包含的小说文体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传统。 ” [9]67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源头的史传文学,在文笔技巧上对后世小说家创作的影响自不待言,模仿《史记》《国语》等文法笔法特色从事小说创作者甚夥。 在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方面中,史传文学的叙事方式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最为明显,也最为深远,这与史传作品在叙事性上达到的高度密不可分,“史传乃是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真正渊薮,中国古代的叙事艺术最集中地表现于古史之中”。 [10]33具体到《聊斋志异》论,其中叙事时间序列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便明显带有继承史传作品的特点,对史传作品“深明体裁作法者”阅读到相关篇目时,自会“方知其妙”,可见清人便已以曲笔点明《聊斋志异》与前代史传作品的深层次关联。
史书的创作目的在于“写远追虚”,因此最常见的叙事时间序列是按照时间发展忠实记录历史事件的线性顺序,正所谓“叙事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时间则是立体的。 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的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线上”。 [11]506《聊斋志异》的诸多篇目中,以线性时间链条作为叙事依傍者为其大端。 虽然以时间先后串联事件发生关键节点的写作方式在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不乏先例,但多为长篇世情小说所用,且往往掺杂有多条并行不悖甚至相互龃龉的时间线,如《金瓶梅》的“多事并举”、《红楼梦》的“时序倒流”等。 但《聊斋志异》的叙事特点却与此不同,极尽谨严。 蒲松龄十分重视叙述故事的始末由来,相当篇目对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的叙述严格按照时间推移顺序,展现出完整、详尽的线性时间链移。 这种以时为序的写作方法与正史中的列传,以及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写作方式颇为相类,有如史家著述,可谓是《聊斋志异》受到史传文学影响的外在表现之一。
《祝翁》开篇简练点出祝翁姓氏、里籍和年岁,五十有余便已离世,进而说明其“死而复生”的原因:“我适去,拚不复返。 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 故复归,欲偕尔同行也。 ” [12]86将此篇立意托出,祝翁心系妻子不忍其独身过活,然而此举却得到“媪笑不去”“媳女皆匿笑”“家人又共笑之”的反应,衬托此事的荒唐。 而后老媪携手祝翁离世,这也是作者叙述最为详尽之处:“媪笑容忽敛,又渐而两眸俱合,久之无声,俨如睡去。 众始近视,则肤已冰而鼻无息矣。 ”在数句之中运用大量诸如“忽”“渐而”“久之”“始”“已”等表示时间顺序的词语,文中其他地方还曾使用“又促之”“俄视”等字眼串联情节,使得全文顺序了然,最后又以“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之句作结,既增加了该事件的真实性,又为这一故事提供了长时间段上的节点作为参照。 这样的叙事方式以时间线串联起故事的因果逻辑,整体结构明晰,而在重点观照的主要事件发展与结果之处更是条理井然、援事随时,与史书的记事方法高度一致。
除却时间视角选择上深受史传文学影响外,《聊斋志异》的叙事角度选择也颇可玩味。 石昌渝先生指出,以《左传》《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叙事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传统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 [9]69-72实际上采用全知叙事视角乃是各民族历史叙事作品的共性特征,各类英雄史诗的叙述模式也往往采用这样的方法。 这与历史叙事本身对清晰勾勒历史事件、使读者或听者身临其境的要求,以及作为讲述者的叙事主体采用较为客观的叙事立场、游离于事件之外、在叙述过程中尽可能较少干预事件发展的超然地位密切相关。 《聊斋志异》在讲述客观事件时也是如此,作为作者的蒲松龄采用全知角度,从全知视角出发对各类事件予以叙述。 如《聊斋志异》中的各类狐鬼花妖,在叙述的开篇便已经明确点出其异于人类的特点,甚至在题目中便明确称其为“画皮”“庙鬼”“鬼令”,或称其事为“狐嫁女”“狐入瓶”,可以说除了文章主人公不知道自己乃是与鬼怪打交道外,讲述者和读者均已心知肚明。 而在叙述不带有灵异色彩的故事时,蒲松龄同样采用了这样的叙述方式。 如《黄将军》一篇中,仅用不足百字之文叙述黄将军之勇猛:“黄怒甚,手无寸乒,即以两手握骡足,举而投之。 贼不及防,马倒人堕。 黄拳之臂断,搜索而归。 ”对黄将军的描写仿佛置身于战场上空,以俯视的角度冷眼旁观、如实记录古战场的场景。 又如《佟客》中开篇即讲董生“好击剑,每慷慨自负”,与下文与败于佟客却向他“按膝雄谈”,毫无谦逊之礼相应,开篇便对董生予以全面总括,也是作者全知视角的展现。 采用全知视角出发叙述事件,“可以带给叙述者极大的讲述自由,为其顺利建构文本话语系统提供便利”。 [13]321上承《史记》《左传》的《聊斋志异》所采用全知的叙事视角和客观的叙事立场,全面立体地展现出事件和人物的发展,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摹了引人入胜的事件经过,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作为叙事核心的人物形象与慎辨心术的“史笔道心”
“史传著作的叙述者,遵循的是‘无征不信’的实录原则,作者与叙述者基本是同一的。 被视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尽管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叙述者却总是以‘史官’的标准限定自己,按照历史的叙述法则进行着小说的叙述。 ” [14]11中国古代史书虽体例多元,但作为正统的乃是以人物为纲目和叙事核心,将事件系联于相应人物条目之下,围绕人物生平层层铺叙展的纪传体史籍。 不以人物为主要线索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虽然在外在结构上以时间、事件建构叙事框架,但构成历史事件内核的基本事实,仍然是相关人物在给定时间段或特定历史事件中的行为以及对历史进程发展的影响,严格说来仍是为人物立传,只不过是冠以其他形式的外壳。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作品,乃至受其影响的杂史、杂传,通常在开篇便以简明扼要的语句介绍主人公的姓名、身份、性格、家族、才艺等背景,进而刻画其生平重要事件,意在“借人以明史”。 这种“以人物为本位”的写作方法,既是“最异于前史者一事”,又对后代影响深远,“确立了以人物为本位的纪传体创作风范。 ” [15]15-16这样的写作方法为后世作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之一,后世小说作家往往模仿史家口吻撰述,其模仿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与描写作为主体,运用“为人物造像”的方法编联全书。
从《聊斋志异》的内容来看,其十分重视情节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和谐统一,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颇具匠心。 蒲松龄在叙述事件之时,每每在篇首介绍主人公“某生,籍贯某地、性情如何、行止如何、体貌如何”等等。 如“厍大有,字君实,汉中洋县人”“青州东香山之前,有周顺亭者,事母至孝”“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 豪爽,好施”等等,皆在开头前两句中托出主人公个人情况,凝练恰当,往往在后文便表述与其个人特色之事,将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妥帖自然。 而从《聊斋志异》的篇目命名看,很多篇目更是近于记事以状人的传记作品。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中以人名或官职作为篇名的作品达277篇之多,且不乏《王六郎》《劳山道士》《娇娜》《婴宁》《聂小倩》《林四娘》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可以说以人物为中心是蒲氏的创作基准之一,也是《聊斋志异》史传文学色彩的重要表现。
中国史传作品往往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圭臬,厘清“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所潜藏的历史规律,加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史家“心术”,以离析“因事生感”而导致“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亦或是“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的失衡。 [5]266进而“深入研究历史,更好地指导当下和主导未来”,发挥“史学,所以经世”的用世功能。 [16]从形而上的角度“用名教养气情”,以期为读者提供精神滋养,收获“益于人”之效,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入世之心的外化。 《聊斋志异》在创作中自觉将处世道理与训诫之意插入其中,恰似史官将历时进程规律、社会发展脉络纳入著述之中,这种融合方式珠联璧合,丝毫未见矫饰、牵强之感,堪称“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 《柳氏子》中开篇便将叙事写人重心转移到柳氏儿子身上:“胶州柳西川,法内史之主计仆也。 年四十余,生一子,溺爱甚至。 纵任之,惟恐拂。 既长,荡侈逾检,翁囊积为空。 ”而后刻画了柳氏溺爱孩子的形象,下文中既有从侧面众人之口“尊大人日切思慕”“众归,以情致翁”侧面反映柳氏爱子之心,又以“翁大哭”“柳涕泣”直面书写其思念之情。 然而返魂的柳氏子却言“彼是我何父! 初与义为客侣,不图包藏祸心,隐我血货,悍不还。 今愿得而甘心,何父之有”,将其与开头作者写柳氏溺爱儿子以致养成“荡侈逾检,暴虐成性”的性格,最终“翁囊积为空”相映照。 这样的写作方法将寓意囊括于柳氏与柳氏子的行为对比之中,点悟“为善者本为恶,为恶者原为善”的道理,可谓是在文学创作中以史笔点明“道心”。 《聊斋志异》虽为“小说家言”,难以木铎席珍作比,但仍可收“晓生民之耳目”之效,高扬史传作品的匡世功能。
(三)“由正而奇”的虚实关系与“由文而幻”的艺术特色
《聊斋志异》中部分本有其事的故事,在具体情节上又融入了部分虚构成分,加入了文学创作色彩。 这种“以实对虚,以拙对巧”的创作方式,与《左传》《史记》中的叙事风格颇为相类,都是以文学想象填补诸多细节,增益其所未有,既有写实的成分,又有根植于写实之上“由正而奇”的虚构情节,形成虚实相映的别样虚实关系,收获了“由文而幻”的艺术特色。
《王司马》一篇中的镇边将军王象乾,巧借木刀贴上银箔,假装是“阔盈尺,重百钩”无人能举起的大刀,故意在敌军面前挥舞以迷惑对方,收到“诸部落望见,无不震惊”之效。 此外作者还描述了王将军引得敌军焚烧苇墙,并在此设下伏兵,最终“北兵焚薄,药石尽发,死伤甚众”一事。 王象乾为明代能臣,曾任大总督、兵部尚书,史称“居边镇二十年,始终以抚西部成功名”,其机警智谋可见一斑。 但蒲氏所记载的这两则简短小事在《明史》《山东通志》《新城县志》等史志中均未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象乾家乡的《新城县志》记载其事甚详,却未提及这样的说法,这就颇令人怀疑,蒲松龄此处记载的文献来源甚至有可能连所谓“民间传说”都不是,而是赖于作者想象的发挥。 此外,明代的军制乃是“以文治武”,作为军事文官的王象乾上阵挥舞大刀的情节也带有几分虚构色彩。 无论此处的记载来源于民间传说还是作者个人对其他小说情节的移植,甚至“无中生有”的艺术想象,都带有虚构写作的色彩。 但这些细节的填充不似官方正史一般佶屈聱牙,而是以其生动形象抓住了读者的目光,使民众易于接受,更是便于普通读者了解王将军之勇猛机警。
运用各类奇异现象杂于本有其事的叙述过程中,又杂以各类曲折离奇的情节以制造戏剧效果,乃是蒲松龄“由文而幻”,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重要手法。 如《阳武侯》在记录明朝大将薛禄逸事时,起首便刻画了其出生之际的奇遇:薛禄尚未出生时其父则地而居,见“蛇兔斗草莱中”,被风水先生视为“宅兆”。 降生时暴雨倾盆,又被躲雨的指挥说“(薛禄)是必极贵。 不然,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 ”然而随着薛禄的成长,读者并未见到其“极贵”,而是“侯既长,垢面垂鼻涕,殊不聪颖”,甚至“时侯十八岁,人以太憨生,无与为婚”,这与前文的异兆形成了鲜明对比。 及到薛禄后入军籍,“勇健非常,丰采顿异。 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又与前文相呼应。 但其后裔却又辛苦遭际,袭爵后的某公辞世后,薛家血脉一度遭人质疑,“应以嫡派赐爵,旁支噪之,以为非薛产”,最终“官收诸媪,械梏百端,皆无异言”,几经周折,“爵乃定”。 一波三折的情节叙述、虚实杂出的内容,使得薛禄故事充实而又高潮迭起,烘托出了其人的奇遇,丰满了薛公的传奇人物形象。 这样的写作方法将正史记载、民间传说与作者的文学想象完美融合,成为《聊斋志异》善于处理虚实关系以收“由文而幻”艺术特色的绝好样本。
“幻想实际上只不过是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秩序的拘束的一种回忆,它与我们称之为‘选抉’的那种意志的实践混在一起,并且被它修改。 但是,幻想与平常的记忆一样,必须从联想规律产生的现成的材料中获取素材。 ” [17]60-61前代史书所载提供给后世文人可以发挥的凭借,蒲松龄结合自己的创作理念与民间传闻,生发出丰富的文学想象。 这种在史实基础上填充想象成分的做法,来源于史传文学,而又被蒲松龄所高扬,最终在《聊斋志异》中收到引人入胜之效。
三、如实记述,颇具机巧:《聊斋志异》部分篇目的非虚构叙事特点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其作品《冷血》中最早尝试了“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把新闻报道的严肃真实与小说的艺术表达相结合,将一件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谋杀案经过真实且详细地调查记录下来。 这一尝试成为非虚构写作的发轫,自此小说家的写作技巧和客观报道的真实性相互融合,“出现了一种依靠故事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nonfiction)的形式”。 [18]6嗣后,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人进一步发展非虚构写作手法,通过作者对真事实事件亲力亲为地采访,或参与其中,从而获得大量的第一手素材,然后用文学的手法将这些素材编写成小说。 [19]68“非虚构小说”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在文学界也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文学”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线,如1986年王晖、南平在《当代文艺思潮》期刊上发表的《美国非虚构文学浪潮:背景与价值》一文中,定义了中国化的“非虚构文学”即“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和口述实录体(作品)”。 在此影响下张辛欣、桑晔所著《北京人——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便是典型的“口述实录体”作品。 但这一概念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较晚出现,并不意味着类似的实践前无所据,人物传记、游记散文、口述实录,乃至非虚构小说、报告文学、新新闻主义小说等所有以真实描述为写作手法的文类,虽然此前未被冠以“非虚构文学”之名,但这些写作实践中作者均自觉抑或不自觉地运用“小说精神、小说结构、小说语言、小说手段去写实”,“写地地道道有过存在过的人与事,情与景,时与地”,可谓是早期的作为写作实践而非理论建构的“非虚构文学”,也是这一创作理论的材料源泉。 “非虚构”的写作技巧不仅在欧美作家群中可以找到范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典型,《聊斋志异》的部分篇目便带有“非虚构”叙事特色。
《聊斋志异》作为文言小说集,其中的大多数篇目自然以“搜神博物,谈仙说鬼”作为重点,但其中存在部分篇目乃是蒲松龄小说家视角观照真实事件,并对其予以如实记述的作品。 所记述的内容有的是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如《山市》《地震》; 有的则是各类奇观异物、自然灾变,如《瓜异》《水灾》; 有的则是记述各类人物轶事,如《金世成》《杨千总》。 当然,这些分类并非判若经纬,部分篇目的内容实质上融合了其中的数种,如《地震》篇既记载了地震的事实,又将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融入其中。 这些以“非虚构”技巧写作的篇目数量较少,且其本身的体量也较小,加之这部分作品与“谈狐论鬼”的篇目或带有史传文学意味的虚实相生作品相较,由于“文人爱奇”这一客观存在的阅读偏好的影响,在读者的阅读趣味与阅读意愿上也不占优势。 长期以来这部分篇目并未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但实际上这类“非虚构”创作实践丰富了《聊斋志异》的叙事方法,也是蒲松龄对确有其事的历史事件书写的另一种异于“虚实相生”的史传文学叙事方法的尝试。
(一)与古史所载相合的真实记录
以“谈鬼说妖”著称于世的《聊斋志异》中,也不乏以确实可考的真人真事为蓝本进行的创作。 这部分内容有的杂以作者的文学想象,也即前文论及的具有史传文学底色的篇目。 但也有部分篇目并未杂以文学想象,而是忠实记录事件本身、以事为本,且通过与古史所载相互对照可以发现其“于史有征”,真实地记载了各类其人异事。
康熙七年,山东南部的郯城县发生了特大地震。 这次地震波及山东省内多地,就连远离震中的海阳、威海、诸城、日照等地也有震感,在当地史志、碑刻,以及诗文作品中多有记载。 《聊斋志异》中也记述了此事,作者“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此时“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地震时“几案摆簸,酒杯倾覆; 屋梁椽柱,错折有声”。 而纵观全文不难发现,作者对地震相关事件的记载并未杂以想象性成分,而是对本人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进行细致描摹:
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 屋梁椽柱,错折有声。 相顾失色。 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 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 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 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 河水倾发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 逾一时许,始稍定。 视街上,则男女裸体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
清代济南方志中对此处地震的记载较为简略,仅载其“七年夏六月十七日地震” [20],对当时的民众的反应和地震引发的后果缺乏具体描述。 而蒲氏则根据亲身经历,细致地描摹了相关事件,弥补了这一空白。
当然,《地震》篇中也杂有某些夸饰成分,如“后闻某处井倾侧,不可汲; 某家楼台南北易向; 栖霞山裂; 沂水陷穴,广数亩”的记载。 由所谓“后闻”可知,此处并非作者亲眼所见,乃是道听途说之语,野语乡谈往往与史实存在一定的疏离与偏差,因此这部分内容的真实性则是存疑的。 但总体来看,《地震》的主体内容仍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据,真实地记述了作者在地震中的所见,且文中描述准确可感,并有时间地点作为副证,具有极强的真实性。
此外,《聊斋志异》叙事中涉及到诸多人物,除却以“某甲”“某乙”等作为代称者之外,在史书中有记载或有相关典籍可查的真实人物也数量众多。 据王建平先生考察,其中所涉的非虚构人物达一百多人,不乏莱阳宋琬、巨野徐鸿儒、栖霞于七、长山李化熙、历城朱缃、高唐朱徽荫等广为时人所知者。 [21]26这些人物的相关记载往往记载翔实,保留了与之生平经历密切相关的第一手材料。 如《张贡生》篇,铸雪斋抄本的附记里记述了高西园对“张贡士”其人的探讨:“余素善安丘张卯君,意必其宗属也。 一日晤间问及,始知即卯君事。 ”这一附记指出张贡生即张卯君。 张卯君确有其人,即安丘张在辛,康熙二十五年拔贡,为郑簠及门弟子,“尝从郑簠学隶书,事周亮工传授印法”。 [22]125-126《张贡士》的内容虽看似荒诞不经,“忽见心头有小人出”,但考虑到“安丘张贡士,寝疾,仰卧床头”的背景,在病中看到异象也是不难理解的,并不能以之否认其真实性。 此外张在辛与蒲松龄为同时代人,且二人所居相去不远,这也可佐证蒲松龄对此人的记载当真实可信,这应是张氏亲身经历之事而非作者的艺术加工。
(二)《聊斋志异》部分篇目的方志特色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 ” [23]作为“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所述内容乃是将地方史料分门别类予以记述,使之成为地方史料的渊薮。 《聊斋志异》中的部分篇目以现实人物或事件为蓝本,除却上文曾论及的乃是“与古史所载相合的真实记录”外,还因其内容特点,以及往往发生于蒲松龄所居之地及其周边地区,带有某种方志特色。
《聊斋志异》中《水灾》一篇详尽地记载了康熙年间先旱后涝的自然灾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时间节点的细致描写:“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无青草。 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种粟者。 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种豆。 ”这种叙述不像小说的写作风格,反倒颇类方志中的“灾祥志”对一地自然灾害以及对农事影响的记述。 此类篇目虽然数量不多,但类型多元,往往与方志的相关门类相似。 如《地震》《水灾》《瓜异》《赤字》等篇目与中国古代方志中“灾祥”门类的相似,《丐僧》《番僧》《单道士》等记载僧侣、道士的种种奇方幻术的篇目与中国古代方志中“释道”门类的相似,乃至记载官员政绩的篇目、记载当时有名望之人轶事的篇目与中国古代方志中“宦迹”“儒林”等门类的关联等,均是蒲松龄着眼于地域文化,采择旧闻轶事而成。 胡泉在为《聊斋志异》所作的序言中盛赞蒲氏史才,认为“留仙公生擅仙才,锦在心而不竭; 异史氏文参史笔,绣出口而遂多”。 [3]592蒲松龄在创作中所带有的方志特色,以及对地方逸闻的重视与收录,既是其史才的表现,又因为客观真实地记载历史事件,将一时一地的各类历史真实囊括入《聊斋志异》之中,而丰富了该书的创作模式。 这种带有方志特色的篇目,也因其着眼于真实事件,却又杂有小说家的写作偏好与技巧,而带有“非虚构写作”的特点,成为《聊斋志异》收录诸多篇目中别具特色的内容。
四、结语
纪昀将文言小说的文体分为“小说”和“传记”,其著述之法则分别是“著书者之笔”和“才子之笔”。 “志怪小说只能叙述见闻,不能随意虚构; 而传奇小说可以细致描摹,驰骋想象。 ” [24]61这种文体上的杂糅特质也是《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特色为标榜文体纯洁性的纪昀所诟病的根源。 但实际上“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李善注此为“文章之体有万变之殊,众物之形无一定之量也”,《聊斋志异》在模糊文体泾渭的创作过程中却曲尽其妙,足见蒲松龄善于驾驭文字的功力。 这种“模糊文体泾渭”的表现之一,便是将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相交融,也构成了“一书而兼二体”的要件之一。 这种融合史传文学与非虚构叙事特色的成因,与《聊斋志异》的内容密切相关。 《聊斋志异》中与现实世界具有密切关联的作品,都有其叙事的事实基础,而由于蒲松龄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技巧与角度,这类作品又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发展方向。
取自真实事件,而又借由第一手素材融入部分文学想象的作品,对历史真实进行了文学化小说化的处理,基于事实加以虚构渲染。 这样的写作方法在中国古代史书中早有彰明:“《左传》、《史记》等史著并没有拘泥于史实,而是采用了踵事增华的叙事手法,也就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想像、虚构。 这样的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古代小说叙事就孕育自此。 ” [25]52这种将史实与文学想象融合为一的内容,在写作上沿袭史籍体例、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熟练运用史籍典故、在文末的论赞中臧否是非曲直,高扬史籍精神,也构成了《聊斋志异》中与现实关系密切篇目的史传文学底色。
蒲氏一生广为搜集奇闻异谈,除却在其基础上加以文学想象的作品外,还有部分素材被蒲松龄以白描的手法真实记录在《聊斋志异》中。 无论是对真人真事的记载,还是以“类方志”的写作方法真实地记录部分地域文化现象、奇人异事,都属于以小说家的视野与笔法对事件的客观描摹。 这种偏重叙事真实性而不添加或极少添加文学想象的作品则组成了《聊斋志异》的非虚构写作特点,展现了蒲松龄的另一种创作旨趣。
综合来看,无论是“史传文学底色”,还是“非虚构写作方法”,其创作的基本素材都是蒲松龄搜集到或亲身经历的各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或实践。 但又由于蒲松龄创作过程中的偏重不同,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 从这样的角度来观照《聊斋志异》中与现实相关的篇目,我们可以就“一书而兼二体”之论做出新的读解:所谓杂糅“小说”与“传记”,实质上是蒲松龄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着眼点,表现出不同的创作旨趣。 而《聊斋志异》中偏重于“小说”的内容,实质上是在“传记”的史实基础上进行的史传文学创作; 至于偏重于“传记”的篇目,则往往是一些故事情节性不强,或仅能作为奇闻予以如实描摹的奇事、异事,更多地带有“非虚构叙事”的色彩。
参考文献:
[1][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唐]刘知几.史通[M].浦起龙,注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
[5][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
[8][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4.
[10]董乃斌.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J].文学遗产,1987,(5).
[11][法]兹韦坦·托多罗夫.叙事作为话语[M]//伍鑫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3]尚继武.《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4]王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1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6]李钰.范学辉:深入研究历史,更好地指导当下和主导未来[J].山东大学报.2015,(26).
[17]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8][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M].北京: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19]高晓仙,赵国月.“非虚构文学”术语翻译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J].外国语文研究,2017,(5).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6039.html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璇峰~鍐欎俊鎭紝鍑轰功/涓撳埄/鍥藉唴澶�/涓嫳鏂�/鍏ㄥ绉戞湡鍒婃帹鑽愪笌鍙戣〃鎸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