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美国自白派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有一首诗,题为《当男人进入女人》,呈现了男女欢爱时的两帧镜像。为表述那妙不可言的瞬间,诗人两次以逻各斯显现为替代,暗示床笫动作推进到高潮与收束。逻各斯,人向无名之域不断命名试错的明证。这一用喻的出发点与乔治斯坦纳
美国自白派诗人安妮·塞克斯顿有一首诗,题为《当男人进入女人》,呈现了男女欢爱时的两帧镜像。为表述那妙不可言的瞬间,诗人两次以“逻各斯显现”为替代,暗示床笫动作推进到高潮与收束。“逻各斯”,人向无名之域不断命名试错的明证。这一用喻的出发点与乔治·斯坦纳称“爱是非理性的必要奇迹”同理,指出了我们情感事件中的神性之维,即人类语言四壁所难安置的部分。爱是人类智识的非理性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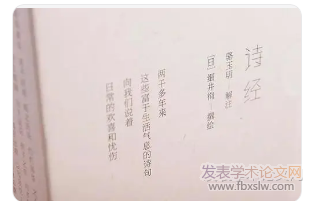
诗人安妮·卡森在其古典学研究首著《厄洛斯:苦甜》中开篇便叹“萨福是第一个把爱欲叫作‘苦甜’的,恋爱过的人谁能驳回”。萨福天然地将情爱的癫狂迷魅归咎于神谕的秘而不宣,开启了一种苦痛袭来以求解脱的张力诗学—“当我看到你,哪怕只有/一刹那,我已经/不能言语/舌头断裂,血管里奔流着细小的火焰/黑暗蒙住了我的双眼,/耳鼓狂敲/冷汗涔涔而下/我颤栗,脸色比春草惨绿/我虽生犹死,至少在我看来—/死亡正在步步紧逼”。
心意动荡,随即口齿无力自展,及至视觉熄灭、耳力失控、五体昏黑浑如被死亡摄取。这种在死生之轴上获取刻度的情感强力(它绝不是修辞术,而是实有发生)直到中世纪仍然适用—但丁在地狱第五层听了“被爱俘获的故事”后,“仿佛要死似的昏过去”,“像死尸一般倒下了”。从古希腊作品中,卡森还识别出“爱人—(受阻的)爱欲—被爱者”的位移关系,提出欲望的受阻反而是世间情事永葆盎然的要义:欲望被延缓、受阻滞,这令爱人者朝向被爱者终究是无法抵达的趋近。
这一过程恰似以智性揣度神意,或以语言趋向太一。在“苦甜”织造的引力之网中,我们体尝爱情节奏的骤变与焦点的挪移,用萨福的诗行来说:如果现在逃避,很快将追逐;如果现在拒绝,很快将施予;如果现在没有爱,爱很快就会流溢。这是西方情诗给人的第一印象,其中矗立着一个完整的希腊。只不过这个希腊远非我们所能在场。
就像伍尔夫盛赞“每个单词都充满生机,倾泻出橄榄树,神庙和年轻人的身体”,这些身体,我们是在石膏模型和博物馆走廊的大理石座上结识的。事实是,萨福情诗里那种相顾失色的惊怪,那种“虽生犹死”的萨满式的剖白,不可能从今人口中说出而不显得失态造作。正如伊格尔顿认为伊丽莎白·勃朗宁的十四行诗“对现代趣味来说太严肃、高尚了”,包括趣味在内的各个范畴总在发生变革。勃朗宁情诗底下笼罩着的教堂烛光、英格兰灰,以及由大写的“正义”(Right)和“赞美”(Praise)为尾音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激情,现在读来未免显得邈远、寡淡。这不是要把过去和当下对立起来。
事实是,一首诗纵使写自异时异地,也能以种种方式找到你。好诗理应是对现时与个例的超越,这方面,从密尔(JohnStuartMill)到波德莱尔到T.S.艾略特都有相 承性的论述,尽管角度有所偏差。他们的当代信徒、美国诗评家斯蒂芬妮·伯特声称,“读抒情诗就是为了发现跨越时空的人类情感的共性,无论多么雷同、多么主观”,因为“诗歌是感情的语言模型”,既然二十世纪的T.S.艾略特能被十七世纪的约翰·多恩打动,原因之一便是前者诗中的某些感情至今仍在。
T.S.艾略特倒未见得从抒情诗的角度立论,但他对艺术何以唤起共情有一个著名的推演:用艺术形式表现情感的唯一途径,是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要做到当那些最终必然是感官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那种情感。这是“情同此心”的慢动作分解。按照艾略特,当我们产生共鸣时,彼此内心状态的等值物是以“外部事实”—“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连串事件”—为中介来兑现的。这里的“外部事实”同写作时代或作家传记无涉,而是指内置于文本的叙事情境,也即后来新批评派在讲授一首诗时,要求投以细读的入门要素。在新批评派看来,一首诗的情感接应是否顺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情感所形诸的“外部事实”塑造得是否明晰、合宜。
后来,“艾略特-新批评”联盟遭到众所周知的抗辩。原因是人们意识到,诗歌的书面流传和视觉接受终会令诗人在“外部事实”中注入的语调变得暗哑,从而让寓居其间的情感扬抑遭到误读—这与新批评派自己提出需加以谨防的“情感谬误”与“意图谬误”并不相去甚远。如果跨时空共情的保值性不过是一个梦想,那么,我们在当代诗歌中收获的熨帖感是否就相对安全无虞?不论如何,有一点或许可以确定,“现代世界有它的依傍之物”(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语),在同时代诗人所提供的、比例更为适中的“外部事实”里,我们的关切与欢娱更易被可视可触可体味的事物所牵引。这方面,情诗尤是如此,因为情诗与我们的身体感觉最为关联。
当艾德丽安·里奇说“我与你同在……”而“莫扎特的g小调从录音机流出”时,无须转译,质地相同的乐声会亲手抚梳我们的心灵,带我们重返那个未曾移位的夜晚。同样地,当在丽泽·穆勒的诗中读到“你那悠长的,流畅动听的词语/像熟透了的牛油果”时,这样一个喻体会从我们的口腔吸入,溶解在双颚的后排。事实是,对一首情诗的理解必然在所有感官的联觉旋涡中完成,城市的落日可以目睹而汽车的啸动得以耳闻。如果阅读情诗时因过多的陌异感而停顿下来,那么,这种停顿是致命的。
词语在经验现实中寻猎,随时咬合其捕获物,这在情诗中尤为瞩目。美国当代诗人从惠特曼身上,保留了大规模列举事物的兴味、对自由律的偏爱以及使用情色语汇时的坦率。其中,《雅歌》那种对身体部位的扫描式称颂,由自白派与“垮掉一代”经手,已然成了一枚独属于“美式”的签章:……厚实紧凑的胸肌,乳头像崭新的硬币印在胸脯上,下面的肌肉扇子一样展开。我察看他的双臂,就像是用了一把刀沿着条条曲线镂刻而成的造型,三角肌,二头肌,三头肌,我几乎不敢相信他是人类—背阔肌,髋屈肌,臀肌,腓肠肌—如此完美的造物。
—金·阿多尼兹奥《三十一岁的恋人》似乎什么也无须克服,美国情诗的领地,天然就为身体感觉而划劈。肉体的私语与细响,在直露的日常生活体验中再度开口。基于广义的现实主义,诗人们无意于净化或参透,而是欲将情思的琐屑与生理分泌物的热味无损地还原。和惠特曼的异域继承者聂鲁达(布鲁姆语)一样,美国诗人写起爱情,用的也是舌、指尖、眼耳与鼻息。罗兰·巴特在谈及《恋人絮语》的写作本意时称,“恋人的表述并不是辩证发展的;它就像日历一般轮转不停,好似一部有关情感的专业全书”。
与此相仿,任何一种美国当代情诗选编,都有其重要的辞典学意义。这些独具美国特色的“工作坊诗歌”(workshoppoetry)整体上呈现为一种与中产阶级审美合谋的“内室叙事”(比利·科林斯写道:“我看不到千里之外的你,/但能听到/你在卧室里咳嗽/也听到你/把酒杯轻轻放在台桌上”),为种种情态所摆布的恋人们,仿佛总是落座在家中(书桌前、起居室、厨房或床上)、在可调节的室内光线下,将情感经验被词语转述出来的快慰分享给(同样在室内的)我们。这些内室叙事不仅搬演我们爱情的诸般欢乐、不幸、饥渴、溃败与狂喜,同时也是对当代城市生活语汇的集中编目。
比如,C.D.莱特以第一人称写道:“我会把双腿像一本书那样打开……我将像一本酒水单、一只青口贝那样打开”,当身体与消费品之间的界槛消失、相互唤来时,诸如“酒水单”和“青口贝”就迁入了新的意义居所;再如,在里奇那里我们读到,相爱的偶然性“就像车辆相撞,/就像书会改变我们,就像我们逐渐喜欢上/新近住进去的某些街区”,大城市的生活界面被唾手组合成情感表述的语义场。又如斯蒂芬·邓恩(StephenDunn)的温存回忆:“而我/当时所知道的/只是汽车的后座和睡袋/暗夜里偷偷摸摸的一晚两晚。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打趣和孤单/把我们引向一个共同的秘密”。暗色调的私人生活展示,重新编辑了语言对现实的抒情,将隐没在背光处的城市爱情常景调制成可能的感悟和灼见。
很显然,美国当代情诗有其切入当下的锐度与速率。在以知觉力为驱动的阅读过程中,感官自动完成了那种调适。每首诗都像是为你而写,未经引介就曾熟识、在布局无异的城市街区顶部将我们隔空捕获。如同美国文化制版的一份拓印,这些情诗复写着时代的肌理,它们展现了美国式的对各色人种与性取向的兼容并蓄、对情感的实用主义体悟,以及对日常物象的美化冲动。在讲述现代交通、品牌消费、技术更新和赛博媒介等对我们情感生活的重新定义:一只橘子,去皮,分成四瓣,盛开着就像威治伍德(Wedgwood)瓷盘上的一朵水仙什么都可能发生。
—丽塔·达弗《调情》“什么都可能发生”:一个正在叙述的恋人,成为我们内心语流的外化。他或她分享的信条是,所有的体验都是有价值的,无论巨细:陡然而发的性欲、让身体发疼的回想、显而易见长期容忍的谎言、剧情展演般的调情、异地恋难以饱餍的思慕、通信失联的懊恼、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仿佛同是一个“我”在产生、发展、流动、敞开;没有一个情境不值得描画,没有一个物件不该被展开度量。
这种细细逡巡的背后,饱含着对于每一个时间单位及其容纳的生命经验行将萎缩乃至熄灭的焦虑与忌惮。毕竟,生活结构于偶然与碎片,爱也即生即死,这或许是原子化时代下唯一恒常不变的真实。所以昂立·科尔在《眼睛泛红的自画像》中写道:“我曾喜欢每天/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小小的生和死。/甚至连你明亮的牙齿上的白色口水/都曾是爱的泡沫。”
梅洛·庞蒂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论塞尚:“对于这位画家而言,情绪只可能是一种,那就是陌生感,抒情也只可能是一种,那就是对存在不断重生的抒情。”在他看来,塞尚通过描绘日常物件来翻新联觉体验,这恰似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自我期许。画家不断拿起世界,如“陌生化”对材料的艺术安排那样,反复为静物和风景注入新的色彩、比例和阴影。这种塞尚式“陌生感”,即感知定式的变异,能引发知觉上的惊讶与震颤,是将逻各斯放逐远征的眩晕冲动。当珀涅罗珀牵起奥德修斯的手,并不是不让他走,而是要把这份安宁压印在他的记忆里:从今往后,你穿行而过的所有静默都是我的声音追赶着你。
文学论文范例: 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阅读体验探究
这是一番刻骨的情话。一个生命楔入另一个。也像诗行,找到了一只同情的耳朵—这是美国当代情诗所向往的实际处境:这些诗歌每每由一个可信任的言说主体引领着,通过现在时的讲述从我们身上贯穿、驻留、直到变为我们身上可携带的一部分。与前述诗人用语词捕获经验的努力互成镜像的是:到了阅读环节,读者将从诗中习得必要的语词,以备为自己的经验命名。或者是,阅读时因惺惺相惜而珍藏的句法,能够在未来某个经验降临时脱口而出。这或许是诗歌共情术所能引获的最好报偿。说到底,没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必须相信这些情话,然而我们还是相信了。
作者:张逸旻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jylw/28119.html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