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98年执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毫无疑问成为战争电影的里程碑。与其他传统的战争电影不同的是,斯皮尔伯格将反抗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发动战争的道德基石。大屠杀记忆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导演融入在电影叙事中,借此构建出更具
摘要: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98年执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毫无疑问成为战争电影的里程碑。与其他传统的战争电影不同的是,斯皮尔伯格将反抗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发动战争的道德基石。“大屠杀记忆”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导演融入在电影叙事中,借此构建出更具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身份认同。对《拯救大兵瑞恩》中唯一的犹太人角色梅利及关键场景的文本分析和解读,能够发现影片对纳粹大屠杀行动的“隐喻”和道德批判。导演将“大屠杀记忆”编织进电影情节中,通过描述战争的恐怖和牺牲引起观众对二战期间犹太人悲惨命运的反思。电影和其他媒体还推动了大屠杀记忆的“美国化”进程,借此构造民族身份认同。
关键词:拯救大兵瑞恩;大屠杀记忆;民族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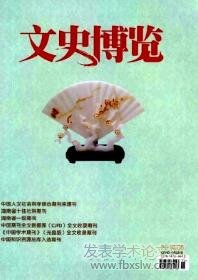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98年执导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毫无疑问成为战争电影的里程碑。它不仅取得了商业票房的巨大成功,在有关“二战”的文化记忆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念历史并重塑民众集体记忆,向战争中的牺牲者致敬。与其他传统的战争电影不同的是,斯皮尔伯格将反抗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发动战争的道德基石。“大屠杀记忆”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被导演融入电影叙事中,借此构建出更具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身份认同。
一、作为视觉修辞的“大屠杀记忆”
作为电影中执行拯救瑞恩任务小分队唯一的犹太人,列兵斯坦利·梅利(PrivateStanleyMellish)成为了观众和“大屠杀记忆”之间的媒介,他的表现以及和其他角色的互动推动了电影叙事的发展。梅利在电影中发挥了两种作用,首先,他代表着世俗化犹太人,举止行为表现出明显的美国文化影子;其次,他的死亡激发了犹太“大屠杀记忆”中的关键因素——濒临灭亡的犹太人拼死抵抗,听到呼救声的美国基督徒同伴即影片中的翻译厄本下士(CorporalUpham))却无能为力,无人阻止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恐怖行径。下面选取影片中跟犹太士兵梅利相关的场景来解读导演对“大屠杀记忆”的展现。
攻占了海滩后,士兵在搜索德军战壕时发现了一把希特勒青年军小刀并把它交给了梅利。他拿起这把刀嘲笑着说:“现在它成为犹太安息日的面包刀了。”梅利说完,靠着战壕忍不住开始哭泣。虽然美国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然而犹太民族在“二战”中遭遇的苦难给梅利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此时的中士霍瓦特(SergeantHorvath)正在向写着“法国”字样的锡罐里装土,旁边是两个标有“北非”和“意大利”的锡罐。镜头在霍瓦特、梅利和其他士兵之间切换,观众可以看到梅利哭泣时其他人眼神的躲闪。
这一镜头语言试图暗示:无论漂泊多远,无论在哪里战斗,哪怕是到天涯海角,他们也不屈不挠地要终结这场可怕的战争。在犹太会堂和犹太家庭遵从的安息日传统象征着人和上帝所订立的盟约,而这把希特勒军刀则致力于亵渎和湮灭这种神圣性,作为犹太人的梅利不可避免地处在这种阴影之下。尽管信仰是神圣的,然而影片中的梅利已经是被同化的美国犹太人,观众从他身上看不到明显的犹太痕迹。梅利在面对制造大屠杀惨剧的德国人时却极力炫耀他的犹太身份:他在德国俘虏队伍旁挑衅地摇晃着自己被“大卫之星”缠绕的胸牌,嘲笑着大喊“我是犹太人”。梅利试图以这样的行动来告慰死在纳粹屠刀下的犹太同胞。然而无论他怎么做,逝者都不可能复生,梅利心中的伤痕也无法抹平。
梅利的死亡发生在电影最后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下士厄本负责给位于二楼的梅利和另外一个士兵运送弹药,然而他在枪林弹雨中被恐怖的景象吓得呆若木鸡,躲在柱子后面的角落里。楼上的美国士兵被击毙,而梅利孤身一人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开始和德国士兵肉搏,在此情境下犹太“大屠杀记忆”强烈浮现。梅利和德国士兵的打斗随着镜头的摇摆使观众无比揪心,犹太人的处境岌岌可危。镜头不断切换到瑟瑟发抖的厄本身上,他听着楼上的打斗声瘫软在地无法移动。此时的德国士兵已经将刺刀抵在梅利的胸前并将其缓慢刺入,同时喃喃自语:“这对你是一种解脱,很快就结束了”。在德国士兵刺死梅利后下楼时,近镜头扫过他衣领上的肩章,表明凶手是纳粹党卫军成员,是把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并执行“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精锐部队。
从叙事角度来看,梅利死亡这一场景渲染了战争导致的悲剧性创伤,下士厄本这一角色在不同层面都发挥了作用。首先,作为观众的这一代人最初极有可能和厄本一样选择对战争袖手旁观,而这样的“不作为”产生的后果很严重。其次,厄本下士象征着美国士兵的情感创伤和牺牲。战争的残酷给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双重创伤,电影男主角米勒上尉(CaptainMiller)也因为战争和死亡的压力留下了双手颤抖的后遗症,这使得美国政府在战后进一步关注士兵精神创伤问题。最后,守卫大桥的战斗开始之前,厄本和梅利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起听歌,谈笑风生时建立了友情,宝贵的友情促使厄本对自己听到梅利苦苦挣扎时的不作为充满罪恶感,而观众通过这些具体场景的描绘更能体会到厄本的极度痛苦和悔恨之心。这些场景交织在一起表现出美国化的“大屠杀记忆”——因为对欧洲犹太人的遭遇没有进行迅速而有效的拯救行动而充满罪恶感。
二、“大屠杀记忆”的美国化进程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犹太民族对大屠杀的记忆一直倾向于颂扬“华沙隔都起义”等英勇抵抗行为,选择性地忽略了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向屠场”的软弱行为。1950年,以色列内政部和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组织在锡安山上被认为是大卫王坟墓的地方为大屠杀受害者建立了一个悼念角,它被命名为“大屠杀地窖”。1951年以色列议会将尼散月第26天确定为大屠杀和隔都起义纪念日(theHolocaustandtheghettouprising),将大屠杀纪念日与反抗德国纳粹的华沙起义联系在一起;同一年,隔都起义纪念博物馆建成。1953年以色列国会通过法律建立官方的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这部法案记录了犹太人从纳粹压迫和死亡集中营时期就开始持之以恒的努力,纪念馆将收集跟大屠杀相关的档案资料、证词、文件。
这些资料将向研究者和历史学家开放,在他们重构历史叙事时发挥作用。1959年又将原有纪念日改名为“大屠杀与英雄主义日”(theHolocaustandHeroismRemembranceDay),将对纳粹的武力反抗看作是英雄行为,由此奠定了“大屠杀记忆”中的英雄主义基调,并通过《犹太大屠杀纪念法》对纪念日的仪式和日程进行规制[1]。以色列各地接连建立起纪念大屠杀的各种场所,包括犹太会堂、公墓以及公共广场等。不同的纪念场所对大屠杀的原因以及对犹太人生活的深远影响不断进行反思。宗教与世俗、官方与民间纪念方式的差异也反映出各方考虑以色列未来政策时所秉持的不同政治理念。
犹太民族致力于利用已建立的大屠杀纪念馆、国家悼念仪式以及教育体系等工具建构出经典的大屠杀叙事,确保犹太复国主义精神中的毁灭和重生、流散和救赎等主要因素得到认同。然而领导以色列建国事业的先驱们担心“大屠杀记忆”在社会上的日益凸显将导致以色列人对非犹太世界持否定态度,好像“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2]72,这些领导者们担心大屠杀记忆和教训在下一代中逐渐消逝。
在1956年大屠杀纪念日的讲话中,阿巴·柯夫纳(AbbaKovner)表达了这样的困境:“有人说:不要忘记,最后他不会记得什么,因为记住一切使他癫狂;但要忘记一切是对生活的背叛。”[2]72他指出了两条看上去自相矛盾的道路:一方面提出要限制大屠杀纪念活动,因为它可能使人在面对生活时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他又把大屠杀纪念活动看作是打开新生活的钥匙。忘却并非是背叛大屠杀行为或者记忆,而是对生活本身的背叛。恰到好处地纪念和审视历史是正确塑造犹太民族未来生活的钥匙。
“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独特的符号,表明流行文化和政治紧密相关。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大屠杀”并没有从死亡集中营的回忆中直接被建构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集中营的幸存者在开始新生活后往往选择对创伤记忆保持沉默,直到1959年“大屠杀”这个词汇才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1960年对阿道夫·艾希曼的逮捕以及1961年在以色列对他进行的审判,首次吸引了全世界对六百万被屠杀犹太人的关注。学者们一致认为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大屠杀记忆”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像欧洲犹太人曾经面临的绝境一样,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联合打压使得以色列国家的存亡危在旦夕。犹太民族这一次选择先发制人,在战争爆发六天后就以绝对优势控制了约旦河和尼罗河沿岸地区,重新接管了耶路撒冷,使得犹太人再次站在神圣的第二圣殿西墙土地上。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对于“大屠杀记忆”的美国化至关重要。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社会开始主张少数民族的身份和权利。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美国各地的大学和学院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种族研究中心。在此推动下,有关“大屠杀”研究的课程逐渐增多,吸引了很多学生的关注。其次,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美国犹太人开始思考自身“牺牲和救赎”的问题。欧洲犹太人沦为大屠杀的牺牲品,而以色列和美国使他们得到救赎。美国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再次扮演了救赎者的角色。
在以色列军队遭受了空前的打击、形势十万危急之时,美国通过空运物资直接干预了战争走势。这对以色列和美国的“大屠杀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1977年以色列人民开始支持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利库德集团并选举梅纳赫姆·贝京为总理,他一直致力于在增强实力、抵抗和利益的基础之上构建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感。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将以色列放在“大屠杀和救赎”叙事的中心位置,它作为被消灭的六百万犹太人的救赎地,保证以色列的生存是必要的职责。“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犹太社区和以色列国家缔结契约的基础。
媒体在塑造美国化“大屠杀记忆”并传播到犹太社区之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同一时期反映纳粹大屠杀的电影之外,1978年4月16号总时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在美国上演,1200万观众通过节目对德国犹太人韦斯一家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报纸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分发学习指南给观众,犹太人在观看节目时纷纷佩戴黄色“大卫之星”。节目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在电视剧播出后不到两周的时间,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就在5月1日宣布成立纪念“大屠杀”总统委员会,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大约一千名“拉比”参加了委员会成立庆典活动。
暂且不提卡特总统这一公告背后的政治目的,委员会的成立使得“大屠杀记忆”在美国意识形态认同层面上得到规制,而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也在1993年落成并对公众开放。纪念馆是为了“悼念被纳粹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和几百万非犹太人”,它旨在呈现出大屠杀的真相,尽可能清晰而全面地告诉美国民众在那段黑暗岁月发生的故事,使得公众警醒“作为袖手旁观者无意间犯下的罪行”。纪念大屠杀的另外一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当年热映,总统克林顿和脱口秀名人奥普拉等人纷纷号召民众走进影院去反思那段历史。“大屠杀记忆”及其象征意义被建构成独特的美国文化符号,这一过程是官方话语权、社会趋势和大众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
三、结语
导演斯皮尔伯格在介绍拍摄花絮时提到:“《拯救大兵瑞恩》是为了退伍军人而拍摄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不会过上想要的生活。”电影不断探讨“怎样在如炼狱般的战争中保持尊严”,角色霍瓦特对此做出了回答,“拯救列兵瑞恩也许是这场战争中唯一得体的事情”。这种对尊严、文明、人权的渴望通过角色传达给了观众。“大屠杀记忆“逐渐走出美国的犹太社区,在社会民族身份认同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从殖民地时期走过的美国基督教价值体系将清白、自省、牺牲、受难以及拯救作为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这些准则是世俗盟约,也是国家统一和人民忠诚的源泉。
在电影中使用“大屠杀记忆”重新强调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从希特勒青年军刀成为安息日面包刀,从心照不宣的目光对视到霍瓦特背包里装满沙土贴好标签的锡罐,世俗盟约被一一践行。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中赋予了寻找列兵和诺曼底胜利登陆同样重要的意义。观众无需解释就能明白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猛攻奥马哈海滩,也逐渐理解了八位士兵去拯救列兵瑞恩的重要性。在大屠杀的语境下,肯定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是最有力的行动。
此外,将“大屠杀记忆”糅合进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使得过去的历史成为未来道德准则的来源。文学评论家蒂姆·伍德(TimWood)在1998年写道:“叙事模式在被用来构建道德历史时会发挥一种功能,在集体记忆的治疗实践中遭遇’不可控制的他者’。”《拯救大兵瑞恩》就是这样一种叙事模式,观众在电影里面遭遇的“他者”显而易见是纳粹暴行的噩梦,然而过去的历史也是“不可控制的他者”。这些因素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道德瑕疵,也是大屠杀“记忆景观”的一部分。电影将这种叙事模式下的美国道德正义置于无可指责之下:无论这个国家的缺点是什么,至少在人类生死存亡时刻它采取了行动,与纳粹势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因此,斯皮尔伯格将“大屠杀记忆”编织进美国的文化记忆中,向那些为了终结战争的恐怖而牺牲的人致敬。
参考文献:
[1]DaliaOfer.Israel[C]//DavidWyman,ed.TheWorldReactstotheHolocaust;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836-922.
[2]DaliaOfer.WeIsraelisRemember,ButHow?TheMemoryoftheHolocaustandtheIsraeliExperience[J].IsraelStudies,2013(2):70-85.
文史论文投稿刊物:《文史博览》(理论)是由致力于理论研究和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成果,人民政协的理论探索和履行职能新鲜经验的研究成果,介绍评析中外学术界最新发展动态、观点和论著的文稿。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2634.html

2023-2024JCR闁荤喐绮嶅妯虹暦椤掑嫬绠归柣鎴f閻愬﹪鏌eΟ鍨毢闁规枻鎷�

SCI 闂佽崵濮抽懗鍫曞磿閵堝鍑犻柛鎰靛枟閻掕顭跨捄鐚村伐闁诲繋绶氶弻鏇㈠幢閺囩姴濡芥繝娈垮枛濞层劎鍒掑▎鎴炲晳闁靛牆鍊告禍鎯归敐澶嬫暠闁告瑥绻橀弻娑㈠Ψ瑜嶆禒婊堟煕濞嗗繒绠绘鐐村姍瀹曟儼顦茬痪顓涘亾

SSCI缂傚倷璁查崑鎾绘煕濞嗗秴鍔ょ紒鎰殘缁辨帗寰勭€n亞浠村銈嗗笧閸犳牕顕i悽鍛婂亜鐎瑰嫭澹嗘禍鏍⒑绾懎鐓愭繛鍙夌矋閻忔瑩鏌i悩娆忓暙椤忣剚銇勯弮鎾村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婵傛潌鍥ㄧ節濮橆剚顥濋梺鎼炲劘閸斿孩绔熺€n喚鍙撻柛銉戝啯娈插┑鐘亾闁跨喓濮寸粈鍡椻攽閻樿精鍏岄柣顓熺懅缁辨挻鎷呴崫銉愶紕绱掑Δ鈧惌鍌炵嵁鎼淬劌鍗抽柣妯鸿嫰缂嶅﹪鐛幇鏉跨倞鐟滃秶娑甸埀锟�

sci闂備礁鎲$划宀勵敊閹剁棗i闂備礁鎲¢悷銉╁嫉椤掑嫬鏋佺痪顓炴噷娴滃綊鏌¢崶鈺佹瀾闁糕晛鍊块弻娑㈠箳閻愭潙顏�

EI闂備浇銆€閸嬫捇鎮规ウ鎸庮仩缂佸娼¢弻锝夊Ω閵夈儺浠归梺鐓庣仛閸ㄥ灝鐣烽崼鏇熷殟闁靛绠戦悞鎼佹⒑閸涘﹤閲滈柟鍑ゆ嫹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绫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Ο鍧�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佺浜悧鐚歩

EI闂備礁鎼悧蹇涘窗鎼淬劌鍨傞柟璺ㄥ厡XSourceList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窏ci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р攽椤旂偓鍤€婵炶绠撻崺鈧い鎺戯攻鐎氾拷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穯d-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鐡ㄧ换宥夊礉閸涱垪鍋撳▓鍨灍婵炲弶锕㈠鎼佸礃椤斿吋鐎梺缁橆殔閻楀棛绮婇敃鍌氱閻庢稒蓱鐏忕増绻涙總鍛婃锭闁崇懓鍟撮獮鍥敇閻旈鍔梻浣告啞鐢亪骞忛敓锟�

CSCD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2023-2024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妤e喛缍栭柡宥庡幗閳锋棃鏌曡箛鏇炐㈤柣搴☆煼閺屾盯寮介鐘电獥闂侀潧妫撮幏锟�2023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顕崑娑滅亣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⒑閸涘⊕顏勎涘Δ鍛剳濡わ絽鍟崕搴€亜閺冨洤浜圭紒澶涙嫹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佸姍瀹曢潧饪伴崼鐔封偓鍧楁煕閹捐尙璐版繛鑲╁█閹鈽夌€圭媭鍚呯紓浣瑰敾閹凤拷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绻樻俊鐢告倷閺夋埈鍤ゅ┑顔斤耿绾ǹ岣块悩缁樺€垫繛鎴濈枃椤撹櫣绱掗幉瀣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ㄣ偅閸愩劎顦卞┑掳鍊愰崑鎾绘煏閸パ勫枠鐎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

2023闂備胶绮〃鍛存偋韫囨侗鏁勯柛銉墮绾偓婵炶揪绲介幖顐︺€傞悡搴樻闁瑰灝鍟獮妤呮煛鐎n亜鏆g€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梻浣哄劦閺呪晠宕伴弽顐ょ闁跨噦鎷�

2023-2024JCR闁荤喐绮嶅妯虹暦椤掑嫬绠归柣鎴f閻愬﹪鏌eΟ鍨毢闁规枻鎷�

SCI 闂佽崵濮抽懗鍫曞磿閵堝鍑犻柛鎰靛枟閻掕顭跨捄鐚村伐闁诲繋绶氶弻鏇㈠幢閺囩姴濡芥繝娈垮枛濞层劎鍒掑▎鎴炲晳闁靛牆鍊告禍鎯归敐澶嬫暠闁告瑥绻橀弻娑㈠Ψ瑜嶆禒婊堟煕濞嗗繒绠绘鐐村姍瀹曟儼顦茬痪顓涘亾

SSCI缂傚倷璁查崑鎾绘煕濞嗗秴鍔ょ紒鎰殘缁辨帗寰勭€n亞浠村銈嗗笧閸犳牕顕i悽鍛婂亜鐎瑰嫭澹嗘禍鏍⒑绾懎鐓愭繛鍙夌矋閻忔瑩鏌i悩娆忓暙椤忣剚銇勯弮鎾村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婵傛潌鍥ㄧ節濮橆剚顥濋梺鎼炲劘閸斿孩绔熺€n喚鍙撻柛銉戝啯娈插┑鐘亾闁跨喓濮寸粈鍡椻攽閻樿精鍏岄柣顓熺懅缁辨挻鎷呴崫銉愶紕绱掑Δ鈧惌鍌炵嵁鎼淬劌鍗抽柣妯鸿嫰缂嶅﹪鐛幇鏉跨倞鐟滃秶娑甸埀锟�

sci闂備礁鎲$划宀勵敊閹剁棗i闂備礁鎲¢悷銉╁嫉椤掑嫬鏋佺痪顓炴噷娴滃綊鏌¢崶鈺佹瀾闁糕晛鍊块弻娑㈠箳閻愭潙顏�

EI闂備浇銆€閸嬫捇鎮规ウ鎸庮仩缂佸娼¢弻锝夊Ω閵夈儺浠归梺鐓庣仛閸ㄥ灝鐣烽崼鏇熷殟闁靛绠戦悞鎼佹⒑閸涘﹤閲滈柟鍑ゆ嫹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绫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Ο鍧�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佺浜悧鐚歩

EI闂備礁鎼悧蹇涘窗鎼淬劌鍨傞柟璺ㄥ厡XSourceList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窏ci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р攽椤旂偓鍤€婵炶绠撻崺鈧い鎺戯攻鐎氾拷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穯d-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鐡ㄧ换宥夊礉閸涱垪鍋撳▓鍨灍婵炲弶锕㈠鎼佸礃椤斿吋鐎梺缁橆殔閻楀棛绮婇敃鍌氱閻庢稒蓱鐏忕増绻涙總鍛婃锭闁崇懓鍟撮獮鍥敇閻旈鍔梻浣告啞鐢亪骞忛敓锟�

CSCD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2023-2024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妤e喛缍栭柡宥庡幗閳锋棃鏌曡箛鏇炐㈤柣搴☆煼閺屾盯寮介鐘电獥闂侀潧妫撮幏锟�2023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顕崑娑滅亣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⒑閸涘⊕顏勎涘Δ鍛剳濡わ絽鍟崕搴€亜閺冨洤浜圭紒澶涙嫹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佸姍瀹曢潧饪伴崼鐔封偓鍧楁煕閹捐尙璐版繛鑲╁█閹鈽夌€圭媭鍚呯紓浣瑰敾閹凤拷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绻樻俊鐢告倷閺夋埈鍤ゅ┑顔斤耿绾ǹ岣块悩缁樺€垫繛鎴濈枃椤撹櫣绱掗幉瀣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ㄣ偅閸愩劎顦卞┑掳鍊愰崑鎾绘煏閸パ勫枠鐎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

2023闂備胶绮〃鍛存偋韫囨侗鏁勯柛銉墮绾偓婵炶揪绲介幖顐︺€傞悡搴樻闁瑰灝鍟獮妤呮煛鐎n亜鏆g€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梻浣哄劦閺呪晠宕伴弽顐ょ闁跨噦鎷�
闂佽崵濮村ú銈夊床閺屻儲鏅查柣鎰惈缁€鍐╃箾閸℃鍑圭紒璇叉閺岀喖顢樿閻忚尙绱掓潏銊х疄鐎规洘鐟﹀ḿ顏堝级閸噮娼�/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閹间礁鏄ラ柨鐕傛嫹/闂備焦鎮堕崕鏉懳涢崟顖氳埞閻庢稒锚缁剁偤鏌ㄩ悤鍌涘/濠电偞鍨堕幖鈺呭矗閳ь剟鎮楀顓炩枙鐎殿噮鍓熼弫鎾绘晸閿燂拷/闂備胶枪缁诲牓宕濆畝鍕垫晢闁绘棁娅i惌鎾绘煙鐎电ǹ浠﹂柛鈺佸€块弻娑㈠箳閹搭垱鏁鹃柣銏╁灠缂嶅﹪骞婇敓鐘茬疀妞ゅ繐妫涢幉鍧楁⒑閸涘﹦鎳勯柛銊ャ偢婵℃挳宕橀鑲╊唶闂佹悶鍎滅仦鑺ヮ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