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先秦法家思想从自然状态和人性假设出发,以法律制定、法之必行为治理手段,以富强为本、法治为用为政治目标,谋划出以刑去刑、以法去法的大治图景,在逻辑上自成严整体系,在战国乱世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效用。 抛开制度设计层面的局限性,于治理手段而言
摘要:先秦法家思想从“自然状态”和人性假设出发,以“法律制定、法之必行”为治理手段,以“富强为本、法治为用”为政治目标,谋划出“以刑去刑、以法去法”的大治图景,在逻辑上自成严整体系,在战国乱世体现出强大的社会效用。 抛开制度设计层面的局限性,于治理手段而言,法家思想不仅是治乱之说,更是治世之道。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和世界竞争格局下,深入挖掘法家思想精髓,对法治国家建设必定有所裨益。
关键词:先秦法家; 法治; 依法治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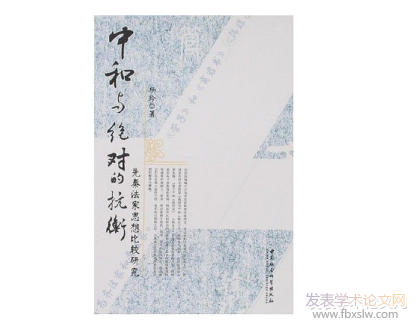
一、作为“治道”的法治
古代中国有无法治早有定论。 俞可平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刀”制而无“水”治,即有法制而无法治,根本在于封建皇权始终居于法律之上[1]。 这一代表性论断基于现代法治“法律至上、法外无权”的内核,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表述:良法与普遍的服从。 现代法治与民主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等现代国家制度设计的各个层面,并随着政治社会化的加快日益深入人心。 然而自亚氏以来,西方始终未能给出法治的确切涵义,法治被认为是“极其重要,但不能随便定义”的概念,现代法治坚持的正义、公平、权利、程序、权力制约等诉求仅可视为法治的普遍原则。
作者:周生虎,于忠华
任何国家都有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正如民主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法治的实现形式也各有千秋。 无论是西方的宪政还是我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现代法治架构无不以民主为前提,并作为民主的保障。 从这个角度讲,先秦法家的思想和实践不可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以法而治”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法律的创制和严格执行为手段,虽不乏朴素的民本思想,但其根本任务是维护封建皇权专制。 因此,于“政道”(国家制度设计)层面而言,先秦法家与现代法治是割裂的,加之传统儒家德治话语体系居主导地位,缺少对法家的关照,当代对法家的研究大多从法哲学层面加以分析,缺少历史照进现实的视角,世界观有余而方法论不足。
用现代法治的标准来定义先秦法家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如果说政道层面的法治侧重价值,则治道(治理工具)层面的法治更重手段; 政道层面的法治与人治相对,治道层面的法治与德治相对。 非公共管理学范畴的“治理”一词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治理的手段多样,较之礼治和德治,法治的作用不可替代,“法”与“治”同为“氵”旁,镌刻着农耕文明的印记。 “,刑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说文解字》对古体法字的解读凸显了中国古代法治的使用价值——维护公平正义与惩治恶行,这同样是现代法治社会作用的重要内容。
轴心时代(The Axis)的理性之光普照后世,自秦以降,“儒法结合”抑或“儒表法里”,从统治架构和治理手段来讲,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法家始终未曾离开过政治舞台中心。 “法布于众”“依法办事”“刑无等级”“法律稳定”等先秦法家的核心理念成为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基因,与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法治建设的核心议题——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遥相呼应。 法为治国之重器,无须在治理工具上过多贴上价值标签,探索先秦法家的逻辑理路,继承重法主义传统,丰富治理手段,这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自然状态:法家的逻辑起点
自然状态假设奠定了近代西方国家学说的基础,成为西方政治哲学逻辑推演的源头。 自然状态假设发轫于格老秀斯的自然权利学说,霍布斯将自然状态定义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丛林法则和暴力逻辑作为行动规则,国家的出现显得正当且必要。 洛克和卢梭以自然状态为逻辑起点,分别提出了权力制约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人民主权学说。 “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2]恩格斯从阶级的视角对早期人类社会状态的描述也可视为对自然状态的认识。
先秦法家虽然没有明确涉及“自然状态”的概念,但在法家代表著作《商君书》和《韩非子》中对国家产生前的人类社会图景均有描述,并以此凸显秩序与规则的重要性与君权的合法性,比西方要早近2000年,《商君书·开塞》有如下描述:
天地设而民生之。 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
亲亲则别,爱私则险。 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 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 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 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 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 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 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 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 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 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这段表述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形态:“力争” “民乱” “莫得其性”,无法实现正常的社会秩序; 二是混乱现象出现的原因:“亲亲而爱私”,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可以任意践踏他人权益; 三是如何止乱禁暴:“立贤说仁” “立禁设制” “立官” “立君”,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和强有力的实施重建秩序。 可以看出,前两个问题与西方政治学自然状态假设基本一致,但摆脱自然状态的政治设计却大相径庭,法家将“立君”作为终极制度安排,无论是宣扬教化还是法令的制定者、颁布者、实施者,君主都高居百姓之上,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然而“立君” “设有司”,又是为了更好地推行法度,以合法的暴力取代非法的暴力,这无疑又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自然状态的混乱无序,究其根本,客观上在于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主观上则因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人性论”与自然状态有着必然的关联性,在战国中后期逐渐成为公共话题。 后世多为法家贴上“性恶论”的标签。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盖人性惟知趋利避害,故惟利害可以驱使之。 法家多以为人之性恶。 韩非为荀子弟子,对于此点,尤有明显之主张。 ”[3]
“性恶论”对标“性善论”,否认人类先天的良知良能,强调趋利避害的“经济人”本性,此外,对《韩非子》的人性假设,学界还有“中性说”(即“自然人性说”)。 善与恶分居人性的两端,“性善说”与“性恶说”都是极端化的表述,人的心理活动是知、情、意的结合,动机复杂难辨,难以用善恶标准简单评判。 现代管理学人性假设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再到“复杂人”便是印证。 因此,在“性善”与“性恶”的争论中,无论天平倒向哪一边都有以偏概全之嫌。 “中性说”认为《韩非子》对人性善恶未予置评,认为《韩非子》提出的人性,既造成战国时代急需拯救的失序局面,又担当着韩非学说凭借法术势得到治、强的前提[4]。
综合法家的人性评价,本文提出“需求说”。 法家典籍中强调的“趋利避害”为人之常情,“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池》),将“人之常情”与“性恶”画上等号未免牵强,从人的行为动机出发,倒是“需求”显得更为贴切。 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会一直困扰人类,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古代社会,如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必然会通过暴力强制获取,这是混乱的根源。 需求本身无关善恶,但需求满足的途径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区别。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 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 ”(《管子·禁藏》)“千仞之山” “深渊之下”,这是极端之害,但当“驱利”与“避害”无法兼顾时,商贾和渔人的选择是“无所不上” “无所不入”,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趋利避害”,而是为了满足生计的必然选择,这里讲的是需求。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 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 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韩非子·备内》)造车之人欲人富贵而有购买能力,造棺之人欲人夭死才有需求,并非舆人善而匠人恶,依然是需求所致,与人之本性善恶无关。
需求的满足构成了人的行为动机,需求与满足之间构成了法治的作用空间,使法治显得合乎情理且必要。 “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商君书·错法》)君主正是由于百姓的好恶和需求而操赏罚二柄维护统治秩序。 相反,如果百姓都“寡欲无求”或者个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法治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从需求角度而言,法治的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发展生产,止乱治暴,建立秩序,不至于在利益争夺中自我毁灭; 二是通过制度建设,使社会稀有资源合法地掌握在君主手中,通过权威性的利益分配和部分需求满足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巩固皇权专制。
三、以法而治:大争之世的应然选择
关于国家的起源,西方和东方众说纷纭。 然而,不论是家庭演变国家论、社会契约论、暴力论、君权神授论、阶级论,在国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上殊途同归,那就是止乱,建立秩序。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最长的分裂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至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纵横捭阖,形势险恶,生存成为第一要务,丝毫的差池,足以改变一国之命运,合理的使有才能之士发挥作用,富国强兵,是各国君主面临的共同问题。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先后献上“帝道” “王道”,秦孝公不予采纳,而后说“霸道”,孝公大悦,后开始变法改革,使秦从一西北边陲小国逐渐走向强大,最终一统天下。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管子·乘马》),“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管子·兵法》)。 帝道、王道、霸道说是先秦的一大政治思潮,诸子百家为止乱图强开出诸多药方,“三道”说是集中代表。 君主若能遵循道,清静无为而天下大治,则是帝,对应道家; 若君主以德治国,有所作为,然后天下大治,君主不再为国事操劳,则为王,对应儒家; 若君主施政有为,建制立法,国富兵强,即使不自以为贵,而天下能大治,则是霸主,对应法家[5]。 三种治理手段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纷乱的诸国有过不同程度的尝试实践。 以结果证明手段之正当似有偏颇,但秦国奉行法家的“霸道”及开展变法改革走向富国强兵之路确是历史的必然。
何谓最好的国家治理? 儒家曾经给出经典回答——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渊》)国富、兵强、公信力,大争之世,儒家的目标没能达成,法家通过变法实践将这一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
第一,“国富”——法家对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力发展步入新阶段,分封制下的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度制约了新兴地主阶层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封建私有土地制度呼之欲出。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法家围绕土地所有制开展了一系列的变法改革,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李悝变法提出“尽地力之教”,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其“平籴法”近似于“政府以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稳定小农经济,实现了“籴不贵而民不散”,保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商鞅吸收李悝变法的经验,先是颁布《垦草令》,奖励耕织和垦荒,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而后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国有土地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立法确认土地私有制,实行税租制度改革,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来源,为秦国的经济强大打下基础。
第二,“兵强”——变法改革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 法家变法改革中对提升军队战斗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是世卿世禄制的废除与军功爵制的建立。 以秦国为代表,“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 军功爵制取消了宗室贵族的世袭特权,军功取代血缘和属籍成为享有爵禄的标准,“猛将必发于卒伍”,开历史之先河。 军功与官爵之迁相称,士兵从“勤于王事”一定意义上转变为“勤于己事”,“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商君书·画策》),积极性空前高涨。 此外,赏罚并行,执法严格,师出以律,军纪建设成为战斗力的保障。
第三,“公信力”——以法而治重塑了国家公信力。 变法改革外在表现为治国方略的选择,实则是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是否敢于动真碰硬关系变法成败。 法家系统深入的变法改革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彰显了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公平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提升了公信力。 商鞅变法之初的“徙木立信”打消了民众对变法改革的疑虑。 “刑其傅公子虔,鲸其师公孙贾”,执法严明,不避亲贵,挑战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 废除井田,鼓励垦荒,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作用。 制定二十等爵制度,削减贵族之权,奖励军功,一定程度上打通了阶层上升通道,缓和了阶级矛盾。 推行县制,统一度量衡,维护中央集权,统一政令,客观上营造了安定有序的社会局面。
四、以刑去刑:法家的理想国
国家向来是矛盾综合体。 霍布斯将国家喻为“利维坦”,作为“必要的恶”,国家的出现是以一种恐怖代替另一种恐怖。 “诺斯悖论”指出,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作为国家最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和治理手段,法治是一把双刃剑,自由主义者认为,法治是实现秩序的必要条件,同时构成自由权利的障碍。 法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也一直未能摆脱被用得最多,同时也是被骂得最多的尴尬境遇。 太史公批评法家“严而少恩”,“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所以“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当代也有学者认为:“法家政治是以臣民为人君的工具,是经过长期精密构造出来的极权政治,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但违反人道精神,不能作为立国的长治久安之计。 ”[6]
对法家的批判与“以刑去刑”的核心观点密切相关,“以刑去刑,国治; 以刑致刑,国乱”(《商君书·去强》),“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韩非子·饬令》)。 “以刑去刑”勾勒出了法家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蕴含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思维。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对“必要的恶”的曲解,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恶”上而忽略“必要”。 对法家“以刑去刑”的批判过多聚焦“刑”而非“去刑”,关注点不同,结果必然大相径庭,在此,有必要为法家正名。
第一,法家之法为“良法”。 评判法之良恶有一黄金法则:是保障多数人的利益还是仅仅维护少数人的特权。 任何政治统治方式都须为其合法性辩护,法家的政治理想与儒家的大同社会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希望天下大治,属于民本思想的不同表现形式。 儒家主张广施仁政,“以德去刑”的“仁民”,法家强调富强为本,法治为用“利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于欲,期于利民而已”(《韩非子·心度》)。 商鞅明确提出“为天下治天下”,以增进人民利益为归宿,韩非认为推行法治的根本目的是“利民萌,便众庶”。 较之混乱动荡下的生灵涂炭,法治之下秩序和谐的社会,统治者利益实现的同时,民众仍为最广泛的受益群体。
第二,法家之法为公正之法。 法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强制性力量须具备普遍的约束力,否则便是一纸空文。 法家将辨是非、主公正的独角兽(獬豸)视为“护法神兽”,意指法的独一无二。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管子·任法》)法家的政治理想蕴含着法外无权、全民守法的进步价值,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 “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商君书·修权》),“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商君书·赏刑》),“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商鞅思想中重点强调的“壹刑”凸显了法的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 法是权衡是非利弊的标准,享有最高权威,贵贱亲属概莫能外,一断于法。 此外,成文法应公开透明,使民众明白权利义务,执法者不敢徇私枉法。 “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将法治视为决定国家兴亡的关键,“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其刚性执法思想更带有激进的公正意味,主张一视同仁,铁面无私。 为保证执法公正,法家提出于行政机构之外设置专属执法机构和吏员,集执法、解释法律、法治教育职能于一身,体现了朴素的权力制约和司法独立价值。
第三,法家的“严刑”不是“滥刑”。 “滥刑”者,脱离规则和标准,罗织罪名,随意构陷,乱用暴力,随意轻重。 如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荡然无存,统治必然不能长久,这显然不是法家“严刑”的初衷,立足治乱,而后治世,这才是“以刑去刑”的最终目的。 法家的“严刑”建立在对儒家“轻刑”批判的基础之上,儒家基于“仁政”考虑,提倡重罪轻刑,法家认为此举不明智且是祸乱的根源,“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五蠹》)。
法家的“严刑”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量刑轻重有法可循,通过重刑而建立法律权威,起到威慑作用,使人不敢以身试法; 二是通过法布于众和公正司法使法内化为民众认同的价值准则,从而自觉守法,实现“自治”; 三是通过“严刑”之下的长期“自治”建立起高度法治化的社会,最终实现“去刑”,天下大治。
第四,法不诛心,唯论言行。 “以刑去刑”规范的是人的外在言行,而不惩戒内心活动,这一观点至少有四个方面的进步性:一是体现高效率。 人的内心活动复杂多变,从思想中彻底移除侵害国家或他人的想法,从善如流,固然可贵,然而成本过高,极难实现,相比之下,规范言行简单高效。 二是明确了罪与非罪的界限。 将内心活动和外在表现分开,论迹不论心,保证了法的公开、公平行使。 三是彰显了罪刑法定的理念,限制了人治的作用空间。 可以避免执法者捕风捉影,滥用权力,随意定罪,民众也无需担心被腹诽论罪,人人自危。 四是教化民众。 言行是内心活动的外在表现,对违法言行的惩戒可以教化民众反观内心,避免恶心滋生发展外化于行,引导人心向善,自觉守法。
五、依法治国:通往未来的路
秦统一六国,法家思想“登峰造极”,秦二世而亡,法家“背锅”,身负骂名,何故? 利器交由不善使用者之手,必然造成破坏性后果。 在秦后的历史长河中,法家思想时而化作暗流,潜入地表,滋养万物; 时而波涛拍岸,奏出时代强音。 “法家三期说”认为,先秦法家为法家一期,法家二期为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新法家,法家三期为1949年后(一说改革开放后)法家思想的发展和实践[7]。
每一次法家思想的复兴,都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结合现实政治社会需要的基础上作出的创造性成果转化。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从1980年“人治与法治大讨论”,到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法治入宪”,再到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确立,重法主义传统得以复兴,法家“富强为本,法治为用”的核心理念再次焕发生机。 法家思想与当前的世情、国情深度契合,这是基于法家发生逻辑作出的判断。 从本质上讲,法家的逻辑起点没有变,大争之世的世界格局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敬畏“头顶之剑”,又要用好“手中之剑”。
第一,需求的合法化满足依然是法治存在的重要价值。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矛盾无法避免。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区和深水区,利益固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较突出,人的价值需求复杂多变,社会深层次问题逐渐外显。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实现后,需求层次逐级上升,社会需求、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相对于浅层次需求而言涉及更多的社会稀有资源,满足难度递增,加之各层次需求之间存在叠加,使需求的满足变得更为复杂。 “不患寡而患不均”,需求的满足、利益关系的协调不仅关乎社会总产品生产,更是分配问题,以法治的方式确定分配规则,固化利益表达,保护合法、合理所得,打击损人利己行为,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 这里并非淡化“德治”的价值,但毋庸置疑的是,离开了严格的法律,良好的道德也很难滋养。 因此,“法”“德”并举的同时,必须分清主次,抓住重点。
第二,法治是世界竞争格局下的必由之路。 萨缪尔·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七大文明圈,认为21世纪国际核心的政治角力将在不同文明之间展开且日趋激烈,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末尾,他推演了中国和美国作为两大文明中心发生战争冲突后世界格局的变化。 “文明冲突论”争议尚存,但愈演愈烈的世界竞争形势是不争事实,习近平将其概括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有资格、有能力参与到世界竞争格局中来,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再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日强。 在竞争格局中站住脚跟甚或发挥支配作用,根本上要靠“实力”说话。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改革重心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法制建设。 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协同推进,体现的都是法家“富强为本,法治为用”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 全面依法治国“新十六字方针”与法家思想中的制定法律、法布于众、保持法律稳定、依法办事、刑无等级等核心内容深度契合,体现了治道的历史延续性。 奉法者强则国强,法治是政治走向成熟的标志,更是建设强大国家,在世界竞争格局中处于优势地位的重要保证。
第三,敬畏“头顶之剑”,树立法治权威。 依据马克斯·韦伯权威理论,三种合理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克里斯马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在不同的时代呈现出以某一种为主,其他为辅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完成由克里斯马型向法理型的转换。 韦伯认为,克里斯马型属于人格取向权威,最具合法性但缺乏稳定性; 法理型权威属于制度取向权威,来源于非人格化的制度和法律,通过强制力保证实现,因而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特质,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权威类型。
权威以服从为条件,树立法治权威,由服从到敬畏需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以“力”服人。 历史上任何一次盛世,无不以严格的法令、清明的吏治著称,适当加大量刑,增加违法成本,以国家强制力确保法律严格执行,可以起到以刑去刑、以法去法的效果。 二是以“利”服人。 法律本质上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应通过保护合法利益,取缔非法利益等形式来调整利益分配,规范利益关系。 严格、充分执法,守住司法公正底线,维护群众利益,可以树立人民对法治的信心和坚守法治的决心。 三是以“理”服人。 法理无外乎情理,现实中情理法的冲突恰恰体现出立法的缺失,应以此为契机开展良法的创制。 面对情理法冲突,一方面须坚持法为准绳,法统情理的原则,又要做到理为依托,理涵情法,严格执法并非冷酷无情,而是有理、有节、有温度。
司法论文范例:见刊周期短的法学普刊
第四,用好“手中之剑”,提高法治效能。 法治是一把利剑,可匡扶正义,治国安邦,用好法治之剑,使其效用最大化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于“剑”本身而言,须材质优良,锻造工艺先进,指立法质量。 法家强调的“顺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等立法原则在依法治国语境下就是要做到“科学立法”。 二是于用“剑”者而言,须做到武艺高超、剑术精湛,指执法水平。 执法机构和人员要树立法治思维,掌握执法规律,通晓执法技巧,严格、公正、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效能。 三是配上“剑鞘”,必要时收住锋芒,给用“剑”者戴上“紧箍咒”,而非依赖其“武德修养”,指法治监督。 用权力制约权力,以法治监督法治是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执法主体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不仅可以维护民众合法权利,还能保障“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充分自由。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走向善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2.
[2]江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究读本[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25.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398.
[4]刘亮.韩非子为何不评价人性之善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5(5)∶120-124.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6146.html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璇峰~鍐欎俊鎭紝鍑轰功/涓撳埄/鍥藉唴澶�/涓嫳鏂�/鍏ㄥ绉戞湡鍒婃帹鑽愪笌鍙戣〃鎸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