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留言稍后联系!

本文摘要:[摘要]受尚武之风、边塞环境和戎狄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已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具体而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尚武之风影响下河陇士人亦文亦武的两栖特色与河陇文学的质直共性;二是边塞苦寒环境影响下河陇文学的慷慨悲凉之
[摘要]受尚武之风、边塞环境和戎狄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已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具体而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尚武之风影响下河陇士人亦文亦武的“两栖”特色与河陇文学的质直共性;二是边塞苦寒环境影响下河陇文学的慷慨悲凉之气;三是华戎交会背景下河陇文学的“秦风”特质与文化品格。
[关键词]河陇文学;《秦风》;地域特色;文化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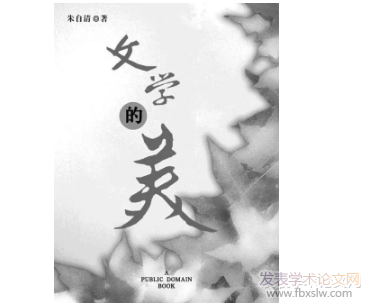
“河陇”是河西、陇右的简称,在中国古代主要指陇山以西、西域以东的广大地区。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河陇”一词出现于汉武帝开拓河西之后。在此之前,中原王朝的西部边疆仅至于陇西(陇山以西,黄河以南、以东的地区,亦即秦代陇西郡),河西地区还是月氏、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游牧栖息之地。《汉书·地理志》载:“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1]
(卷二八下,PP.1644-1645)又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1](卷六,P176),河西地区从此纳入西汉王朝的版图;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1](卷六,P189),河西四郡至此全部建立①。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西汉“初置刺史部十三州”[1](卷六,P197),凉州为十三州之一,其地东起陇坻,西至西域东界,河西和陇右同属凉州刺史部。自此开始,河西和陇右这两个互相毗邻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日趋紧密,此后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逐渐演变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河陇一体的观念也随之形成并不断深化[2]。东汉初年,隗嚣以陇右天水郡(郡治平襄,即今甘肃通渭)为中心,建立地方割据政权,其势力最盛时占据陇右、河西诸郡。
建武八年(32),光武帝刘秀亲征陇右,使隗嚣故将王遵作书劝降瓦亭关守将牛邯,王遵在《喻牛邯书》中说:“冀圣汉复存,当挈河陇,奉旧都以归本朝。”[3](卷十三,P529)其中的“河陇”,显然是包括河西和陇右在内的完整意义上的地理概念,这也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河陇”这一特定的地理概念。东汉一代,凉州刺史部下辖十郡(北地、安定、汉阳、陇西、武都、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两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4](郡国志五,PP.3516-3521),河西和陇右仍然属于同一个行政监察区。
两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河陇地区建都的五凉、西秦等割据政权,都试图将河陇地区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都把河陇地区看作一个完整的政治区域,河陇一体的观念已然成为一种共识。东晋义熙三年(407),西凉李暠遣沙门法泉奉表建康,其文曰“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云云[5](卷八七,P2264),就是以割据河陇,进而东图关中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北魏平定北凉(439)后,河陇一体的观念在北朝虽然有所淡化,但在南朝史官撰写的史书中,“河陇”一词反复出现,河陇地区仍然被视为一个完整统一的政治区域。
如《宋书》卷九七《夷蛮传》史臣曰:“晋氏南移,河陇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断。”[6](P2399)《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河南氐羌传》“赞”曰:“氐羌孽余,散出河陇。来宾往叛,放命承宗。”[7](P1033)沈约、萧子显都是南朝著名的文人学者,他们在所著史书中将“河陇”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政区)名称来使用,说明河陇一体的观念已经突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有限认知,上升为学界共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河陇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交界过渡地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地理单元。正如《甘肃全省新通志》卷六所说:“昆仑望于西,大陇雄于东,岷山亘于南,贺兰迤于北。黄河如带,泾渭夹流其中,渊渟岳峙,脉络贯通气势。”[8](P45)
由于以陇上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为主体,故简称“河陇地区”或“河陇”。历史上的河陇地区,是古代中原王朝的西北边疆地区。这里既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也是中西、胡汉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频繁的文化交流和战争冲突,使河陇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始终承担着沟通与防御的双重角色,丝路驿站和长城遗址因此成为境内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其地域文化也体现出显著的边塞特征[9](PP.12-19)。
尽管由于陇右、关中毗邻相依,历史上常常关、陇并称,陇右与关中似乎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域,但事实上,因陇山横亘于关中平原之西,是天然的地理分界线,所以陇右与关中不仅气候殊异,而且民俗风尚也迥然有别。《后汉书·郡国志》注引《三秦记》云:“其坂(陇坂,又称陇坻)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又引郭仲产《秦州记》云:“陇山东西百八十里。……度汧、陇,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乃冻解。”[4](P3518)《水经注》卷十七《渭水上》也说:“(汧)水有二源,一水出县西山,世谓之小陇山,岩障高险,不通轨辙。故张衡《四愁诗》曰:‘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10]
(PP.1511-1512)由此可见陇山高险,河陇之地气候苦寒。西汉末年王莽置四关将军,其命右关将军王福说:“汧陇之阻,西当戎狄。”[1](卷九九,P4117)扬雄《十二州箴·雍州牧箴》说:“陇山以徂,列为西荒。”[11](P337)张衡《西京赋》也说:“陇坻之隘,隔阂华戎。”[12](卷二,P49)据此可知,陇山也是古人心目中华风与戎俗的传统分界线。受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的影响,先秦以来,河陇地区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民俗风尚和文化品格。对此,《汉书·地理志》已有比较深入的总结:“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及《车辚》《四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1](卷二八下,PP.1644-1646)《汉书》的这段论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见端倪:“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13]
(卷一二九,P3262)类似的记述,还见于《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等。不难看出,河陇地区由于“迫近戎狄”“地亦穷险”,所以“民俗质木,不耻寇盗”,“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正是在质朴民风和尚武精神的浸润影响下,河陇地区自古以来不仅畜马、驭马成风,而且名将代出,甚至歌谣也深受沾溉,富有慷慨之气。《诗经·秦风》中的《车邻》《驷驖》《小戎》《无衣》等篇,或“言车马田狩之事”,或写同仇敌忾之勇,正是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文学呈现。“迫近戎狄”“地亦穷险”的边塞环境和“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的尚武风尚,使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已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格。具体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尚武之风影响下河陇士人亦文亦武的“两栖”特色与河陇文学的质直共性
如前所论,河陇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来华戎交会,民风剽悍。受其影响,秦汉以来,河陇士人大多以勇武显闻。其中天水赵氏、成纪李氏、狄道辛氏、安定皇甫氏、敦煌张氏、武威段氏、安定梁氏、北地傅氏等家族,亦文亦武,人才辈出。《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
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1](卷六九,P2998)班固此处所列诸人,除白起、王翦、苏氏父子外,其余均为河陇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河陇名将不仅勇武善战,而且也有著述传世。
《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公孙浑邪》十五篇”、“给事黄门侍郎《李息赋》九篇”、“《李将军射法》三篇”,作者分别是公孙浑邪(一作“昆邪”,为公孙贺之祖)、李息、李广三位河陇籍将军。赵充国、辛武贤等人的奏疏,文质理辨,史籍也有大量载录(《汉书》卷六九《赵充国辛庆忌传》)。作为西汉中期抗击羌胡的名将,赵充国不仅军功卓著,以“将帅之节”显名当世,其所作《上屯田奏》《条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状》《先零羌事对》等奏疏,简明扼要,条理清晰,后世也有很高的评价。章太炎《国故论衡》即云:“汉世作奏,莫善乎赵充国,探筹而数,辞无枝叶。”[14](P405)太炎先生从文体辨析的角度入手,称赞赵充国的奏疏“辞无枝叶”,显然是将他的奏疏视为汉代奏疏的典范之作。
(二)边塞苦寒环境影响
下河陇文学的慷慨悲凉之气河陇之地,古属雍州(《尚书·禹贡》)。西汉设置十三州,“改雍曰凉”[1](卷二八上,P1543)。之所以更名,与河陇地区“寒苦”的气候特点有关。《释名·释州国》曰:“凉州,西方所在,寒凉也。”[19](卷第二,P1477)《太平御览》卷一六五引《释名》曰:“西方寒冻,或云河西土田薄,故曰凉。”[20](P804)《白虎通义》卷七“八风”也说:“凉,寒也。阴气行也。”[21](P342)郭仲产《秦州记》载:“度汧、陇,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乃冻解。”[4](P3518)据此,则河陇之地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类似的记载,史籍屡见。
如《盐铁论》卷三《轻重》载:“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西方碱地),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22](P180)《后汉书》卷五一 《陈龟传》所载陈龟上疏说:“今西州边鄙,土地塉埆,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守塞候望,悬命锋镝,闻急长驱,去不图反。”[3](P1692)
《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也说:“西方者,金玉之域,砂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23](P93)以上文献中所说的西州“边郡”,显然也包括河陇地区在内,其中所描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风习,也是河陇地理风俗的真实写照。作为河陇地区东面的天然门户和地理屏障,“陇坂”山高路险,是陇右与关中的分水岭,登陇即寒气袭人,怆然伤怀。正如《陇头歌辞》所唱:“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24]
(三)华戎交会背景下河陇文学的“秦风”特质与文化品格
根据文献记载,自班固以来,学界已经将河陇文学的发轫与早期秦文化和《诗经·秦风》联系起来。但是,《秦风》中也有一些作品并非秦人居于陇右时所作,所以严格地讲,只有出现年代较早,且文本呈现的内容与秦人居于陇右时的生活风习比较接近,或者诗中描写了陇右地域风物的部分作品如《车邻》《小戎》等,才可以初步确定为河陇文学发轫期的作品[37]。比如《车邻》,其文本既体现出秦人的车马之好,又有“鼓瑟”“鼓簧”之类的礼乐术语,还有“阪有漆,隰有栗”之类的地域风物描写,郑玄《毛诗谱》确定其为秦仲时代的作品,可谓信而有征。
总之,《诗经·秦风》中的《车邻》等作品,产生于秦人崛起于陇右之时,属于河陇文学的发轫之作;《秦风》中作时较晚的一些作品虽然是秦人迁都关中以后所作,但其文化底蕴仍然是秦人崛起于陇右时已经形成的强悍劲健之气俗,所以《秦风》和陇右发现的早期秦文化遗存一样,都是河陇地域文化孕育的硕果。正因为这样,虽然秦地、秦文化以及《秦风》的外延随着秦人逾陇东进的历史步伐不断扩大,并且远远超越了河陇地区的地域范围,但其“风声气俗”依旧,深深烙刻着河陇文化的印记。正如班固所言:“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
[1](卷六九,P2999)两汉以迄南北朝,受河陇“风声气俗”熏染的历代河陇文士,或批判世道沦丧,或讥刺政治昏暗,或抒写人生失意,其作品大都充溢着刚直劲健之风和慷慨悲凉之气,与《秦风》的廉劲尚勇一脉相承。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境遇各异,但其作品所承载和呈现的精神气韵,仍然是先秦以来河陇文化的“秦风”特质和文化品格。
文学论文范例:史传文学底色与非虚构叙事手法
综上所述,河陇地区由于僻处西北边隅,历来华戎交会,民风剽悍,堪称苦寒边塞。其风土气俗,不仅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河陇文化,而且滋养了亦文亦武的河陇文士。受边塞环境、尚武之风和戎狄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河陇文学自先秦以来已经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质直劲健,慷慨任气,充溢着华戎交会的蓬勃生机,彰显着河陇文士的勇武刚强。
作者:丁宏武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7055.html

2023-2024JCR閻熸粍婢樺畷顒勫箹閻戣棄鐐婇柣妯垮皺閹斤拷

SCI 闁荤姳鑳堕崕銈夊几閸愵喗鐒诲璺猴工閻忎線鏌曢崱鏇犲妽濠殿喖娲ㄧ划娆戞啑閵堝倸浜惧ù锝夋敱閸欏繘鏌涢妷褍浠滈柛娆忕箻楠炴劙宕惰绾偓

SSCI缂備讲鍋撻柛娆嶅劤缁愭绱掓径瀣仴妞ゆ帞鍠栧鐢告偄瀹勬壆浜栭梺纭呭煐濞叉粍鐏欓柣鐘欏啫顏い鏃撴嫹

婵炴垶鎼╅崢濂杆囨繝姘闁搞儯鍔庢竟瀣叓閸パ冩殲婵犫偓閿熺姴绀嗗┑鐘辫兌閻瑧绱撴担鍝バ$紒妤€鐭傞獮搴ㄥ即閻樺苯缍婇獮鎰板炊瑜嶇涵鈧�

sci闂佸憡绮岄鎶痗i闂佸憡鐟ラ張顒勫极绾懌浜归柡鍥╁枑閸╁倿鏌涢幒鐐村

EI闂佽 鍋撻悹楦挎缁夊潡鏌i妸銉ヮ仹闁煎灚鍨垮畷鍫曟嚍閵夛箑鐒搁梺鍛婂釜閹凤拷

闂佸憡鑹剧€氼剟顢楅悢铏圭煋闁规彃妾籧i

闂佸憡鑹剧€氼剟顢楅悢铏圭煋闁规彃妯坕

闂佸憡鑹剧€氼剟顢楅悢铏圭煋闁硅京鐗猚i

EI闂佸搫鐗忛崰搴ㄥ垂閹跨兌XSourceList

闂佸憡锚濡鎯囩紞绶巗ci闂佸搫绉舵灙缂佹椽绠栧鐢告偄瀹勬壆浜栧┑顔炬嚀濞诧箓鍩€椤掑﹥瀚�

闂佸憡锚濡鎯囩紞绶巆d-婵炴垶鎼╅崢鐓幟瑰Δ鍐煋闁瑰瓨绻嶉崝鍛偓娈垮枟濞叉﹢寮搁崘顔兼瀬闁绘鐗嗙粊锕傚箹鐎涙ɑ灏版繛濂告涧閳瑰啴骞囬鐔风劯闂佸憡甯幏锟�

CSCD闂佹寧鍐婚幏锟�2023-2024闂佹寧鍐婚幏锟�

婵炴垶鎼╅崢楣冿綖閺嶎厽鈷旈柕蹇曞Т閻庡鏌涢弽顓犵窗闁靛棴鎷�2023

婵炴垶鎼╅崢鐓幟瑰Δ鍐煋闁瑰鍋涜灇闂佸搫绉舵灙缂佹椽绠栧鐢告偄瀹勬壆浜栭梺鍛娒Λ妤呮儑妤e啯鍎庢い鏃囧亹缁夛拷

2023濡ょ姷鍋涢顓熸櫠濡や胶鈻旀い鎾跺仦缁傚洨绱掓径瀣仸濠碘姍鍥у唨缂佸娉曟俊鍥煛閸垹鏋庨柛銊︽閹嫰顢欓懖鈺冃梺鎸庣☉閻楁劙宕靛⿰鍫熷€块柛鎾茬贰濞肩娀鎮楀☉瀹狀吅缂佹唻鎷�

2023濡ょ姷鍋涢顓熸櫠濡や胶鈻旀い鎾跺仦缁傚洨绱掓径瀣仸濠碘姍鍥у唨缂佸娉曟俊鍥煛閸垹鏋庨柛銊︽閹嫰顢欓懖鈺冃梺鎸庣☉閻楀繘濡甸悙鏉戭嚤婵﹢纭稿ḿ鐘绘倵濞戝疇顓虹紒鎲嬫嫹

闂佸憡锚濡鎯囨ィ鍐ㄧ婵°倐鍋撻柕鍥ф喘瀵晫绮欑捄銊ヮ洭

2023闂佺粯顨呴悧蹇涱敄閸ヮ剙纭€濞达絽鎼。鐓庘槈閹垮啫骞楅柡瀣暣瀵晫绮欑捄銊ヮ洭闂佺儵鏅╅崰鏍礊閿燂拷

2023-2024JCR閻熸粍婢樺畷顒勫箹閻戣棄鐐婇柣妯垮皺閹斤拷

SCI 闁荤姳鑳堕崕銈夊几閸愵喗鐒诲璺猴工閻忎線鏌曢崱鏇犲妽濠殿喖娲ㄧ划娆戞啑閵堝倸浜惧ù锝夋敱閸欏繘鏌涢妷褍浠滈柛娆忕箻楠炴劙宕惰绾偓

SSCI缂備讲鍋撻柛娆嶅劤缁愭绱掓径瀣仴妞ゆ帞鍠栧鐢告偄瀹勬壆浜栭梺纭呭煐濞叉粍鐏欓柣鐘欏啫顏い鏃撴嫹

婵炴垶鎼╅崢濂杆囨繝姘闁搞儯鍔庢竟瀣叓閸パ冩殲婵犫偓閿熺姴绀嗗┑鐘辫兌閻瑧绱撴担鍝バ$紒妤€鐭傞獮搴ㄥ即閻樺苯缍婇獮鎰板炊瑜嶇涵鈧�

sci闂佸憡绮岄鎶痗i闂佸憡鐟ラ張顒勫极绾懌浜归柡鍥╁枑閸╁倿鏌涢幒鐐村

EI闂佽 鍋撻悹楦挎缁夊潡鏌i妸銉ヮ仹闁煎灚鍨垮畷鍫曟嚍閵夛箑鐒搁梺鍛婂釜閹凤拷

闂佸憡鑹剧€氼剟顢楅悢铏圭煋闁规彃妾籧i

闂佸憡鑹剧€氼剟顢楅悢铏圭煋闁规彃妯坕

闂佸憡鑹剧€氼剟顢楅悢铏圭煋闁硅京鐗猚i

EI闂佸搫鐗忛崰搴ㄥ垂閹跨兌XSourceList

闂佸憡锚濡鎯囩紞绶巗ci闂佸搫绉舵灙缂佹椽绠栧鐢告偄瀹勬壆浜栧┑顔炬嚀濞诧箓鍩€椤掑﹥瀚�

闂佸憡锚濡鎯囩紞绶巆d-婵炴垶鎼╅崢鐓幟瑰Δ鍐煋闁瑰瓨绻嶉崝鍛偓娈垮枟濞叉﹢寮搁崘顔兼瀬闁绘鐗嗙粊锕傚箹鐎涙ɑ灏版繛濂告涧閳瑰啴骞囬鐔风劯闂佸憡甯幏锟�

CSCD闂佹寧鍐婚幏锟�2023-2024闂佹寧鍐婚幏锟�

婵炴垶鎼╅崢楣冿綖閺嶎厽鈷旈柕蹇曞Т閻庡鏌涢弽顓犵窗闁靛棴鎷�2023

婵炴垶鎼╅崢鐓幟瑰Δ鍐煋闁瑰鍋涜灇闂佸搫绉舵灙缂佹椽绠栧鐢告偄瀹勬壆浜栭梺鍛娒Λ妤呮儑妤e啯鍎庢い鏃囧亹缁夛拷

2023濡ょ姷鍋涢顓熸櫠濡や胶鈻旀い鎾跺仦缁傚洨绱掓径瀣仸濠碘姍鍥у唨缂佸娉曟俊鍥煛閸垹鏋庨柛銊︽閹嫰顢欓懖鈺冃梺鎸庣☉閻楁劙宕靛⿰鍫熷€块柛鎾茬贰濞肩娀鎮楀☉瀹狀吅缂佹唻鎷�

2023濡ょ姷鍋涢顓熸櫠濡や胶鈻旀い鎾跺仦缁傚洨绱掓径瀣仸濠碘姍鍥у唨缂佸娉曟俊鍥煛閸垹鏋庨柛銊︽閹嫰顢欓懖鈺冃梺鎸庣☉閻楀繘濡甸悙鏉戭嚤婵﹢纭稿ḿ鐘绘倵濞戝疇顓虹紒鎲嬫嫹

闂佸憡锚濡鎯囨ィ鍐ㄧ婵°倐鍋撻柕鍥ф喘瀵晫绮欑捄銊ヮ洭

2023闂佺粯顨呴悧蹇涱敄閸ヮ剙纭€濞达絽鎼。鐓庘槈閹垮啫骞楅柡瀣暣瀵晫绮欑捄銊ヮ洭闂佺儵鏅╅崰鏍礊閿燂拷
闁荤姴娲ら崲鏌ユ晲閻愬搫绀冩繛鍡楃凹缁诲棝鏌熼褍鐏茬紒杈ㄧ箞瀹曟瑦娼弶鍨潬/婵炴垶鎸婚幐鎼佸春閿燂拷/闂佹悶鍎村Λ鍕船鐎涙ê绶為柨鐕傛嫹/婵炴垶鎼╅崣鈧悗姘▕瀵剟鏁撻敓锟�/闂佺ǹ绻堥崝宀勵敆閻旇櫣鐭撻柟瀵稿仦閸╁倿鏌涢幒鎴敾閻㈩垰缍婇幊锟犲箛椤忓棛鎲块梺鍛婄懄閸ㄥジ濡撮崘顔肩闁搞儜灞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