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 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 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 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 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刻,恰好反映了心学新颖思想在西南边地的广泛传播,呈现了黔中王学崛起于边缘区域的生动文化景观,折射出边缘与中心交流互功的复杂历史信息。
关键词:阳明文献 《文录续编》 黔中王门 边地文化 思想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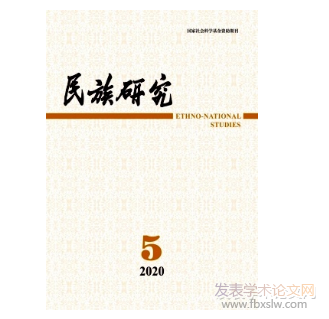
16世纪下半叶,为配合心学运动在西南边地的发展,黔中王门学者凝聚各种政治与学术资源,先后刊刻了《居夷集》《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先生遗言稿》《阳明文录》六部专书,即使较诸王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浙江、江西等中心地区,其数量规模亦足以令人惊诧,不能不说是阳明文献传播史上必须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
民族文化论文投稿刊物:《大连民族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Minzu University(双月刊)曾用刊名:大连民族学院学报;创刊时间:1999年,出版地:辽宁省大连市。语种:中文;开本:大16开,《大连民族大学学报》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大连民族大学学报》根据学校“立足东北,面向全国,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及西部地区”的办学定位,发挥学校民族学科的特色及理工为主的学科优势,坚持为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办刊宗旨,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等相关问题。
作者:张新民
贵州刊刻的阳明文献虽多已亡佚,然《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嘉靖十四年刻本及《阳明先生文录》嘉靖十八年补刻本,今皆尚存。 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凡三卷,各卷均按文体类别编次,依序为文类、书类、跋类、杂著、祭文、墓志、诗类。 据书后所附王杏《书〈文录续编〉后》,可知书之梓行,乃是因其初至黔,即有感“(阳明)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 特别是“(阳明)先生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 今日之所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 遂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以为“读是编者能以其心求之,于道未必无小补。 否则是编也,犹夫文也,岂所望于贵士者哉? ”可见是书之所以题曰《续编》,乃是补已刊的《阳明先生文录》之未载者; 所谓“新刊”云云,亦相对旧刊本《阳明先生文录》而言。 而新刊本《续编》之梓刻时间,亦必在王杏撰文之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是时距阳明先生逝世才七年,谢廷杰之《全书》合刻本尚未刊刻,流传于世之单行本,无不“各自为书”。 《续编》即早期少数罕见单行本之一,历来鲜有史志目录专书著录,即使置于阳明文献整体系统之中,也弥足珍贵。
一、地方王门学者的合作与《续编》的刊刻 [见英文版第5页,下同]
《续编》之梓行,王杏既云乃其“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则主其事者必乃其人,刊刻地亦当在黔省无疑。 考书之每卷卷末,均分三行题有“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耀州知州门人陈文学”“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字样,则参与校刻者尚有赵昌龄、陈文学、叶梧三人,后两人为阳明亲炙弟子,否则便不会在姓氏前冠以“门人”二字。 而王杏、赵昌龄亦必为服膺或私淑阳明者,刊刻《续编》一事即足可证明之。 王杏之史迹,综合历代史志考之,知其字世文,一字少坛,号鲤湖,又号日冈,浙江奉化人,嘉靖十三年(1534)巡按贵州。 时“贵州虽设布、按二司,而乡试仍就云南。 应试诸生艰于跋涉,恒以为苦”。 故早在嘉靖初,给事中田秋即“建议欲于该省开科”,然前后逾五年未有定议,至此复“下巡按御史王杏勘议,称便。 因请二省解额,命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各自设科”。 杏之勘议奏疏明确称:
贵州地方,古称荒服,国初附庸四川,洪武十七年开设科目,以云、贵、两广皆隶边方,将广西乡试附搭广东,取士一十七名,贵州乡试附搭云南,取士一十五名。 永乐十三年,贵州增建布政司,以后抚按总镇,三司衙门渐次全设,所属府、卫、州司遍立学校,作养人才,今百五十年,文风十倍,礼义之化已骎骎与中原等,乃惟科场一事,仍附搭云南,应试中途间有被贼、触瘴死于非命者。 累世遂以读书为戒,倘蒙矜悯,得于该省开科,不惟出谷民黎获睹国家宾兴盛制,其于用夏变夷之意,未必无少补矣。
足证嘉靖年间,尽管黔地“环处皆苗,其冠带而临苗夷者皆土官”,“夷多汉少”的族群生态局面,实际并未完全改变。 但儒家思想的传播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地域性的士绅阶层早已形成,诚如王阳明《寓贵阳诗》所云:“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后人据此以为其用心之苦,乃在“喜其向道知方也”。 适可见不仅府州县科考生员的数量日益增多,即独立开科设考亦成为历史的必然。 而正德二年(1508),王济(字汝楫)“巡按贵州,大有声绩,以贵州少书籍,曾与左布政使郭绅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以公之士林”。 书稿刊刻前,王阳明受王济之嘱撰序,即称是书乃“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是独为举业者设耳。 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 因而重新刊刻是书,必能“嘉惠贵阳之士”。 当然,他也特别告诫:“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 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凡此种种,在阳明看来,均极不可取。 而主事者王济又尝“谋诸方伯郭公辈,相与捐俸廪之资,锓之梓”。 故阳明又极为担心“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 尽管“地以人才重,人才以科目重久矣”,但“若作兴风励之机,则在上不在下”,因而“能本之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以致“风动远人,使知激劝”,仍为多数在黔官员的共识。 即在王济本人,也认为“枋得为宋忠臣,固以举业进者,是吾微有训焉”,用心诚可谓良苦。
由此可见,随着边地科考人数的增多,相关书籍的刊刻也开始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 《续编》的编排刊印虽较《文章轨范》为晚,但也与大量读书士子文化心理上的需求有关。 《文章轨范》或《续编》的刊行流通,如同科考的独立开设与取名额的增加一样,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宏观治理策略,从地方官员边政实情的观察视野出发,都既可在文化上“昭一代文明之盛”,也能在政治上满足“用夏变夷之意”,从而促使“夷多汉少”的边地朝着内地化或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王朝中央强化或巩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治边目的。
当然,从国家有意建构的一整套教化体系看,更重要的是,“凡古昔名贤流寓之地,必稽姓氏,为往迹之光,甚而崇庙祀景德,永流韵为人心之芳传”。 如果说稽考流寓名贤姓氏,乃至立碑建祠,使人知所景仰固然重要,则刊刻其生前撰述,从而移易地方习俗风气,影响世道人心,从而改变“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益偷,风教不振”的文化积弊现象,在地方官员看来,当也是其展开教化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 因而《续编》的刊印作为一种官方政治行为,尚有其他具有地方官员身份,署名为“贵州都司经历”的赵昌龄的参与。 赵氏生平事迹,史籍载之甚少。 考徐问《抚院续题名记》“昔司马文正公谏院题名,有忠诈直回之语,将欲揭诸后之人,俾瞩目警心,聿兴劝戒。 然则今日之求宁,非后事之师乎? 某以是惧,爰命都司从事赵昌龄董工伐石,窃取文正公之意以续书焉”; 王杏《清理屯田事议》“臣巡历贵州新添等卫地方,查据经历赵昌龄呈称,贵州屯种额例……恐虚言无凭,委官履田踏勘,已各得实”云云; 具见参与校勘《续编》者,必是上述两条材料提及之人,则赵氏除参与校对之役外,又曾“董工伐石”,以便刻写贵州抚院续题名,并受命查核“贵州屯种额例”,所报数字均一一真实不虚。 可证赵氏与王杏,二人虽在官秩有为上下之分,多有公务往来,然在私交上亦必时有过从,均心仪阳明心学,赵氏遂深得王杏信任,参与《续编》之文字校订,其名赫然列于书中。
参与《续编》之文字校对者,尚有陈文学、叶梧两人,均阳明早期黔籍弟子,分别署名“耀州知州门人”与“镇安县知县门人”,然其时早已由官任返归贵阳,实际仍以门人弟子之身份,主动承担《续编》文字校雠。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嘉靖十三年甲午五月”条载:
师(阳明)昔居龙场,诲扰诸夷。 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 提学副使席书延至贵阳,主教书院。 士类感德,翕然向风。 是年杏按贵阳,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 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 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 门人汤、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 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
席书延请阳明至贵阳,主讲文明书院,其事亦见郭子章万历《黔记》:“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席书)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 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不汩没于俗学者,皆二先生之倡也。 ”可见阳明之主讲文明书院,与提学副使席书的关系极大,也可说是地方官员有意支持的一种施教行为,因而参与听讲的生员显然数量较多,汤、叶梧、陈文学即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实乃阳明在黔期间最早的亲炙弟子,亦必列坐于“环而观听”诸生之中。
二、国家边地政治策略与纪念阳明系列活动 [6]
钱德洪提到的汤、叶梧、陈文学等人,因阳明之因缘而知儒家心性学说,晚年致仕归黔带头请建阳明祠一事,亦见于李贽《阳明先生年谱》:“门人汤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 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田以供亲事。 ”实际是时“贵阳初设府,未建庙学,权以阳明祠为学,而庙则附于宣慰学”。 故建祠之同时而阳明书院亦得以成立,可证其事之必可信据,则贵阳之建专祠祭祀阳明,较诸直隶巡抚曹煜于九华山建仰止祠祭祀阳明,时间上整整早了一年,可谓全国最早建专祠祭祀阳明的区域,足证边地民众思慕系念之情弥久弥深。 只是无论钱德洪或李贽所记,如果沿流讨源,追溯其原始出处,实皆本于王杏的《阳明书院记》。 王氏在《记》中明白称:
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 ”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虽往矣,岁时思慕,有亲到龙场奉祀者,有遥拜而祀者,予问曰:“何为遥拜而祀也? ”对曰:“龙场去省八十里,陵谷深峻,途程亦梗,士民艰于裹粮,故遥祀以致诚云尔。 ”子闻而矍然曰:“有是哉。 ”先生门人汤君、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 余曰:“公帑未敷也。 ”次日,宣慰司学生员汤表、张历等以辞请; 又次日,汤君辈又请。 予曰:“诸君之请,私情也; 问之于官,公议也。 牵之以私者徇,强之以公者矫,矫与徇君子弗取,诸公斯请,情至义得,是可以行矣。 ”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佥曰:“此舆论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祀典有弗舍焉者乎? 请许之以激劝边人。 ”遂许之。 为赎白云庵旧基,给之以工料之费,供事踊跃,庶民子来,逾月祠成。
文中提到的汤、叶梧、陈文学,以及当时尚为宣慰司学生员的汤表、张历等,显然均为黔籍人士,而受到阳明心性之学的沾溉。 其中之汤,字伯元,即贵阳人,正德三年(1508),“王伯安先生谪龙场,公师事之”,“得知行合一之学”,“正德辛巳成进士,历官南户部郎,出守潮州……甫三月,改巩昌,便道归省。 其在任思亲,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仕逾十载养全贫’之句。 居无何,中飞语归。 ”汤撰有《逸老闲录》《续录》,惜俱亡佚。 黎庶昌撰《全黔故国颂》,将其收入儒林传。
与汤同时之陈文学,字宗鲁,自号五粟山人,贵州宣慰司人,“年十余即能诗,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弘治丙子乡举,知耀州。 三年调简,不果赴。 杜门养痾,一切世故罔预。 稍闲,即与圣贤对……自耀归,日者言岁将不利公,自作《五栗先生志》”。 著有《耀归存稿》《余历续稿》《孏簃闲录》,均合编为《陈耀州诗集》。 后人认为他与汤氏,均“亲炙文成,以开黔南学业,宗鲁得文成之和,兼擅词章; 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虽以飞语见责,恬然自退,又何伤哉? ”
同陈文学一样,叶梧(或作“叶悟”)也参与了《续编》的校勘。 叶氏字子苍,亦贵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举人,曾任陕西镇安县知县,刘咸炘撰《明理学文献录》,广搜阳明弟子,“子苍”之名即赫然列于其中。 正德三年(1508)阳明龙场悟道后,讲学龙冈、文明两书院,他与汤、陈文学同时,均为最早进入师门的一批王学弟子,较诸最早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师事阳明的徐爱(字曰仁),其前后相去不过仅仅一年。 故晚年返归故里筑垣后,不仅与汤、陈文学共同带领地方读书士子请建王文成公祠,同时也与赵昌龄、陈文学合作共同校订了师门的《文录续编》。
汤、叶梧、陈文学三人,外出入仕即为肩负官守职责之地方父母官,可谓握有朝廷权柄大任的士大夫,返黔乡居则为望重一时的缙绅,乃是能够代表读书士子发言的地方知识精英。 而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贵州都指挥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贵州宣慰司在治城北,贵州布政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在治城中,贵州都指挥司在治城中西,均同在府城,彼此紧邻。 城内“官军士民移自中土,且因迁调附住于此,生齿渐繁,风化日启”。 故叶梧、陈文学虽名为贵州宣慰司人,实际也是贵阳人。 时王杏恰在巡按任上,按察院具体位置即“在会城东门内”,阳明祠及所附书院也在城东。 据此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黔本《续编》,刊刻地点尚可确定在王杏、赵昌龄、汤、叶梧、陈文学共同交往和活动的区域,即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贵州都指挥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的贵阳,可称为嘉靖十四年贵阳刻本或筑刻本。
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之修建,虽出于汤、叶梧、陈文学等地方缙绅之请,但毕竟要经过代表官方的王杏的允准,并商之“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周忠、韩士英等人,以为可以“激劝边人”,能够强化地方秩序,达致教化目的,才最终得以建成,可视为朝廷官员与地方缙绅的一次重要合作。 而筑本《续编》的梓行,既有主事官员王杏及其下属当差赵昌龄的倡导,也有叶梧、陈文学等地方精英的配合,也可说是地方政府与边地读书士子的一次成功合作,体现了国家治边大员与边地士绅文化共识空间的良性开拓与扩大。 如果以阳明心学在边地的传播和发展为观察视角,进一步向前追溯,则正德三年(1508)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与阳明往复论辩,最终为阳明所折服,并“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也可说是“身督诸生师”阳明,即以阳明的身教与言教为中介,实现了地方官员与边地读书士子的良性互动。 而阳明亦因此开始传播其与朱子有别的“知行合一”学说,从而培养了以汤、叶梧、陈文学为代表的一批黔中弟子,标志着心学思想在贵州的扎根,汤、叶、陈可称为黔中王门的“前三杰”。 此后更以修建阳明祠及阳明书院为触媒,实现了地方政府与边地缙绅的合作,不仅透过祭仪活动提升了边地士子仰止先贤之心,而且也扩大了有利于边地秩序建构的思想符号资源。
十分明显,《续编》的刊印梓行,与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的修建一样,也是国家行政理性与地方文化认同资源的一次整合,既满足了边地士子阅读心理的需要,也有裨于阳明一生完整思想的传播,遂有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第二代心学学者的兴起,当被称为黔中王门的“后三杰”。 尤其贵阳一地,“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据荆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不仅在文化风气的开启上具有引领全省的重要作用,即在国家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也有稳定整个西南的战略意义。 地方官员形成了“(阳明)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祀典有弗舍为者乎”的共识,并与地方精英群体合作刊刻了《文录续编》。 稍后黔中王门学者陈尚象为万历《黔记》撰序,也立足于国家立场着重强调:
今夫天地之元气,愈渐溃则愈精华; 国家之文治,愈薰蒸则愈彪炳。 而是精华彪炳者,得发抒于盍代之手? 其人重,则其地与之俱重,黔盖兼而有之。 贵山富水与龙山龙场,行且有闻于天下万世矣。 世有寥廓昭旷之士,亦必于黔乎神往矣。
这些足证《文录续编》的刊行,与席书要求诸生礼敬阳明为师,王杏采纳缙绅意见修建阳明祠类似,都是颇具国家边地政治策略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其发挥了学术、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符号感召力量和影响作用,蕴含着“用夏变夷”即移易地方礼俗的微妙深意。
三、黔地刊刻的多种阳明文献及其源流关系 [8]
阳明著述文献的整理刊刻,即便在僻远的贵州也远不止一次。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便明确提到:“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 又称“阳明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 具见《续编》梓行之前,黔地尚刊刻过《阳明王先生文录》《居夷集》《传习录》等书。 如论撰作先后次第,《居夷集》主要为入黔后之著述,与黔省关系最为密切,结集时间亦最早。 嘉靖《贵州通志·王守仁传》亦明载阳明“正德间以兵部主事任龙场驿驿丞,有《居夷集》传于贵”。 郭子章万历《黔记·艺文志》著录“《居夷集》,阳明先生谪龙场时撰”,亦必为黔中之刊本,均可证王杏之言必不诬。 其刊刻时间,考正德四年(1509)岁杪阳明离开贵阳赴庐陵任,途中曾有信札寄黔中弟子,信中便强调“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区区欲刊一小书故也,千万千万”。 所云似即指《居夷集》之刊刻,或阳明在黔时即有刻印是书之打算,付梓则必在正德年间后期。 阳明信中提及之黔地弟子达十七人,其中必有参与其事者,当为全国最早的《居夷集》印本。 稍后贵州按察司副使谢东山谓其“读公《居夷集》”,显然又联想到阳明在龙场“百死千难”的情形,“未尝不叹天之所以重困公而玉之成者,实在乎此”。 其寄慨如此之深,似亦入黔获读《居夷集》后才有之文字。 惜书已不传,历来著录者亦极少,然必是最早刊刻之本,似无任何疑义。
《居夷集》今存嘉靖本三卷,首有丘养浩叙,末有韩柱、徐珊跋,丘《叙》云:“引以言同校集者,韩子柱廷佐,徐子珊汝佩,皆先生门人。 ”徐《跋》谓“集凡二卷。 附集一卷,则夫子逮狱时及诸在途之作。 并刻之”。 可识丘、韩、徐三氏,均为是书之校刻者。 惟三人均未曾入黔,其书亦非黔刻本。 韩、徐二人尚在跋文落款处明书“门人”,揆诸史迹,其入门时间必在阳明离黔之后。 故钱德洪特别强调:“徐珊尝为师刻《居夷集》,盖在癸未年,及门则辛巳年九月,非龙场时也。 ”癸未即嘉靖二年(1523),据丘养浩“嘉靖甲申(三年)复孟朔”叙,知“二年”必为“三年”之误; 辛巳则为正德十六年(1521),是时阳明离开黔地已久,故是书决不当牵混为黔本。
继黔刻本《居夷集》之后,黔中尚有阳明在黔遗言专书之锓刻。 主其事者为胡尧时。 胡氏字子中,号仰斋,亦阳明弟子,好与人讨论阳明心学。 郭子章万历《黔记》尝载其事云:
胡尧时,字子中,泰和人,嘉靖丙戌进士,由驾部郎出为云南提学副使、贵州按察使。 公昔为阳明先生弟子,虽职事在刑名案牍,然谓贵阳民夷杂处,宜先教化、后刑罚。 既以躬行,为此邦士人倡。 复增修黉舍与阳明书院,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垂远,且与四方学者共焉。 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即诣阳明祠展拜,如谒先圣礼。 已,乃进诸生堂下,与之讲论学问,率以为常。
胡氏在“民夷杂处”的边地,以秩序的建构为目的,认为“宜先教化、后刑罚”,又鉴于阳明在黔省的影响,遂有一系列的行政作为。 其中搜考阳明在黔遗言,并在贵阳镌刻垂远一事,清人邹汉勋也主动加似证实,以为其“尝师事王守仁,学以躬行为本……又新阳明书院,刊守仁所著书于贵州,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 可证其事必当可信,阳明在黔之遗言,除《居夷集》外,尚另有一胡氏刊本。
胡氏刊行之书,据郭子章《黔记·艺文志》之著录,当题作“《遗言稿》”,或乃《阳明先生遗言稿》之省写。 郭氏按语明云:“贵州按察使泰和胡尧时编集阳明先生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与四方学者共焉。 胡,王(阳明)先生门人也。 ”胡氏对阳明的尊崇,观其友人谢东山的赠言:“我国家文明化洽,理学大儒后先相望,而阳明王公则妙悟宗旨,刊落支离,其有功于后学为尤大”云云,或亦可窥而知之,故书名必作《阳明先生遗言稿》,似可完全断言。 是书专记阳明谪居黔地期间遗言,就阳明一生思想发展而言,较之徐爱所辑《传习录》时间断限更早。 然成稿并锓版于何时? 考胡氏到任贵州按察使,乃在嘉靖三十年(1551),则撰稿或当始于是时,付梓则必在稍后。 刊刻地点与《续编》类似,亦当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 其时去阳明龙场悟道不久,与阳明交往之人或多健在,可说“地近而易于质实,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显然具有材料搜考核实上的便利。 其书必多有可观,兼可与《居夷集》互证,惜早已亡佚,难免不令人兴叹。
与《居夷集》《阳明先生遗言稿》一样,《传习录》一书亦有黔中之刊本。 然是书之最早编集,实因徐爱从阳明游久,乃“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遂得以成书。 考阳明与徐爱畅论《大学》之旨,乃在正德七年(1512),而今本《传习录》卷一,亦多载有相关内容,则其书之结集,亦必在是年或稍后不久。 虽规模狭小,不过十四条或稍多,然保存阳明龙场悟道后早朝教言,功亦不小。 以后薛侃据徐爱所载,补以陆澄与自己所录,刻于虔州(今江西赣州),时在正德十三年(1518),是为最早之初刻本,即今本一之上卷。 嘉靖二年(1523),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之中卷。 其他可考者,如聂豹有感于其所见之本,“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乃与陈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八闽”。 钱德洪广搜师门遗稿,合以诸家之所录,补入其撰辑,重编增刻,时间已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之后。 故王杏所言专记“门人答问”之黔本《传习录》,必在钱氏之前即早已刊刻。 如谢东山乃四川射洪人,嘉靖十年(1531)举乡试,二十年(1541)登进士,自谓“自弱冠时得公(阳明)《传习录》而读之,虽以至愚之质,亦未尝不忻然会意”,则其所读者,必乃早期刊本。 而蜀、黔两地毗邻,谢氏亦长期关心阳明在黔史迹,则其所读之书,似不能排除即黔本之可能。 因此,尽管《传习录》陆续补辑成书,“四方之刻颇多”,然黔刻本仍为早期罕见之书,透露出不少阳明文献地域传播的信息,惜亡佚甚早,学界亦鲜少知之。
前云《续编》,其书名既冠以“新刊”二字,王杏又明言:“一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 予至,属所司颁给之。 贵之人士,家诵而人习之,若以得见为晚。 ”足可说明黔地必曾刊刻过《文录》,刊刻地点亦必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惟原版印数甚少,所谓“颁给之”云云,极有可能据原刻再印,否则便谈不上“家诵而人习之”。 足证其亦为官方牵头出资梓行,不仅刊刻时间早于《续编》,即印次亦绝非一次可限。 王杏《续编》接踵后出,实即其书同一性质之补编本。
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文录》,虽久已不为人所知,幸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有明嘉靖年间刻本,书名正题作《阳明先生文录》,凡三卷三册,非特体制规模大小与《续编》相当,即称名亦与王杏所言一致。 而版刻特征虽有差异,风格仍有接近之处。 更要者即与贵阳本《续编》类似,是书卷末亦赫然题有“门人陈文学、叶梧重校”字样,并附有《祭阳明先师文》一篇。 祭文称“隆辈生长西南,实荷夫子之教”; 又云“嘉靖己丑三月戊辰,阳明夫子卒于官,讣闻至辰,门人王世隆等为位设主,哭于崇正书院之堂,复具香币往奠之”。 可证作者必为王世隆,当为阳明生前入门弟子,相互之间多有过从,故一俟闻知阳明讣信,即专设木位祭祀,严守弟子守丧之礼。 具见是书之刊刻,不仅涉及黔地及其学人,更与王门弟子王世隆有关,极有可能即是王杏所说之黔本《文录》。
四、《阳明先生文录》之补刻及其与黔地学者的关系 [9]
《祭阳明先师文》当撰于阳明病卒之后。 按史籍载阳明之卒年,当在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 时王氏(世隆)正在湖南辰州,故获知师门讣闻,已在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月,祭文即撰于是时。 是书既由陈文学、叶梧“重校”,则必与黔地有关。 考明人郭子章《黔记》,果在《总督抚按藩臬表》中有王氏题名,据此可知其字“晋叔,长洲人,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副使”。 检读《阳明先生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恰好有别本不载之阳明《与王晋叔》三通。 首通开首即云“昨见晋叔,已概其外,乃今又得其心也”; 次通又云:“所惠文字,见晋叔笔力甚简健”; 第三通复云:“刘易仲来,备道诸友相念之厚”; 则二人不仅时常见面,同时更有文字交往,从中可见以阳明为中心,其周围已形成一讲学群体,所谓“实荷夫子之教”云云,当为信实可靠之语。
然极为可疑者,王氏里贯既在长洲,万历《贵州通志》所载亦同,长洲乃在江苏,王氏何以自称“生长西南”? 而黔本《文录》与《续编》,一前一后,时序分明,附有王氏《祭文》之书,如若真为黔地刊刻之书,则必有线索可寻。 复核郭子章《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可知王氏到任贵州副使时间,乃在“嘉靖十七年”(1538),是时《续编》已刊毕,更遑论更早之《文录》,王氏可能与役? 欲回答上述问题,则必须进一步详考。
先看王氏之里贯,除长洲说外,早出之嘉靖《贵州通志》,便明载其为“辰州人”。 而辰州或称辰阳,故欧阳德亦径称“王君晋叔,辰阳人也”。 其地历来为湖南属府,再查《沅陵县志》,果然内其立有专传云:
王世隆,少英敏,强记为文,援笔立就。 年十七,中正德丁卯举人,嘉靖丙戌进士,授刑部主事,谳议精详,多所平反。 历升贵州副使,有风裁,既归,构大酉妙华书院,集诸生讲业,其中湛甘泉为铭其堂,著有《洞庭髯龙集》行世。
文中提及之大酉妙华书院,乃因大酉山妙华洞而得名,其地即“在辰阳西北”。 其所著《洞庭髯龙集》一书,早已不传,今存《辰州郡城记》一篇,或即其中之佚文。 文中总结辰州形胜,称“据楚上游,当西南孔道”,则王氏所谓“生长西南”云云,显然自有其立论根据。 足证其必为辰州人,所谓“长洲”当为音近致误。 嘉靖《贵州通志》纂成时,距王氏出任贵州副使,前后相去不过十七年,实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较之晚出之其他志乘,似更为准确可靠。
王氏既为辰州人,阳明赴谪贵州,往返均经过其地,而尤以正德五年(1510)返程就庐陵知县,滞留当地时间最长,遂多有讲学活动,并“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从游者则有“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 所谓“静坐僧寺”,前引阳明《与王晋叔》第二通亦有句云:“守仁前在寺中说得太疏略”云云,其事似均发生在同一地点,即当地虎溪龙兴寺内。 而文中之刘观时,其人“字易仲,从阳明讲学虎溪,尽得其奥妙。 阳明曾作《见斋说》遗之,学者称为沙溪先生”,显然即《与王晋叔》第三通提及之刘易仲。 具见阳明函札之前二通,必当作于其在辰州时。 第三通有语云:“路远无由面扣,易仲去,略致鄙怀,所欲告于诸友者,易仲当亦能道其大约。 ”其时阳明已离开辰州,似当撰于滁州督马政送别观时之后。 阳明尝自谓“辰州刘易仲从予滁阳……久之辞归,别以诗”,诗中有句云“秋风洞庭波,游子归已晚”,足可征而证之。 故王世隆与冀元亨、蒋信、刘观时,亦必在正德五年(1510)初,阳明离黔途经辰州时,得以面益入师门,遂形成楚中王门早期重要人物群体。
再论黔本《文录》之刊刻,《续编》既云“新刊”,则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必为旧刊,时间当在嘉靖十四年(1535)之前。 然王世隆嘉靖十七年(1538)始任贵州副使,何以能与黔人陈文学、叶梧合作,提前预刻是书? 陈、叶二氏之所为,亦径称“重校”而不云“校”? 实则王氏之到任副使,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文录》旧版尚存,而王氏似有可能获见其他异本,遂据以补刻,分置于各卷之后,痕迹宛然犹在,均不难辨识。 例如,《与王晋叔》三通,虽为阳明旧文,亦必乃王氏私藏,复加上其私撰《祭文》一篇,或如钱德洪所预知,乃“好事者搀拾”,虽文献价值极高,仍为补刻时羼入其中者。 其时王杏已离任,陈、叶二氏仍告老乡居,遂聘其就旧版重校,或有个别挖改,为官绅之再次合作。 与王杏刻本《续编》一样,补刻重校地点亦必在贵阳。 而王氏以副使身份与陈、叶二人合作,就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补刻重校,其书以其到任次年或再次年推之,亦当称其为嘉靖十八年或十九年贵阳补刻本。 以补刻重校耗费时间相对较少而论,似可即定其为嘉靖十八年贵阳补刻本。
王杏所刻之《续编》,乃是有鉴于“《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则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之贵阳本《文录》,其补刻时间固然为嘉靖十七年(1538),然其所据之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刊刻时间必早于《续编》。 故凡《文录》未载者,《续编》均悉以补入。 则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原本之锓版,虽远在西南之边城贵阳,时人每以“衣之裔”即“边裔”喻之,以黄绾刊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之《阳明先生存稿》为时间坐标,完全有可能较其更早,或与邹守益嘉靖六年(1527)刻于广德之书同时稍后。 黄绾当时即感叹阳明之书,“仅存者唯《文录》《传习录》《居夷集》而已,其余或散亡,及传写讹错。 抚卷泫然,岂胜斯文之慨”。 其所提及阳明三书(《文录》《传习录》《居夷集》)居然贵州一一都有刻本,是时阳明文献虽刻而多有凋零,黔中则一刻、二刻、三刻而分别有其藏本,亦文献学史上值得称叹之奇事。 故王世隆遂据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复校补刻,王杏刻《续编》必得以经眼并有所参考,故其所补者亦绝无一文与之犯复。 而补刻虽在后,原刻却在前,《续编》本则居中,如果再加上万历十九年(1591)贵州副史萧良干刊刻之“《阳明文录》一部十四册”,以及前述《居夷集》《阳明先生遗言稿》两书,则阳明之文录前后已有五刻,屡计出书共六部,均可视为同一谱系之文献专书,即使置于各种版本系统之中,都自成一连续性知识谱系,足可反映阳明学地域分布及传播特点。 而贵阳作为阳明文献刊刻与流通之重要地点,显然也跃跃然成为一大全国性心学传播之核心区域。
由此可见,贵阳本《续编》的刊刻,从版本渊源流变及其谱系看,实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而黔中学者陈文学、叶梧,既勘对《续编》新刊本,又重校《文录》补刻本,就阳明文献传播史而言,实属罕见,厥功甚伟。 则斯二人之史迹,亦颇值得关注。
五、阳明与黔中弟子的往返互动与情感联系 [10]
陈文学两次参与校刻阳明著述,史籍明载其“少事阳明先生”,当为龙冈、文明两书院早期受业诸生,后人以为“黔中学者得其传者,惟陈宗鲁及(汤)伯元。 宗鲁得阳明之和,(伯元)先生得阳明之正”。 阳明曾有《赠陈宗鲁》诗:“学文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泻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师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该诗或题作《示陈宗鲁》,未见丘养浩嘉靖三年本有载,必先收入黔刊本《居夷集》,始辗转录入《王文成公全书》“续编”,有邵元善“余姚王阳明先生谪官龙场时,(宗鲁)先生师事之,今《居夷集》中‘示陈宗鲁’是也”之说可证。 则早出之黔本《居夷集》,钱德洪极有可能已获见,并为其所编之《阳明先生文录》所甄采,亦难免不以阳明早年“未定之论”为由,时加砍削或删汰,未删者必多为谢廷杰《全书》本所收。 然亦可见黔本所载必较他本为多,遂有不见于丘养浩刻本,反见诸《全书》本者。
尤宜注意者,陈文学又有《借阳明集》诗:“不拜先生四十年,病居无事检遗编。 羲文周孔传千圣,河汉江淮会百川。 ”陈氏两次参校阳明文集,则经其手校之《续编》新刊本及《文录》重刻本,必常置案头,难有再借之怪事。 故其所借者,必为省外流入之本,极有可能即为欧阳南野门人闾东新刊之《阳明先生文录》。 是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刊刻于关中天水,几乎同一时间传入贵州,时距正德四年(1509)岁杪阳明离开黔地,恰好符合诗中所云“四十年”之数。 适可见黔省与中原江南,学者间之交流依然十分频繁。
与陈文学一样,叶梧亦阳明早期在黔弟子。 盖阳明之学,乃因谪官贵州而成,最突出者即龙场大悟,直契儒家圣贤新境,遂往返龙场、贵阳两地,主讲龙冈与文明书院,“当日坐拥皋比,讲习不辍,黔之闻风来学者,卉衣舌之徒,雍雍济济,周旋门庭”。 因而不仅在黔时多与诸生俎豆论道,即离黔后亦时有诗文往返,后人乃以“教何其广,而泽何其深且远”评之。 与赠诗陈文学以励志类似,阳明亦有书寄叶梧守职云:
消息久不闻,徐曰仁来,得子苍书,始知掌教新化,得遂迎养之乐,殊慰殊慰! 古之为贫而仕者正如此,子苍安得以位卑为小就乎? 苟以其平日所学薰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观感,诚可以不愧其职。 今之为大官者何限,能免窃禄之讥者几人哉? 子苍勉之,毋以世俗之见为怀也。
叶梧正德年间曾任湖南新化教谕,当地志乘称他“纯厚平实”,“立教严肃,诸生惮之”。 时徐爱当也逆沅江进入湖南西部,与叶梧谋面并带回其问候师门书信,阳明之回札即撰于徐爱自湖南返归后不久。 足证阳明虽认为“吾所以念诸友者,不在书札之有无。 诸友诚相勉于善,则凡昼之所诵,夜之所思,孰非吾书札乎? ”实际仍多有书信往返,不仅情常有所驰念牵挂,即言亦多以改过责善相勉,不啻古君子之交。 尤其阳明“赴龙场时,随地讲授”,而当地士民“悃朴少华,至道尤易”,遂培养了大批黔中志道弟子。 诚如徐爱《赠临清掌教友人李良臣》诗所说:“吾师谪贵阳,君始来从学。 异域乐群英,空谷振孤铎。 ”虽针对个人而言,亦可见群体之品性。 阳明讲学,摄受力极大,按照钱德洪的说法,“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忧愤愊忆入者以融释脱落出,呜呼休哉! 不图讲学之至于斯也”。 其所描述者,虽主要为晚年聚讲之情形,然亦可借以窥知早年传道之信息。 王杏于街头巷尾听到蔼蔼越音,也是阳明教人习礼歌诗转移民风的结果。 具见师生道义切嗟,大得孔门弦歌不辍之乐。 后人感慨“士习用变意者,文教将暨遐方,天假先生行以振起之乎”,当是透过实际观察才得出的结论。 甚至阳明离开贵阳以及逝世后,其情其义仍长久存活在黔中学子的精神世界之中,表现为他们处世行为的气节风范,转化为“觉民行道”建构秩序的动力资源。 刊刻《续编》以广流传,便是他们纪念阳明的最好方式,表面虽仅是少数个别人的行为,实际上乃有知识精英群体的支持。 其中汤、陈文学、叶梧之贡献尤足称道,他们与后来“闻而私淑”阳明的马廷锡、孙应鳌、李渭一样,都“真有朝闻夕可之意”,完全“可以不愧龙场矣”。
六、边地王学的发展与《续编》的文献学价值 [10]
贵阳本《续编》梓行之前,《文录》传世者除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外,可数者仅有邹守益所编之嘉靖六年本及黄绾嘉靖十二年本两种。 《续编》较诸钱德洪刊刻之《文录》,可谓同时而稍早,以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本《文录》与王杏刻本《续编》合观,不能不说在邹本与黄本之外,又多了一个地域性的版本系统,其文献价值之重要,自不必赘言。 而王杏与钱德洪,一冷居西南,一闹处江南,虽各不相谋,却同刻《文录》,仍可谓同声相应。 与钱氏刻本以“正录”“外集”“别录”分篇,篇下再区分文类,并一一注明年代不同,贵阳本则无有“正”“外”“别”之界划,一概按文体部居类次,不出注年月。 或许由于钱氏过于迴护师道,担心时人或后世攻诘,同时自居阳明高弟发话地位,拥有师门著述之责任处理权,遂过多重视阳明晚年定论之言,“自滁以后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而于早年文字特别是所谓“未定之论”,则凭一己主观之见多加删汰,不仅减损了分析阳明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线索依据,而且也模糊了心学传播历史必有的地域面相,即使置于知人论世整个学术传统之中,也有其违理碍情不合理之处。 幸贵阳本《续编》所载,多有《全书》本所未收者,极有可能即为钱氏有意砍削之文,皆可补充阳明思想发展及地域传播的微妙细节。 当有必要将《全书》本未载之篇,依其固有卷次列表如下:
由于《王文成公全书》梓行之前,阳明撰述均“各自为书”,谢氏所编《全书》乃仿《朱子全书》之例,凡所能见之单行本,内容大体已为其涵盖,阳明学之能风行天下,亦与其“附于朱子之学而并传”密契相关。 因而《全书》本既出,单行本遂废,不仅贵阳本《文录》《续编》少为人所知,即黄(绾)、钱(德洪)所刻之书亦鲜见流传,以致上述未为《全书》本所收之诗文,均长期存而如亡,自明迄清少见人提及,表面仍托身于欲求传世之书中,实际则沉没隐晦已近五百年。
上表所列历来少为人所知之诗文,提供了大量可以说明阳明思想发展的微妙细节。 例如,《答汪仁峰》谈到“朱陆异同之辩,固某平日之所以取谤速尤者,亦尝欲为一书以明陆学之非禅见,朱说之犹有未定者。 又恐世之学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心,将观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 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小册,名曰《朱子晚年定论》,使具眼者自择焉,将二家之学,不待辩说而自明也”。 即可见阳明因其说多与朱子有异,每每遭受巨大诽谤非议,遂急于刊刻《朱子晚年定论》,以争取更多的认同资源。 如果取该文与收入《全书》本的《朱子晚年定论》比较,尤其是比对序言中“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等自辩之语,则《答汪仁峰》无疑多提供一重了解其撰写《朱子晚年定论》的时代氛围与文化心理背景。 而《与薛子修书》强调“心之良知,是谓圣人之学,致此良知而已矣。 谓良知之外尚有可致之知者,侮圣言者也”,亦可见阳明一生学问的归宿,即为“致良知”之学。 “致良知”本质上即为本体实践之学,也是儒家学圣成圣之“正法眼藏”。 他在《寄云卿》中之谆谆告诫:“君子之学,惟求自得,不以毁誉为欣戚,不为世俗较是非,不以荣辱乱所守,不以死生二其心。 ”显然既得力于龙场悟道后的深邃生命,也反映了良知说最重要者仍在工夫,工夫则以“自得”为标准,不能不有“事上磨炼”的社会化实践过程,同时也要转化顶天立地的主体人格自我精神。
贵阳《续编》既梓刻于黔地,故凡涉阳明在黔活动,尤其与黔中王门有关事迹,不见于《全书》本者,则多载是书。 其中如《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其墓志实物1955年出土于贵阳城西,志石今藏贵州省博物馆,上有徐节篆写盖文:“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一行,志文分题“赐进士出身余姚王守仁撰”“赐进士出身通奉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那人徐节篆”“乡进士奉直大夫云南北胜州知州嘉禾汪汉书”。 而阳明之手书真迹原件,今亦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版刻典箱、出土文物、作者手迹,三者俱在而可互证,诚可谓罕见难逢,不能不称为奇事。 墓志涉及之人物,如篆写盖文之徐节,“字时中,其先寿昌人,戍籍贵州卫……幼习《易》于御史陈鉴,大奇之,遗以《易》义。 成化壬辰举进士”。 历官云南右参政、右副都御史、山西巡抚,“以廉正忤刘瑾,瑾矫制削秩,罢归。 瑾诛,奉诏复职致仕。 比老,自拟渊明。 生作挽歌行状,以示其门人汪沐,诀别如平时”,撰有《蝉噪》等集,当与阳明有过从。 墓主越氏乃詹恩母,恩字荩臣,贵州卫人,先世或可溯至江西玉山。 恩乃“弘治八年举人,弘治十二年进士,任大理寺评事”。 进士会试与阳明同科,故阳明撰《墓志铭》,遂称其为“年友”。 恩之父“评事公好奇,有文事,累立军功,倜傥善游。 尝自滇南入蜀,逾湘,历吴、楚、齐、鲁、燕、赵之区,动逾年岁”,必在云南时即与汪汉有交谊。 恩之祖父英,字秀实,号止庵,为人“豪迈不羁,成化年间领云南乡荐,授河西教谕”,“执师道,条约肃然,时用兵麓川,英画策以闻,且劾主司之过,英庙以英有识,俾赞军事,英辞不就,士论高之”。 英“卒二十年,大理寺副詹恩,公孙也。 请于编修罗玘,表其墓”。 检读罗玘《圭峰集》卷十九“墓表”,《止庵詹先生墓表》果在其中。 清贵州巡抚田雯表彰有明一代“以理学文章气节著”之黔中士子,詹英之名即赫然列在其中,亦不失为“大雅复作,声闻特达者也”。 继罗玘受詹恩之请为其祖撰墓志之后,越二十年,阳明又为其母越氏作墓表,时詹恩刚卒一年,阳明以“言事谪贵阳”,有感于“不及为荩臣铭,铭其母之墓”,乃成此文,为《续编》所收。 而越氏之“高祖为元平章,曾祖镇江路总管”,亦明初始“来居贵阳”者。 阳明尝自谓:“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 ”初到贵阳时,阳明多“与中土亡命之流”过从,后来才将交往范围扩大至“夷人”文化圈,透过《止庵詹先生墓表》一文,尤其是他与詹氏一家以及徐节等人的往来,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阳明有《龙冈新构》诗,已载入《王文成公全书》。 诗前冠有小序云:“诸夷以予穴居颇阴湿,请构小庐,欣然趋事,不月而成。 诸生闻之,亦皆来集,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 ”《续编》则有《全书》失载之《龙冈谩书》诗:“子规昼啼蛮日荒,柴扉寂寂春茫茫。 北山之薇应笑汝,汝胡局促淹他方。 彩凰葳蕤临紫苍,子亦鼓棹还沧浪。 只今已在由求下,颜闵高风安可望。 ”诗或稍早于龙冈书院建成前,然亦可见其创办书院之前后心境。 龙冈书院乃阳明创办之首家心学道场,一时诸生闻而前来听讲者,人数颇多,座下不乏附庸风雅者,然亦培养了一批最早接受并传播心学思想的知识精英。 所谓“教化大行于贵州,陈宗鲁等于是出焉”,便是当时情景最好的描绘。 陈氏《龙冈书院歌》亦有句云:“何陋轩旁石碑卧,何陋轩文壁头破。 伤悲壁破石未磨,四十余年昕夕那。 ”适可见黔中弟子阔别阳明既久,思念之情亦随年岁积久而愈加深长。 陈诗撰作时间,当与其重校《文录》同时。 而未见于《全书》之阳明《寄贵阳诸生》,也特别提到“诸友书来,间有疑吾久不寄一字者。 吾岂遂忘诸友哉,顾吾心方有去留之扰,又部中亦多事,率难遇便,遇便适复不暇,事固有相左者,是以阔焉许时”。 则信必当撰于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升南京兵部尚书,不赴并“疏乞便道省葬”稍后不久。 是时阳明已经历了“(张)忠、(许)泰之变”,虽已走出诽谤构陷危疑困局,但也亲身感受到“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即在去留未决困顿忧虑之际,亦未忘出以“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诸友勉之”等语,以激励黔中弟子。 足证其与黔中弟子书信往返,虽时断时续,然道交感应,情义不问自通,始终长驻各人心间。 阳明早期离开黔地,于镇远以书信话别时,曾有言云:“别时不胜凄惘,梦寐中尚在西麓,醒来却在数百里外也。 相见未期,努力进修,以俟后会。 ”叶子苍之名,即见于该信手迹中。 收入《续编》之《寄叶子苍》,亦必系叶氏校书时,据阳明手书载入者,均可见阳明系念贵州学子之情,终其一生,从未断过。 教泽入于人心者甚深,影响播之山川者亦广。 至于黔人之怀念阳明,则如陈文学《赠汪识环歌》所云:“慨昔阳明翁,过化此边疆。 崒嵂龙场冈,夙愿终当偿。 驾言道阻长,吾道歌沧浪。 ”经过数代王门弟子的传承,“黔之士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彬彬然盛矣”。 《续编》既刊刻于黔地,所载多有《全书》失收之文,提供了大量阳明与贵州学者往返互动的信息,透露出很多黔地王门学者活动的情况,其书自当加倍珍宝。
七、开卷展读当求得其意而能传其道 [14]
阳明之书究竟应当如何读? 钱德洪强调:“传言者不贵乎尽其博,而贵乎得其意。 得其意,虽一言之约,足以入道; 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则泛滥失真,匪徒无益,是眩之也。 ”尽管阳明“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 《续编》之编排亦依文别类,容易引起他人重词章末节,而非身心本源之学的质疑,但实际上王杏也与钱德洪一样,认为如果只汲汲于表面的辞句或文章,不知有更深一层的本真生命的实践性体验,则不仅有违于阳明传道设教的初衷,甚至也不符合黔人传播其学的本怀。 因而与钱德洪的看法类似,王杏也特别强调:
(阳明)先生谪寓兹土,遗惠在人,思其人而不可见,故于文致重也。 其勿剪甘棠之义乎? 或又谓先生之文,简易精明而波澜起伏,倏忽万状,文士视以为则焉,故若是其汲汲欤,是皆未得贵人之心者也。 先生处贵仅期月,位不过一恒品,惠泽布流,宜若有限; 而由今所垂,乃有不世之休焉。 可以观教矣。 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 知吾知也,其心之自有者也。 先生诏之,而贵人听之。 吾有而吾自教焉尔。 故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 今日之所以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 是求之者非以先生也,非以其文也,求在我者也,其或越是而在外者之是索,面对而心相非者有矣。 其肯求之耶,其肯求之于异日耶? 彼谓因惠而思,思先生者也。 以文为则,又其浅之者耳! 岂足以知贵人之心哉?
王杏既私淑阳明,入黔后又多与王门早期弟子汤、叶梧、陈文学交往过从,沃闻阳明龙场悟道各种遗事,了解“知行合一”之说,后又与阳明晚期弟子“南野欧阳德、念庵罗洪先、荆川唐顺之、龙溪王畿讲求阳明致知之学,训迪诸士,多所成立”。 今《明儒学案》引有王畿(字龙溪)回答“王鲤湖问:‘慎独之旨,但令善意必行,恶意必阻’”,工夫应该如何的答语,实出自罗洪先《冬游记》,为王杏、罗洪先、王畿三人聚会时之晤谈。 相关的讨论以后还以书信的方式继缤展开,今存王畿《答王鲤湖》亦保存了不少有趣的讨论内容,均可见他不仅与王门学者多有交往,同时也在身心之学上下过工夫。 因而他特别强调龙场悟道后,阳明在黔所“面授”者,无非是人人均有的原初本心,无非是即内在即超越的形上大道,最根本的仍是返归本源真实的自我。 《续编》的梓刻传播作为一种“垂教”方法,读其书者也决不可舍此而汲汲他求。
十分明显,王杏所表达者并非个人一己之见,而是黔中学者的集体性共识。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他所撰写的《阳明书院记》,从中可知亲炙阳明之黔中学者,嘉靖年间曾有一系列的纪念阳明的活动,最突出者即为建修祭祀专祠与刊刻书籍两件大事。 黔人所追尊者固然不能说与阳明无关,更重要的则是行人人可返身而得的天下大道。 故特节录其文如下:
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象于其外,不若佩教于其身。 (阳明)先生之教,诸君所亲承者也。 德音凿凿,闻者饫矣; 光范丕丕,炙者切矣; 精蕴玄玄,领者深矣。 诸君何必他求哉? 以闻之昔日者倾耳听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法言也,吾何敢言? 以见之昔者凝目视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德行也,吾何敢行? 以领之昔日者而潜心会之,有不以道,则曰非先生精思也,吾何敢思? 言先生之言,而德音以接也; 行先生之行,而光范以睹也; 思先生之思,而精蕴以传也,其为追崇何尚焉。
上述文字,钱德洪撰《王阳明年谱》俱载之,李贽续编《年谱》亦踵而节抄之,均可见“阳明子之学言于天下,由贵始也; 夫贵也,殆先生精神所留乎”。 故黔中王门之史迹,并非完全不为外界所知。 惟黔人质朴,“以气节相高”,不好自我表曝,虽亲承阳明之教,能在“言”“行”“思”等多方面发扬光大阳明之真精神,其行为事迹斑斑可考,仍历来鲜少有人提及,隐晦不彰者颇多。 王杏既入黔,而与黔中学者交往,可谓能知黔人之学者,故乃汲汲表彰之。 其与黔地学者合作,梓刻《续编》一书,虽只是黔中王门诸多大事之一,实亦王学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因缘。 读其文非仅可了解黔中王学早期发展情况,亦有裨于《文录》之阅读及其理解。
《续编》原刻本“刀法朴茂,别具古趣”,不仅为黔中难得一见之珍本,即使置诸全国范围也堪称佳椠,当然更是阳明文献学研究必读之要籍。 该书一方面以影印存真的方式再次刊行,俾读者一睹珍本原貌; 另一方面也以点校整理的方式锓版重梓,助学者开卷展读、身心受益,庶几前人代代相续之道统学统不致消歇中辍,贤者能够发扬光大并垂久于将来。 兹事体大,乃公诸世人,以广流传,并盼赐教焉。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6210.html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