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美的本体论关系到世界的存在方式。 世界万物的存在方式有三: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主观互动决定的存在、以虚体空性的形态存在。 中西印文化对这世界三种存在的不同强调而形成的理论整体,决定了中西印美学在美的本体论是不同理论建构。 关
摘要:美的本体论关系到世界的存在方式。 世界万物的存在方式有三: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主观互动决定的存在、以虚体空性的形态存在。 中西印文化对这世界三种存在的不同强调而形成的理论整体,决定了中西印美学在美的本体论是不同理论建构。
关键词:美的本体论; 中西印美学; 存在形态; 理论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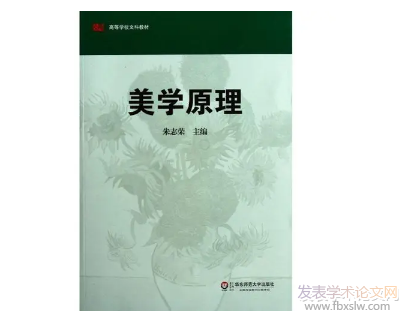
作者:张 法
一 三个命题与美学之难
人生在世,皆知世界有美,皆怀向往美、追求美之心,皆有过拥有美、欣赏美、陶醉美之时……然而,倘如你遇上一个像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猛然地问你一句:什么是美? 不知道你会不会给出一个正确的回答。
美学论文范例:浅析美学理论变迁对动画片镜头语言的影响
在《大希庇阿斯篇》中,那些被问到的人,最初都信心满满地给出自己的答案,对那些花样百出的回答,倘作一离形得似的重组,可为:一个说,美就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漂亮姑娘。 另一个说,美就是我家庭院中的那朵开得红艳艳的鲜花。 还有一个说,美就是我爸书房里那个精致的陶瓶。 第四个说,美是他们城邦神庙中的阿波罗雕像……当这帮人一一说出自认为不错的答案之后,苏格拉底严正指出,他问的不是某一具体人、花、器皿、雕塑是美的,而是问的为什么这些具体事物能够被称为是美的? 人、花、器皿、雕塑,明明是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东西是美的。
在苏格拉底的问题里,包含着很多内容,就柏拉图的本意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从理论上去思考美的问题。 从西人的思维方式来讲,就是,宇宙中任何事物是处在现象与本质的结构中,人、花、器皿、雕塑等现象事物是美的,这是现象; 决定这些人、花、器皿、雕塑为什么是美的,是本质。 现象各不相同,本质只有一个,知道了这个美的本质,我们才从理论上知道了什么是美,才可以从理论讲清楚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美。 因为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文化开始建立起了美学,即关于美的理论形态。 柏拉图之问也成为后来很多美学著作的基本结构:首先是关于美的本质定义,然后进入到由美的本质决定的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乃至科学美,以及美的基本类型、优美、壮美、崇高、滑稽、悲剧、喜剧……然而,第一、这一由柏拉图确立的研究美学的方向或曰讲述美学的方式,只是一种西方文化才有的方式,各非西方文化,进入世界现代进程之前,都不是用这种理论方式,而是用自身文化的特有理论方式去谈论美,而且讲得与西方文化一样的精彩。 第二、西方文化自身,自柏拉图建立美的本质之问以来,历尽艰辛,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之问一千多年以后,美学方在德国的鲍姆加登那里,正式成为一门学问,并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到完善。 而且,康德、黑格尔取得胜利不久,这一从柏拉图-鲍姆加登-黑格尔的西方古典美学类型,又遭到20世纪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群起否定。 本来,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提出美的本质,并对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追问之后,发现对这一提问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因此,这一篇具有伟大开创性的对话录,以一句令读者失望的话来结尾:美是难的。
从柏拉图的一声叹息,到西方文化建立美学的拖拉,到各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不用西方美学的方式去谈论美,就可知,柏拉图确实面对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美是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 这里且用三个西方型的命题,来呈现美之难。
这朵花是圆的。
这朵花是红的。
这朵花是美的。
首先要解释一下,所谓西方型命题,即不是中文古代文献上一再讲的“命题立意”之类,而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讲的proposition(命题),用学术方式讲深奥一点,命题是指一个判断句来表达的语义,讲通俗点,命题是西方文化得出真理的方式,它以判断句的形式,对作为具体事物的“主项”(这朵花),通过具有逻辑严格性的“是”或“不是”的“判断”,与一个用谓项表达的“本质性”的概念(圆、红、美)关联起来,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结论。 这种所谓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把事物与世界用概念进行逻辑组织,形成正确的命题,由一个个命题的提出,最后形成正确的理论体系。 命题的正确保证着理论的正确。 确保人达到了客观真理。 这是一种西方型理论方式,但进入这一方式,并将之关联到其非西方文化(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方式,却可以使世界的性质和理论的性质,得到理论性的理解,同样,也使本文的主题,美学问题,得到基本性的理解。
在上面的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讲花的形状。 物的形状是由物的客观物理事实确定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状态而改变。 这是一个正确的具有必然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命题。 谁要说这朵花不是圆的,肯定错了。 第二个命题讲花的颜色。 物的颜色并不是物本身固有的,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是由光波,波长800-390纳米的光波可以形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 二是由花的性质。 光照射到花上,这种花的物理性质吸入其他波长但使之不显,而只把与红相关的800-600纳米的波长呈现出来,形成此花的固定色。 三是由人眼的性质。 人眼在生物进化中,形成了杆状细胞和椎状细胞为主的视感官,人有如是的视感官,方能看见800-600纳米光波在此花上所呈现的红。 许多食草动物看不见颜色,只有灰色视觉,大部分哺乳动物,视觉等同于色盲之人,有些动物比人色觉更好,很多昆虫可看见800纳米-1毫米长光波的红外线之色,蛇能看到400-10纳米光波的紫外线之色。 四是由人脑的性质,花之红在光的变化并与周围其他事物的互动中,会发生不同色彩变化,但人之看花,由椎状细胞经神经系统传导到大脑皮层,在由文化形成的心理定式中,认知到红是此花的固有色,使花的红在人的感知中具有恒定性,不管花在昼夜晨昏阴晴的光线中怎样变化,都被认知为红。 ①花之红还有更多的内容,与这里的主题无关,仅以上三条可知,花的红乃主观互动与合和的结果。 虽然花之红是一个必须依赖于人型的视感官方成立,但对人来说,花之红仍为一种与花之圆一样的“客观事实”。 如果你不是色盲又说此花不是红的,那肯定错了。 总之,花的红与花的圆一样,正确答案都只有一个,都是非常符合建构一种西方型的理论的命题。 下面到第三个命题,就开始出大问题了。 你说:这朵花是美的。 他说不美。 你却不能说人错,顶多只能说,他的审美观与你不同。 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两个命题都有客观(或加上主体生理感官结构而来)的物理标准,而且都可以把命题与客观事物进行对照而进行验证。 但对花之美,既不没有客观的物理事实,花之美,不是花之蕊、之瓣、之叶、之茎、之色、之香,而是既在之蕊、之瓣、之叶、之茎、之色、之香里面,又是超出这些因素,且难以形求的东西。 知道了花之红可以从主体方面去找原因,花之美呢,在那些感受到花之美的人的生理感官中,却找不到感受美的专门细胞、专项感官,专门的皮层区域。 人的生理心理机能感受到了花的美,却不能科学地实指是怎样感受到的美。 对花的审美感知和其他感知,审美情感和一般情感,审美愉快和一般愉快,在生理和心理上找不到确切实在的定位。 从科学上和理论上讲,你说这朵是美的和他说不美,在理据上同等。 这就是美的理论之难。
三个命题中,第一个命题是具有宇宙普遍性真理,圆是一个放之天地而皆准的客观存在,并随时可以验证。 第二个命题只具有人类普遍性真理,是人与世界互动后的产物,仅在人中才可以验证成功。 第三个命题只有部分真理,而且这部分真理无法验证(花中找不出美的因子来)。 重要的是,通过这三个命题透出的美的理论建构之难,却通向着西方人最初并未想到,而又确实存在着的人身于其中的世界构成。 而理解这一世界构成,方能使人体悟到美的理论建构之难对人类的意义。
二 三个命题与世界结构和理论类型
以上的三个命题,从第一到第三,真理的普遍性范围越来越小,验证越来越难。 又恰巧透出了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世界的构成,二是理论的特性。
先讲第一个方面。 人身于其间的客观世界,以三种基本方式存在:一种恰似花之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有人还是没有人,这一类世界都是如此,永远如此。 另一种宛如花之红,是依赖于人的性质,在与人进行互动中,方成为如此的存在。 在一些与人不同的物种眼中,如在食草动物、许多昆虫、各类蛇虺的眼中,世界呈现为别一种模样。 还有一种仿佛花之美,它在世界中存在着,但乃虚体,虽为虚体,又从具体事物上显现出来。 对之要想确知,却无从寻觅,用中国《老子》第十四章的话来讲,是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而得不到的存在。 ②用印度《歌者奥义书》的话来讲,它是“人体之外的空”“人体之内的空”“心中的空”。 用司空图《诗品·缜密》的诗句来讲,乃“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以上的这三种形态又浑然一体地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存在着。 人在自身的演进中,展开为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面对如此的世界,进行整体思想时,各按自身的实践方式,对世界进行观察、思考、组织,得出自认为应是如此的世界图景,各有不同。 人类从数百万年产生以来,从思维方式和思想类型上看,经历了五大阶段,以虚体之灵为主的原始阶段,以神为主的早期文明、以哲学理性为主的轴心时代,以科学加哲学理性为主的走向全球一体的现代时期,以电视-电脑-手机的“电文化”为主的多元哲学思想互动的全球化时代。 在这五大时期,三大地区的哲学理性的思想升级最为重要,由地中海的希腊和希伯来综合的西方思想、由南亚的奥义书和佛教形成的印度思想、由先秦诸子形成的中国思想。 三大文化形成人类思想的三种基本形态,并开始对美的理性思考和理论组织。
(一)“花之圆”型的思想与西方的世界结构
西方人面对三类一体世界,把思想着重点放在“花之圆”这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形态,并以这一形态为基础或曰为主干,建构起包括“圆”“红”“美”在内的整体世界的基本模式。 这一以“花之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几何学为基础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学院门牌大书:非懂几何,切莫入门。 几何学专注物体之形体(比例尺度),对形体进行精密计算(数),在计算中进行严格推理(逻辑)。 希腊人看待世界进行思想的三大要项,美的“比例”、精确的“数”、严格的“逻辑”,都来自一种古老的语词:逻各斯(logos),逻各斯被中国人译为“道”。
这一来自古代思想又加以改进了的逻各斯之“道”,以几何学的三大要项为指导,就可以面对任一事物或整个世界,说出明晰确定的“是”(希腊文的ε? μ? 即英文的to be)来。 当理性哲学在希腊产生之后,事物和世界的存在,通过“是”而得到确定。 因此,“是”成为西方哲学最最重要的东西,说“是”就意味着有物“存在”(而非“不存在”),存在之物一定是“有”(而不是“无”),这一“存在”之“有”一定乃正确之“是”。 正是从“是”开始,按花之圆的方式运行,曾为流动性的逻各斯变成了严格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专用来证明“存在”的“有”的世界在何以为“是”。
且看希腊人是怎样从花之圆这一方式出发,并按照花之圆之“道”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念的。 对世界的认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具体的单个物体,可称为个物; 二是同类个物的集合,可称为类物; 三是由一切个物和类物形成的世界整体。 对三类事物,希腊人用花之圆的方式进行认知,并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
每一具体之物,是多种属性的统一。 比如人,有身高、重量、肤色、性别等自身的身体属性等,同时与他物和世界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并由这些关系及关系物产生并决定着一些属性,比如地点(雅典、商店、运动场)、时间(童年、中年、老年)、拥有(宫殿、草屋、技能、知识),还有具体的存在状态,如言谈举止姿势,在与具体相关物中是主动的(医生做手术)或被动的(病人被做手术)。 在希腊人看来,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属性可以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贯穿于这一物体从产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决定了这一事物之为此物,非本质属性则只在此物的某一阶段存在。 因此认识某一事物,就是认识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 希腊语与西方语一样,一个词有多种形态,人要认知物的属性,最后的结果要用ε? μ? (相当于英语的to be和现代汉语的“是”)来表达。 因此,用是(ε? μ? )的阴性分词oυσ? a(英译即substance)来指具体个物的本质。 中文翻译为实体或本体。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实体或本体或本质来自“是”,由求是思维直接推出,就算得其要旨。 这一点在英语中显得更清楚,就是从对一物认知开始的to be(是什么)到认知结果的being(此物的本质之是)。 这里being已经排除了所有非本质的to be(是),而只留下本质之是(being)。
对个体之物的认知,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把个物归为类,比如人,归于动物,再归生物,如此等等,同一类就有这一类的共性。 然而个体之物是多种属性的统一,属于他的各种属性,都有其类,有实体性的属体归类:人的身高归为以米、厘米、毫米相关的长度一类,体量归于轻重的重量一类,肤色属于色彩一类,人种属于家族、民族一类,如此等等; 还有各种抽象品质的归类,如善恶属于道德,美丑属审美,脾气属于气质,兴趣属于爱好,如此等等。 很多属性,对于个体来讲,是非本质的。 但对这一属性存在于各种不同事物中来讲,又有其本质,比如红色,花有红的,布有红的,墙有红的,血是红的,火是红的……红作为这些不同事物的共性,有一个本质,希腊人把这种类物的本质称为ιδεa(理式),中外学人都研究了,在希腊语中,“理式”(ιδεa)也与“是”(ε? μ?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③,可以说也由“是”而来,也乃“求是”思维导出的结果。 在类物层面的求本质中重要的是,不仅是在个物整体性种属体系内追求共性本质,如星、云、山、河、人、兽、花、草……而且是个物的分离性属性中追求共性本质,如颜色、长短、高下、善恶、美丑……这里的对象,不是某一个物的整体,而是其部分,正是在这里,本质追求进入到一个更加抽象和更加复杂的层面。 通过各类物种中的分离属性进行跨种属的重组,呈现了一种世界的分类方式。 而这种新方式,又是在个物本质追求的原则和逻辑上进行的,把抽象的属性,如数量、善恶、爱好等,转变为实体的东西,可以说,把花之红按花之圆的方式进行。 忽略了花之红的复杂性,把它放进了花之圆的普遍性的推导中。 在类物层面的求是运行中,美的本质问题会与红的本质问题一样被提出来,但却难以像红的本质得到解决。 其解决要从更高的层面才可得出。
把世界万物进行类物层面的分类,一级级上升,最后达世界的整体本质。 世界中个物由oυσ? a(substanc,实体或本体,即个物的本质之是)可以得到确定,世界中的类物由ιδεa(idea/form即理式即类物的本质之是)可以得到确定,世界的整体就是个物和类物的大集合。 对个物和类物的本质的确认,是从认知的“是”(ε? μ? 即to be)到本质的确定之是(oυσ? a)和类物的本质之是(ιδεa)。 同样,对世界整体的确认,也是从认知的“是”(ε? μ? 即to be)开始,到确定的o? (世界整体的本质之是),在希腊文中o? 是ε? μ? 的中性分词。 用英文来讲更为清楚,就是从to be(是……)到Being(世界整体的本质之是)。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可以把希腊文三个层面的本质oυσ? a、ιδεa、o? ,都按essence(本质)理解即可。 从词汇史讲,个物之是的oυσ? a在闪米特各种语言中去跨界旅行一圈之后,再被翻译回拉丁文,成了essentia,又成为英语和法语的essence(本质)④。 但同时要知道三个层面的本质又是有差异的。 这一差异,本来大致可以对应于“花之圆”“花之红”“花之美”,但希腊人面对三个不同层面却用“花之圆”型的“是”一以贯之,从而形成了西方世界观的基本特质。
希腊人在世界的三个层面进行的如上的知识进路,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从西方思想的特性本身,二是从世界构成的三个层次进行。 先从西方思想的特性本身来讲。 如上的三个进路使西方世界成了一个实体-区分型的世界。 这一实体-区分型世界有如下特点:
第一,世界是由实体构成的。 凡物都是实体,实体可以大如地球,小如原子,但都是实而非空,构成西方的物与空间的关系,作为实体之物存在于空间之中,在空间中运行,但与空间是没有本质关系的。 占有空间和征服空间成为西方人的特征之一。 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约前55),用诗的语言,呈现了西方实体宇宙的基本结构:
独立存在的全部自然,是由于
两种东西组成,由物体和虚空
而物体是在虚空里面,在其中运动往来。 ⑤
第二,实体是有本质的,并由本质决定的。 本来,物体存在于时空之中,是在时间中变化的,但从个物本质理论,变化的是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不会改变,这样时间带来的变化无论多么重要都与本质无关。 西方文化形成的排斥了时间的空间性文化。
由以上两点,实体在本质上与空间无关,也与时间无关。 形成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物体是独立的个体,在本质可以与他物完全区分开来。 认知物体应当对物体本身(排除掉所有关联)进行认知。 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形成了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 运用于物,形成了亚氏逻辑中的物和实验科学中的物。 这两大使西方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要项的理论基础,都在个物作为个体的独立性。
第三,实体是可分区的。 个物可以与他物区分开来而独立。 同样个物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与之区分开来进行独立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西方理论的基础,也是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开始的本原追求和元素分析。 由于世界三个层面在本质上的实体性。 可分性要有一个终点,在物体的最小方面是:原子(原子的希腊词? τομον的词义即为不可再分); 在理念的最后核心是理式,在世界的最大方面是Being(有-在-是本身)。 这样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最大的不可变无的Being(大有),构成了对在最大和最小之间的万物的可分性认知。 而观念上的最后的理式,成为对世界中从最大到最小之有进行分析的理论工具,成为学科分类的理论基础。 因此,由区分而达到本质成为西方思想的基本方式。
第四,实体是可以定义的。 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特有实体性区分性的本质追求,形成特有的语言方式,用定义的语言形式,即“是……”对本质进行明晰的语言表述。 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给出“定义”,如:“点是没有部分的”“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圆是由一条线包围成的平面图形,其中有一点与这条线上的点连结成的所有的线都相等”。 ⑥
第五,实体世界是二分的。 人对世界认知,一旦像希腊人那样,一方面用实体区分的方式,定在如上所讲的,使个物在本质上与空间区分开来、与时间变化无关,可以进行层层面面的细分细观,从而得到关于个物的明晰知识,另方面,人又是靠工具(物质工具和思维工具)去认识世界的,人的工具发展的程度又决定了,用实体区分的方式,只能认知一部分个物和类物,从而世界被区分成了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两个部分。 作为这两部分统一的Being(整体的存在之是),是用实体-区分型思维,由近到远或曰由部分到整体的方式推论出来的,未知部分被认为与已知部分有相同的性质,可以由人的工具一步步发展和提升而被不断地认识到。 因此,对西方人来讲,未知世界,从工具的严格性来讲,是未知的,但从由工具进行的逻辑推导来讲,又是已知的。 然而,因为这一已知还未经过验证,因此,从哲学上讲,就是希腊人得出来的Being(整体之有的存在),从希伯来人得到的宗教上来讲,就是上帝。 希腊人的世界整体需要一个“整体之有的存在”或上帝来给自己以文化自信。 因此,当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在罗马帝国后期结合成基督教思想,并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时,早期的希腊文本把《圣经出埃及记》(3.14)中“eheyeh asher eheyeh”(简体中文和合本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公元前2世纪的七十士译本用希腊文译为“Ego eimi ho on”(用英语讲即“I am The Being”,用汉语讲就是“我乃整体之有的存在”。 总之,上帝等于Being(世界的整体之有的存在),是西方思想运行的必然结果。 但这并没有改变世界被区分为已知和未知两个部分的事实,只是每当已知部分有了质的提升,世界的整体的性质就会进行一次新的改变,古代科学得出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型的世界整体,到近代科学成为哥伯尼和牛顿的世界整体,到现代科学又成了爱因斯坦型的世界整体,但无论世界整体的性质怎样随科学工具和思想的进展而提升,世界整体都不会改变其作为Being或上帝的性质。 从宏观上讲,可以说,希腊的科学-哲学与希伯来的上帝一道,消灭或排斥一切非科学的灵或神的异教思想,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具有实体-区分性质且有着客观规律的物质世界。
以上五点,是从西方思想自身的视角去看的,这样的好处是不但可以按其所是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可以对之有因换位思考而来的同情的理解。 现在需要从世界构成的三个层次去看西方的实体区分型思想,从而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是怎么“走偏”的。 西方思想可以说都是从“花之圆”得出来的,就世界本就存在着“花之圆”来讲,西方通过把个物与他物区别开来,与空间和时间区别开来,乃至可以宇宙整体区别开来,而取得了最明晰的结论。 西方文化的两大基础,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然而,当进入到世界构成中的“花之红”部分时,西方人仍是用“花之圆”去思考,从而把“花之红”不是按照本来方式看成主客互动的结果,而仍看成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正因为这样看,产生了很大困难,因此西方哲人把颜色排除在理论思考之外,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的理论成果都与颜色无关,近代哥白尼、伽里略、开普勒的理论成果,也与颜色无关。 当牛顿通过光谱把色彩纳入进科学理论之后,西方理论在色彩上仍充满一个又一个的困惑。 关键在于色彩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的问题,而是一个主客互动的问题。 直到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升级,方把主客互动而形成的世界构成部分,纳入进了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主流观念之中,主要体现在相对论、量子论、现象学、符号学,以及各类后现代的思想中。 同样,当西方人面对“花之美”时,仍是按照“花之圆”的方式去思考,仍把“花之美”看成一个与“花之圆”相同的实体结构,而不是按照花之美的本来那样,看到一个虚实结构且重点在虚。 这样虽然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进入到对美(以及与美相同性质的事物)的理论思考,但对美的理论一直困难重重,虽然以花之圆的方式去建构美的理论,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按照西方实体区分型的理论的严格性来讲,却难讲圆满,特别是相对论以及时空一体论的产生,量子论以及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出现,才把谈论和建构美的方式,转到了虚实结构上来。 然而,由于西方思想是在实体-区分基础上形成的,当自20世纪开始转到主客互动论和虚实结构论,也是由实体区分型思维推动下一次次的思想升级后出现的,在讲主客互动论和虚实结构论时,仍带着较强的实体-区分的基因,西方思想的调整还在演进之中,但只要知道世界是三种层面的统一体,对于西方思想从古代到现代以来的复杂演进,应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二)“花之红”型的思想与中国的世界结构
中国人面对三类一体世界,把思想着重点放在“花之红”这主客互动而形成的存态形态,并以这一形态为基础或曰为主干,建构起包括“圆”“红”“美”在内的整体世界的基本模式。 这一以“花之红”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道”的字形和词义中。 下面是道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
(严一萍《释 》) (《散盘》)
甲骨文的道,由 (人)和 (道路)两部分组成,金文中人简化为首和止(脚),重在脚,止又可换“寸”(肘),重在手。 正书里止(脚)或寸(手)之义并在辶(辵)里,只有“首”,道路之
(行)也化入“辶”之中,成为(首加辶之)道。 因此,道,是人行走在道路之中。 道字所内蕴和反映的观念,回溯到远古,最初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日月星运行的天道,道中之“人”实为道中之神,比如,当人以太阳为鸟,这个人即鸟头人身的太阳神。 与之相应,人在地上的仪式中,族群的巫王在与世界整体同形的亚形仪式空间中模仿太阳神,以鸟头人身的装饰举行仪式,太阳运行被文化地想象为地中巫王的舞步运行。 巫王在仪式空间的道中模拟各种天地神灵的舞蹈性行走,被想象为世界本身的客观性运行。 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这一观念包含如下内容:天地是运行中的客观存在,但这一运行是需要人去认识的,因此孔子讲“非道宏人”,而是“人能宏道”(《论语·卫灵公》)。 上面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型的主客合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的宏道,不是人可以自由去做,而是必须要按照道的规律去做,这就是屈原强调的:“禀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橘颂》)。 人参天地,并在参天地的“参”中,形成中国型的主客互动而来的世界图景。
参天地的“参”的前提,是一种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中国人对世界的整体认知,来自远古以来的立杆测影。 在村落中间空地立一中杆,进行日月星的天文观测。 《周礼·考工记》讲了天文观测中昼观日影和夜观极星的重要性。 太阳一天的东升西落在中杆的投影,构成了东西方位; 一年的南北移动与回归构成了南北方位; 冬至日影最短,夏至日影最长,春分秋分日影等长。 立中的日影观测,得出的是(日月季年之)时和(东西南北之)空合一的世界整体。 从时空合一的世界整体去看世界万物,是中国世界观的一大要点。 在北纬36°的黄河流域,各种星辰在一年中有出有没,但天北极的星区却是从不没入地平线的常显区。 中国的星相,形成了以北极-极星-北斗为中心,日月众星围绕这一中心运行的天文常态。 天上的中心是北辰,地上的中心是京城,各省城州城县城围绕着京城这一中心,进行政治运作。 以中为核心来看待世界万物,即古人一再强调的“尚中”“执中”“中庸”( 郑玄和孔颖达注《中庸》时都讲:庸,用也。 中庸即用中),是中国世界观的又一大要点。 在中国天相中,北极是天空中一个几何点,极星是离北极最近的星,由于岁差,北极附近的星辰会缓慢移动,因此极星约一千年会变动一次。 虚体的北极与具体的极星,构成了虚实的关系结构。 理解了北极为无,极星为有,可以体悟《老子》以“道”为“无”的思想和“道生一”的思想。 曾离北极很近后又稍远的北斗,因其随地球自转而绕北天极作周日旋转,又随地球公转而绕北极作周年旋转,斗柄或斗魁的不同指向,与四季的变化形成了同构的对应关系。 由天之中的北极、极星、北斗引导日月星的运行,引起天地互动,产生万物。 中杆的天文观测中,只有日月星在轨道上运行,天地互动与万物是怎么产生的呢? 古人认为是气。 气是中国哲学与道同样重要的核心概念。 《春秋·文耀钩》曰:“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 含元出气,流精生一也。 ”《御览》卷22引徐整《长历》曰:“北斗当昆仑,气注天下。 ”《鹖冠子·环流》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 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天地互动与万物生灭,是由气的运行。 道,来自日月星的运行轨道,(轨)道看不见,又确实存在,可从日月星的移动体会出和计算出来。 道是由(日月众星的)实和(运行之道的)虚的统一。 日月星的运行可明见可计算为“实”,但其运行引起的天地互动及万物生灭,实际发生着又不可见、难计算,为“虚”。 由此,中国世界的又一大要点突显出来。 中国世界是一个气的世界。 前面讲过,人类思想的演进,是从原始文化之灵到早期文明之神到轴心时代的理性,从本原上讲,轴心时代的理性思想从来源上,都与原始时代变动不居的灵相关,西方的逻各斯与灵相关且由灵而来,印度的大梵与大我以及幻相,都与灵相关且由灵而来,中国先秦理性化的气,也来自原始时代之灵,只是将之做了理性的提升。 知晓中国哲学中气的来源和理性化之后的性质,是理解中国思想的关键。 这里,主要从已经理性化的气的特点来讲,中国的世界是一个气的世界。 因气的重要,可以得出中国世界的基本特点如下:
第一,中国世界是一个气的世界,气化流行,产生万物,物灭又复归于气。 气是虚体,成物后有形而为实体,但气仍在物中,并成为物的根本。
第二,中国世界是一个虚实结构世界。 其一,世界整体是虚实结构。 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动植,皆由气而生,带气而行,气灭而亡,复归世界之气。 其二,具体的个物是虚实结构,任何一物,可以有很多属性,但各种属性,都可以归为由外在之形和内在之气构成,形成古籍中常讲的“形气”之物。 其三,类物是虚实结构,中国类物有两个方面之虚,一方面在与西方似的分类中,如青赤黄白黑为颜色类,角徵宫商羽为声音类,酸苦甘辛咸为滋味类,有自身的实与虚。 另一方面,色声味等类又属于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色之青、声之角、味之酸等,都属于五行之木,五行即五种基本的运行之气,这是与前一种类不同的另一更高的分类,这种类进入到宇宙整体的关联。
第三,中国的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 气的世界决定了中国世界是一个虚实结构且以虚为主的世界。 以虚为主,即个物的根本在于其中虚体之气,类物的根本也在于其中虚体之气,更重要的是,个物的虚体之气与类物的虚体之气,都与世界整体之气紧密关联在一起。 个物不能与类物区分开来,与世界整体区分开来讲自身的本质。 没有西方式的独立性,而是一定要与类型相关联、与世界整体相关联方形成自己的个体的丰富性。
第四,中国世界是在时空一体中运行的世界。 中国的道和气都强调的是运行之“行”,道,一是讲决定世界运行的根本本质,二是讲这一根本本质只有在运行中方体现出来,但在运行中体现出的道也不是道的全部,因此,道从根本性来讲是“无”,但人又可以在道的各种体现中去体悟认知运行后面的道。 这就是体用不二,知行合一。 道的运行,既是在时辰天月季年中的时间中运行,不同的时点,个物和类物都呈现出不同的外在面貌和内在气质,又是在东西南北中的空间中运行,不同的空间,个物和类物都呈现出不同的外在面貌和内在气质。
第五,这样一个气化流行、虚实结构、相互关联、时空合一的世界,是人用自己之眼去观、用自己之心去思而体悟出来的。 《周易·系辞下》讲:“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成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包牺即远古的伏羲,他立于原始仪式的中杆之下,仰观俯察、远近往回地游目,去观看按着道的规律、气的流动,在天上地下、四方远近运行着的世界,从中体会出了万物运行的规律,天地后面的真谛。 这里包含个物和类物于其中的世界整体,一方面是按自然的本来面貌出现,另方面,又是在他的眼之所视的“观”中出现的。 世界的呈现是一种心物互动而产生的结果,按如花之所以呈现为“红”。 孟子讲,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强调主体的作用,庄子讲“以天合天”(《庄子·达生》),即以人来于自然的天性去行动以符合客观运行之自然。 张载讲“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陆九渊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年谱》),要强调的都是,只有当人用主体本然的方式去看,世界就是以符合主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人的观照中,世界呈现是以人的主体能力能够见到的方式呈现的。
由于中国思想是在花之红这一层面强调主客同一和心物同一,因此,中国人虽然对于花之圆的形的一面也重视,但并没有放在首位,而是要服从于花之红的主客互动,因此要求“以形写神”乃至于“离形得似”的境界; 虽然对于“花之美”的空的一面也重视,但并没有放在首位,而是要服从花之红的主客互动,强调从天地的运行中、世间的实践中去体验难以体会之“无”,从而达到一种既与无形无色无味的形上之道有关联,又完全落实到君贤臣忠、父慈子孝、夫妇合好的家国运行中,落实到每天每月每季每年的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这种在主客互动中达到一种既与天契又与人合的非圣非凡、即圣即凡的境界。
(三)“花之美”型的思想与印度的世界结构
印度人面对三类一体世界,把思想重点放在“花之美”这一体悟现象世界后面的形上性质而形成的存在形态,并以这一形态为基础或曰为主干,建构起包括“圆”“红”“美”在内的整体世界的基本模式。 这一以“花之美”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印度哲学的最高概念Brahman(绝对的大梵)和ātman(绝对的大我)上。 与中国思想进行比较就非常明显,中国讲天人合一,“天”是世界的整体,具形上的本质性,人是现象界中的人,乃形下的现世性。 而印度的梵和我皆为形上整体,与本体的梵相对的是现象世界的万象(māyā),与ātman(本体大我)相对的是现象世界的jīva(个我)。 印度的根本至言是梵我如一。 这里的我不是现象上的jīva(个我)而乃本体性的ātman(大我)。 梵和我都是在形上层面讲的。 在西方和中国,世界本体的存在(Being)和天地的根本之道,都是客观的,在人之外的,而印度梵即是我,梵我一如,世界的整体本质同时就是人的最高本质。 印度人认为,与梵如一的大我就内在于个我之中,只是由于世俗所障而感觉不到、意识不到、自知不到而已,但既然梵-我就像内在于世界万物之中一样,本就内在于个我之中,因此,个我可以通过特有的方式,达到自身的觉悟,从世俗的存在中解脱出来,达到与形上的梵我合一。 印度人把人生和世界的价值放在梵-我上,而梵-我正如花之美一样,乃空。 奥义书有很多故事和论说,一再讲述着梵-我为空的至理,且举《歌者奥义书》第6章第12和13节讲故事。 第12节的故事如下:
父(对儿说):去摘一个无花果来。
儿摘来呈上说:父亲大人。 这,无花果。
父:剖开它。
儿:剖开了。 父亲大人。
父:你在里面看到什么?
儿:这些很小的种子。 父亲大人。
父:剖开其中的一颗!
儿:剖开了。 父亲大人。
父: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儿:里面什么也没有。 父亲大人。
父:好儿。 你没有看到这个微妙者,正是妙机其微,这棵大无花果树得以盛大挺立
第13节的故事如下:
父对子说:把此盐放于一碗水中,明晨再来见我
儿子遵命而行。 第二天执碗见父。
父:且将水中盐取出给我
儿看向碗中水,不知盐在何处
父:尝上面的水——怎样?
儿:咸的。
父:尝中间的水——怎样?
儿:咸的。
父:尝底面的水——怎样?
儿:咸的。
父:放下碗,你坐到我这儿来吧。
儿子坐定后,
父:你的身体犹如那碗水。 在身体之中,你察觉不到那存在者,犹如在碗中你看不到水中之盐一样,但它本就存在于你的身体之内。 那是宇宙之中的精妙,宇宙万有以此为自性。 ⑦
第12节的故事讲梵-我为空存在于自然物中,虽然难以感知却的确存在。 第13节的故事讲梵-我为空在人体中的存在,梵-我之空如盐在水中一样,进入到人体之中,虽然难以感知却的确存在。 印度世界整体的梵-我之空,初一看来,与中国的道之无相同,但本质有异。 中国的道,虽然其本体为无,但一定要在运行之中进入到具体事物里,以有无相生的方式突显出来,犹如《老子》第十章讲的,用泥土做一个陶器,陶器底壁部的实有和中间的空无,特别是中间的可以盛物盛水的中空之“无”,使之成为一个可发挥功能的器皿。 本体之无在具体之器“有无相生”中突显出来。 而印度的空,则强调的是空本身,正如商羯罗(Sankara,约788~820)的经典举例,世界本空,陶工做瓶,围起了一个瓶内之空,瓶内的具体之空与瓶外的世界之空使人只见瓶内的具体之空,一旦瓶破,瓶内之空与瓶外之空就合为一体,再无分别。 如果说,《老子》的无在于运行中的“有无相生”,“无”在使用中显出功效; 那么,商羯罗的空,就是进入瓶中,也并不强调其现实的功用,只有突出其本质之空被误认为具体之空。 从哲学上来讲,是一种现世中的误认。 本体之空在这里成了现象之幻。 商羯罗的瓶空之例,内蕴着印度哲学的根本思想。 与本节相关的重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印度哲学中世界的本体之空,不是像中国那样从道之无具体运行中去讲,而一定要做空本身讲,这就是各种奥义书反复述说的,梵-我是什么呢? 是不生、不死,无前、无后,非动、非静,非过去、非未来,不执、不住,无家名、无种姓、无呼吸、无思想、不可目视,不可耳闻,不可言说、不可名状、不可知之……总而言之,本体之空,一说即错。 因此,本体之空是存在的,可以说,但既然是空,又说不出,要说,只能用遮诠方式,说:它不是……它不是……空进入瓶中,成为瓶内之空,虽有本体之空在其中,又不是以本体之空而是以瓶内之空显示出来的。 瓶内之空在现象上已经成了本体之空的幻相。 用瓶之空去讲本体之空,正如《金刚经》论用语言去讲本体之空一样:“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如来说般若波罗密(智慧),即非般若波罗密(智慧),是名般若波罗密(智慧)。 ”⑧本体之空一时进入具体之空,虽然与本体之空有关联,但已经不是本体之空。 理解此,就理解了印度的本体之“空”与中国的本体之“无”的差别。 同时从印度的本体之空,可以理解西方用实体方式去理解花之美何以会遇上巨大的困难。
第二,瓶存在于一段具体的时间过程之中,从瓶由陶工制成而产生,到瓶的最后破碎而消亡,因瓶的存在,世界本体之空转成了瓶内的具体之空。 前面讲了瓶内之空为本体之空的幻相,主要从空间的有无角度去讲,对于印度人来讲,在世界的时空中,一维时间最为重要,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万物皆在时间之santāna(时间流动,汉译为“相续”)中,时流由每一k? a? a(“刹那”,姑称为“时点”)所构成,时点流过,事物存在此时点的这一存在也随之逝去,不存在了。 在新的时点上存在的此物,已经与上一时点上的此物有了变化,但由于此时点的此物来自于上一时点,因此,人们还会将之视为一物,但强调时点与物的捆绑关系的印人知道,虽是一物但已非前一时点之物。 此时点也会转瞬即逝,从而此时点之物也会转瞬成空。 在印度人“物时一体”的观念中,事物,不但由空而来(生)又回归到空(死),而且在其生存时段中的每一点,都在实与空的统一中存在并变化着。 由(已逝时点之)空而(当下时点之)实,又由(当下时点之)实而(已逝时点之)空。 时间之流的每一时点都不会停留,永不停留,从而物存在的每一瞬都转瞬即灭,由此形成了佛教三法印中的“诸行anitya(无常)”观念(这与中国的五行永恒观念形成对比)。 就物在每时点中已逝而人往往感觉不到其此瞬已逝来讲,印度人将之称为māyā(幻相或幻象)。 “象”在中文里,指事物在时间中变动着。 中国人会把在时间中变动的事物看成实实在在的事物(只要它没有从世上消失),但印度人却认为事物随着每一时点的流逝而已经消失,事物的存在就是一个不断在时间中消失的过程,把这一不断转瞬成空的事物看成一个一直存在的事物,与事物本来的客观存在不相符合,因此,中国人在实有“象”上加一“幻”的定语,称为:幻象。 “相”在中文里,是专门停顿下来,照相即让人在按快门的那一瞬停顿下来,亮相即戏曲表演时从行动中突然停顿下来让观众细看。 时间由时点构成,事物在每一时点上停下来让我们细看,就是相,但时间一直在流动,停下来只能在人观念上而非客观的事实上,但人认知事物的确是通过一种停的观照方式进行,使事物以“相”的方式呈现,这一方式与事物的客观事实并不相符,因此可加一“幻”的定语,称为:幻相。 对于印度人来讲,幻象或幻相都是māyā(摩耶)。 在思想中,人们可以把本来在时流中不断转瞬成空即诸行无常的事物,转变为一些长时段的整体,如某人的节庆之夜,少年时代,乃至他的一生,进行把握。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知道,从客观实际讲,这些都是幻相。 因此,按照印度哲学,一切现象界的事物,无论是个物还是类物,都在不可逆的时间流动中存在,都是māyā(幻相或幻象)的存在。
且不管印度人是先得出本体之空,方以此推及类物和个物,得出世界本空万物为幻的哲理,还是先由对时间之流的强烈感受,从个物与类物之幻,才推出世界本空的玄思。 总之在时间之流中,再美好的事物都转瞬成空,给印度人以太深太强的感触,他们因时间之太重要反而轻视历史,不像中国与西方那样去作详实的历史记录,因此,我们目前只能从无精确时代典籍中,寻出众多久远的碎片,以推测思想的演进。 在《梨俱吠陀》中,有宇宙之神用幻化之神力幻出具体之物,物亡又被神用神力幻归回去,从而世界就是由神幻化而出和幻归而去的幻相世界。 印度神系在雅利安文化与哈拉帕文化的互动中,最后产生了三位宇宙主神,是按照时间进行安排的,梵天是创造之神,世界万物皆由之而生。 毗湿奴是保持之神,世界万物由产生到死亡,由他主管。 湿婆是毁灭之神,世界万物的死亡由他掌控。 当然毁灭又与转世重生相连,时间三神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印度神系在时间上展开,正与希腊的神系强调空间的分布形成对比:宙斯是天界之神、波塞冬是海洋之神,哈迪斯是冥界之神。 中国的神话虽然在先秦理性化中被弄得面目全非,但从先秦典籍中,可以看到天神地祇祖鬼物鬽的体系,这是一个天之神、地之祇、四方物鬽的天地四方的空间加上由祖鬼形成历史世系的时间形成的时空合一的神系。 从先秦到汉代形成的五行体系中可以看到,空间上东西南北中的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同时兼为时间上的春夏长夏秋冬五季之神,同样是一个时空合一的神系。 在中西印的比较中,印度神系的时间性特别突出,上面讲的梵天作为生、毗湿奴作为保持的住-异、湿婆作为灭是印度教的三主神,佛教的最基础的四相图,强调的仍是佛陀一生的四大阶段,一是佛陀在母亲的肋下诞生突出的“生”,二是佛陀成佛时的降魔成道突出的“住”,三是成佛后的佛陀第一次宣讲教义的初传法轮突出的“异”,四是佛陀双林涅槃的“灭”。 这里印度教和佛教都突出的时间性对世界整体性质及世界万物运行的决定作用,使得印度哲学面对客观上从不停顿下来而一直流动的时间这一事实,一方面认为,在以“空”去反映世界整体的本质,另方面以“幻”去反映世界万物的生灭,是合适的。 与之相应,在反映和肯定形上界的世界本质,梵语用了as一词作为本质之是,在反映和肯定现象界的世界万物,梵语用了bhū作为现象之是,因为现象界的万物总是在时间的流动中存在并为之所决定,因此bhū在具有“是”的词义的同时,还是“变”的词义,乃“是”与“变”的统一。 这样现象界万物的bhū(是-变一体),正与本体界上对世界本空的肯定之as(是)相应合。
三 世界的三种存在与美学的理论构成
现在,先把上面对中西印文化的分别讲述进行一下统一的总结,然后再转到美学的问题上去。
中西印三大文化,面对世界三种类型的构成,都感受到了这三种类型是相互关联着的整体存在,但在对之进行互动和认知上,在进行思想选择和强调重点上各不相同,从而有了不同的世界结构。
西方文化把重点放“花之圆”上,对世界的认知从确确实实的个物的“这一个”开始。 一方面让个物成为几何学上的确实存在又不可再分而且可以进行时空扩展的“点”,让个物可以从关联和整体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从而得到一种可以独立于类物和整体的与时间无关的空间性的本质,形成了关于个物的本质的具有明晰的“是”的语言定义。 并把这一关于个物的认知,推演到类物,形成西方的分科性知识体系; 进而推演到世界整体,对于本来无法确定的整体之是(只有说是而不说是什么方才成为不是具体个物或具体类物之是的是本身),却把作为整体之是(Being)的是本身(Being),定在确定“存在”(Being)的“有”(Being)上。 这样虽然西方思想看到了三种类型的区别,但对三种类型都作了“花之圆”的思考,得出了与“花之圆”相同的结论。
中国文化把重点放在“花之红”上,从天人合一到主客合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开始,面对个物,不但将之放到类物的关系中,而且放到与世界整体的关系中,找出个物与类物以及世界整体的关系,把个物的本质不是定在只是自身具有的实体上,而是定在与他物、类物以及世界整体相关的虚体即气之上。 面对世界整体,也不是从世界整体之性的本身去讲,而是从世界整体之性在具体的运行中去讲,把形上之道转为运行之行,为了让道之运行之道通达无碍,把世界上的一切,整体之性、类物之性、个物之性,都定义在虚体的气上。 道之运行的气之本体与世界上的方方面面都关联了起来,成为一个虚实合一关联整体。 任何客体之物在时空的运行中,都如钟嵘《诗品序》所讲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 任何主体之人,在时空的运行中,都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讲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总之,无论是世界整体,还是类物和个物,在中国文化中都呈现为“花之红”的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从大讲,要求天人在互动中合一,以小论,要求主客在互动中合一。 文化的最核心概念,无论是形上的道、无、气,还有形下的含气之物或含气之器,都讲究以人和世界互动中的和合与中庸。
印度文化,把重点放在“花之美”上,在世界的整体性质上,只能是空,无论从客观角度讲世界整体的大梵,还是从主体角度讲世界整体的大我,性质都为空。 面对“花之红”这样的人与世界互动突出之处,初看来与中国的天人合一或主客合一互动相同,但实际上在这种相同更突出的是空,以及由空而来的变动性。 这就是vi? aya(境)的理论,一方面,印度看来,世界呈现的一切,只有在人的感知器官,眼耳鼻舌身意,去感知方才呈现出来,另方面,主体所感知到的世界上的一切,色声嗅味触法,只是在世界本身具有这些性质,方能够感知到。 但是,第一,每一个人的主体性质不同,面对相同的客体,其主客互动所呈现出来的境就显得不同。 第二,每一客观物体在不同环境和不同时点上是不同的,面对相同的主体,其主客互动所呈现的境也是不同的,因为,主体与客体不但本有其性,而且都处在时间之流的是-变的过程之中,因此,主客互动之境也都是不同的。 总之,主客互动之“境”在客体上的呈现是每呈每变,在主体的感知中也是每感每变,从而主客互动,如果要从西方型的确定性来讲,呈现的是一种在是-变一体中不断变化的幻境。 由于世界本空,因此当印人面对具体个物之时,也是用是-变-幻-空的思维去看,如胜论学人认为,由于个物是宇宙之空中的个物,因此也充满了空性、具体来讲有五种空,个物之空不是宇宙的整体之空(? ūnyatā),而乃由个物在时间之流中所呈现出来的空,个物在时间之流中是动态,称为bhāva(情态),每一时点上的情态都因时点的转瞬即逝而成为空,因此个物的空性在梵语就是在bhāva(具体时点中的情态)这词前面加一个否定前缀a,成为abhāva(个物之空)。 与宇宙整体之空而来的具体个物之空,可从五个方面讲,即胜论学人关于个物 “五空论”⑨:第一,个物产生之前,是“空”,曰pragabhāva(未生之空)。 第二,当其已灭之后,也是“空”,可称为pradhvamsabhāva(已灭之空)。 这两个空讲的个物与世界的关系,即个物从世界幻化而出与幻归而去的问题。 由此可悟世界万物本空之理,接着是个物进入存在之后的特点。 第三,个物在从空到有之前,成为何物有多种的可能,而一旦成为此物,其他可能性就不再存在了,如人已成为人,不可能再成鸟成鱼成虫成树成草成石成泥成风成雨,所有这些可能,对于人来说业已成空,可曰atyantabhāva(毕竟之空)。 第四,个物之为此物,是在与相对或相反的甚多事物的对照中成为此物的。 如人,是在与地上之马牛羊狗猪的对比中,与空中之鸟和水中之鱼的对比中,与田野的庄稼,屋中的器具的对比中,以及其他事物的对比中,成为人的。 他成为了人,就再也不具有其他事物,如马、鱼、鸟、庄稼、器具的性质,这些他物的性质对于人来说,是空,可曰anyonyadhāva(比较之空)。 第五,世界上的个物千千万万,各物有各自的特点,一物一旦成为此物之后,再也不可能有很多世界上其他事物的特点,如人再也不可如鸟一样在天上飞,如雨一样从天上落,如树一样立在土中不动,总之,由此成为此物而再也不会获世界上的其他特点,这些人永不会得到的特点对于人来说是空,称之为asamsargadhāva(不会之空)。 胜论的个物“五空”论,实际就是关联着世界本空的思想去看个物,使个物内蕴的空性得到彰显。
中西印三大文化面对世界的三种存在,强调的重点不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世界认知和世界图景,但正因为不同,又使世界的三种存在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极大的彰显,因此,将三大文化的思想在一种互补的方式综合起来看,可以使整个世界图景得到更为充分的呈现,特别是使人类之美这一复杂问题,得到较好的体悟。
美,一方面,如“花之圆”一样,自美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之后(各原始文化中艺术的产生是其实物证明,各文化的文字中美字的出现是其观念证明),是一种客观存在。 美的客观存在,可以如几何学上的圆的存在一样,以一种明晰确实的话语去言说,比如在看重“花之圆”的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就以几何学的方式,得出了美的比例,从思想的演进来讲,比例(logos)就是逻各斯(logos),有其形上的基础。 从美的本质来讲,美的比例就是符合黄金比例的事物(如5:8之比等),古希腊的公共建筑,神庙、市政厅、运动场、剧场,都符合美的比例。 用比例讲美,不仅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美学的内容,也是所有文化的内容,只是在不同的文化,什么比例是最美的比例,又是同中有异的,美的比例在文化中具有怎样的理论性质,也是不同的。 用比例讲美,在中国,美的比例是由立中测影而来的9:5之比; 在印度,印度教的《梵天度量论》和佛教的《造像量度经》,又有自己的美的比例。 不同文化的美的比例虽然在具体内容有同有异,但都用“花之圆”这样确切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思想,来讲事物由此具有美的比例,而使此物呈现为美,是相同的。 这就是,美的理论是可以用“花之圆”这样的理论方式去谈论的。 当然,用比例讲美,在不同文化的性质中是不一样的,在实体区分型思维的西方,比例为美,具有本质性的重要性。 帕特农神庙和持矛者雕刻,成为美的典型标志。 在虚实关联型思维的中国,比例为美,只是美的因素之一,而非最高之美,最高之美不是与实体而是与虚体相关联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 在印度,比例为美也只美的因素之一,在性质上属于“下梵”和“俗谛”,而非“上梵”和“真谛”。
美,另一方面,如“花之红”一样,自美在人类历史中产生之后,特别是在各文化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中,走上不同的文化之路后,是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 这里,不但产生了“各美其美”的或小或大的差异,比如原始时代把身体的生殖部位加大特别夸大的维纳斯雕像,在理性化以后的文化中被认为不美甚至为丑。 又比如,西方油画在明清传到中国,被中国学人认为画得不好,相反中国绘画初传到西方,也因不讲正确的比例和应有透视,而得到差评。 由主客互动而产生的美,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个人中产生赏美和评美差别的主要原因。 这一“各美其美”的现象,只在一个文化圈之内还不突出,一旦进入不同文化的互看互赏,审美观的差异就马上放大出来。 这时美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产生了出来,进一步,美在客观上是什么的问题产生了出来和各美其美的差异是什么造成的问题也产生了出来。 这些问题都与“花之红”一样,仅由物之为美的客观方面是不能完全讲清楚的,而必须从主客互动的角度,方可进入理论的门径。
美,再一方面,如“花之美”一样,虽然自美在人类历史中产生以后就被感受到了,但怎样从理论的严格性上,讲出美是什么,却一直是一个难题。 西方文化从实体-区分思维的命题角度提出“花之美”,但却在花的实体上找不到实体性的因素,无论是像福尔摩斯那样用逻辑方式为在一房间内找细小东西把房间划成一个个小方格,一格格去找,还是如科学家那样把花放到实验室中进行物理的区分性分析,始终在花上找不到美的因子。 用严格的西方思维,像分析哲学家那样去面对“花之美”的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说“这花是美的”这句话是错的。 我们可以说“花之圆、之红、之香、之柔”等等,但从科学的严格性和理论的严格性上,不能说花是美。 “花之美”,在客观上得不到“花之圆”那样的验证,在经验上得不到全部人类的验证,“花之美”是一个全称判断,只要有一个人确实感到花不美,又不能证明他错,“花之美”这一理论命题就是不成立的。 虽然可以从“花之美”退回到如“花之红”那样,把全称命题变成非全称命题:“花在一部分人那里是美的”,但只要“花在另一部分人那里是不美的”也成立,更主要的是:在花上找不到“花之圆”那样确切的证明,“花是美的”这一命题就不成立。
当然这一不成立,只是在西方实体区分型思维中方才成立的。 西方人把花看成只由实体构成,而且与他物和整个世界没关联,在花的实体上找不到美的因子,从而无法成立。 但只要把这一命题移到中国和印度,就可以变成理论上是成立的了。 西方思想把物体看成可以与他物和世界整体区分开来的实体,从花的实体性去找,肯定找不到美的因子。 中国思想把物体看成虚实结构,实和虚两部分,特别是虚的部分,是与他物和世界整体紧密关联着的。 中国人看来,美不仅在实的方面,更在虚的方面,《庄子·知北游》讲,“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天地大美为虚,因此难以言说,“花之美”主要在与天地大美相关联的虚体上。 贺知章《咏柳》诗讲“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讲的就是植物之美在春来之时由天地的虚体所产生。 因此,植物之美最关键的不在植物本身,而在植物与天地的虚体关系。 这种虚体的关联其实还内蕴着客体与主体的互动关联:正如徐志摩的诗所写的:
那河畔上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徐志摩《再别康桥》
徐志摩用诗写出了与“这朵花是美的”相同的感受。 因此,这朵花是美的,中国型的正解,不是在花中去寻找实体性的美的因子,而是要与一个虚相生的世界关联起来:“是有真迹,如不可知”(司空图《诗品·缜密》),“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司空图《诗品·自然》),“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司空图《诗品·疏野》)。 与中国人相似,印度人对“这朵花是美的”不仅不是从实体上去看,而且是从时间与事物的关系去看,一方面,人只能在某一时点上说这句话,此话之真只与这一时点相连,只要人在说这句话时,他确实感到这朵花是美就可以了,正如泰戈尔在一瞬间感受到百合花的美:
池水从幽暗中
高高擎起百合花
那是池水的抒情诗
太阳说:他们真好
——泰戈尔《流萤集》(第五十首)
泰戈尔用这首诗表达了相当于“这朵花真美”的感受。 这句话既与他此前是否感到此花为美无关,也与他此后是否还感到此花为美无关,还与其他人是否也感到此花为美无关。 另一方面,在印度人的理论里,这朵花是美的,不属于与西方的本质相同的上梵和真谛,而属于在空幻世界中属于幻相的下梵和俗谛。 从作为世界整体本质的上梵和真谛来讲,人在感受到此花之美的俗谛之时,还应同时从“这朵花是美的”这一刹那的感受体会到世界整体的空性之永恒,悟感到“一花一世界”的空境。
总之,“这朵花是美的”在中国和印度之所以成立,在于中国思维和印度思维都从西方型“花之圆”的实体区分思维转移了出来,中国转换到了“花之红”的主客互动的虚实关联型思维上,印度思维移迁到了“花之美”的是-变-幻-空思维上。 综上所述,可以对以中西印的三种思维方式以及由之产生的对美的理论思考作一综合的点评。
分而观之,世界的呈现可分为三种形态,一,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花之圆”的规律; 二,由主客互动而产生的“花之红”的规律; 三,由虚实结构之“虚”的由虚呈实和空幻结构之空的由空呈幻而来的“花之美”的规律。 合而观之,这三种形态又是相互关联的三而一的存在。 中西印在三种存在形态中各选其一作为基础,进而将之合而为一,形成各自的理论。 这三种理论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美的问题是理论问题中最复杂最微妙最难讲的问题,三大文化的理论在面对美的问题时,各有所长又各有所偏,展开了一幅五彩斑斓的思想图景,内蕴着启幽探微的形上理路。
西方理论因为只有实体,而提出了美的理论问题,但又因为只知道实体,而解决不了美的理论问题,虽然其美学理论在成长演进中的载沉载浮中左冲右突、大转大折、体系频出而表演非常精彩。 中国理论因为不仅是实体而且有虚体,因而不会像西方那样以学科的方式提出美学,但却在虚实相生中不断面对和解决着美学问题,其非学科型的美学建构非常精彩又非常微妙,微妙得不但西方人看不出来,连走上世界现代性道路的现代中国学人都不是一下子看得出来,而中国的非学科型美学,在解决西方人难以解决的美学问题上,应当而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这从西方现代思想(如分析美学在家族相似中体现的实虚合一的整体)和后现代思想(拉康把本体的实在世界变成一个虚体,人在对之的追求中只有不断错过的相遇)中所内蕴的中国因素可以悟出。 印度理论因为不仅是实体,而且视实体为幻体,又把现象上的幻体关联到本体的性空,因而也不会像西方那样以学科的方式提出美学,但却以色空转换的方式不断地面对和解决着美学问题,印度型的非学科的美学建构非常精彩又非常空灵。 空灵得不但西方人看不出来,连走上世界现代性道路的现代印度学人都不是一下子看得出来,而印度型的非学科型美学,在解决西方人难以解决的美学上,应当而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这从西方现代思想(柏格森和怀特海强调时间和过程对事物的影响)和后现代思想(如德里达强调时间中的延宕对词义和事物意义的变化。 )中所内蕴的印度因素可以悟出。
要理解中西印美学在互动所产生的美学效果,需要从世界美学的总体演进的大框架去看中西印美学的历史演进。 这就是美学的另外一个大故事了。
注释:
①参见特沃列·兰姆、贾宁·布里奥编:《色彩》,刘国彬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85-106页。
②参见《奥义书》,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6页,See S. RADHAKRISHNAN. The Principal Unpani? ads. (英梵对照本)New York:Humanities Press INC. 1953:P.388.
③See C. C. W. TAYLOR ed:From the Beginning to Plato. NY: Routledge,1997,P.332; 王晓朝:《绕不过去的柏拉图——希腊语动词eimi与柏拉图的型相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7529.html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2023-2024JCR褰卞搷鍥犲瓙

SCI 璁烘枃閫夊垔銆佹姇绋裤€佷慨鍥炲叏鎸囧崡

SSCI绀句細绉戝鏈熷垔鎶曠ǹ璧勮

涓鏂囨牳蹇冩湡鍒婁粙缁嶄笌鎶曠ǹ鎸囧崡

sci鍜宻sci鍙屾敹褰曟湡鍒�

EI鏀跺綍鐨勪腑鍥芥湡鍒�

鍚勫绉憇sci

鍚勫绉憇ci

鍚勫绉慳hci

EI鏈熷垔CPXSourceList

鍘嗗眾cssci鏍稿績鏈熷垔姹囨€�

鍘嗗眾cscd-涓浗绉戝寮曟枃鏁版嵁搴撴潵婧愭湡鍒�

CSCD锛�2023-2024锛�

涓闄㈠垎鍖鸿〃2023

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鍘嗗眾鐩綍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堣嚜鐒剁瀛︼級

2023骞寸増涓浗绉戞妧鏍稿績鏈熷垔鐩綍锛堢ぞ浼氱瀛︼級

鍘嗗眾鍖楀ぇ鏍稿績

2023鐗堢鍗佺増涓枃鏍稿績鐩綍
璇峰~鍐欎俊鎭紝鍑轰功/涓撳埄/鍥藉唴澶�/涓嫳鏂�/鍏ㄥ绉戞湡鍒婃帹鑽愪笌鍙戣〃鎸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