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两条大字标语格外引人注目。 广大的进步作家将之视为文协引领知识分子投入抗战的号召而群起响应。 其中,姚雪垠是这一号召最积极、最忠勇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之一。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 在成立大会的会场上,“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两条大字标语格外引人注目。 广大的进步作家将之视为“文协”引领知识分子投入抗战的号召而群起响应。 其中,姚雪垠是这一号召最积极、最忠勇的拥护者和践行者之一。 从1939年4月至1940年2月,他三次挟笔远征,奔赴抗战的前沿阵地,以强大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了《四月交响曲》等一大批表现抗战的作品。 这些作品虽已经历七十多年岁月的洗练与销磨,但至今仍铿然有声、回响不绝,其中高扬着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旋律,犹如铁马金戈一般在神州大地上驰聘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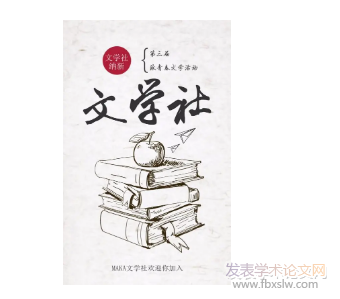
第一次笔征
1939年4月,“随枣战役”打响。 受“文协”第五战区分会委派,姚雪垠与老友臧克家、孙陵等各率一支小小的“笔部队”,分别深入国民党143师、173师和189师驻守的阵地采访。 “敌人就在前面的山头上,山上的寨子清清楚楚地描给人一个影子。 借了夜的掩护,我到了团部、营部、连部,一步一步爬上森林寺的第一线,心,也随着一弦一弦地扣紧了……”(臧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这是真正地走上火线,这是真正地深入前沿。 “五月一日夜间,日军向我鄂北前线阵地猛攻,彻夜不停。 双方机枪如同潮水,炮声亦稠。 黎明,性格豪迈的一七二(应为“三”——作者注)师师长钟毅将军在庭院中设小酌为我们送行。 ”当时情景,姚雪垠记忆犹新:“旁边花坛上的红玫瑰正开,他对我说:‘日寇快要逼近,这花你不能欣赏了,等打完这一仗再来吧。 ’”[1]
告别钟毅将军,他们一路撤退。 “四下里是枪炮,火光,人群。 通到襄樊去的大路被切断了……夺路到河南,盘过了山,到了五战区的最后面——均县,直着爬跑了八天六夜”(臧克家:《笔部队在随枣前线》),终于平安脱险。 回到司令部后才知道,几天前防守襄阳西岸的第33集团军渡河出击,血火相搏九日九夜而重创敌寇。 鏖战中张自忠总司令身先士卒壮烈殉国; 而姚雪垠刚去过的173师也伤亡惨重,原班人马已所剩无几。
不幸的消息,强烈震憾着姚雪垠的心魄。 想到大战在即钟毅将军从容镇定的“赏花”之约,想到在战壕里刚刚见过的那些鲜活生命大多已血肉不存,姚雪垠把一腔悲愤化作笔下烽烟,一篇最具现场感的战地通讯《四月交响曲》慰忠魂泣国殇,长歌当哭荡气回肠:
蔡家河之役,有一位班长的左边肺叶被机关枪弹穿透了,气从伤口随着血液冒出来,人们把他抬到医务所的时候,他用没有光彩的眼睛望着医务主任说:“主任,我认识你的,请你把伤口裹紧一点,别叫它冒出气来,我好回到火线上……”半点钟没过去,这位英雄就在一种兴奋的情绪中死去了。 临死时,据说他又突然睁开眼睛,含糊说了一句话:“丢那妈,这就算完事了吗? 我还要杀鬼子呀! ”
大小九冲的战斗里,有一位连副负了两处重伤后才从火线上退下来。 因为找不到担架兵,等他步行到团部时,已经只剩奄奄一息了。 一边不住的流着血,神智开始昏迷起来,一边还喃喃的告诉团长说:“不要紧的,团长,我用手榴弹打死了七个敌人,已经赚了六个了。 ”
有一位叫做黄式勇的二等兵,负伤后不曾退下火线时,阵地就被敌人突破了。 白天,他有时藏在草堆里,有时藏在被敌人炮火轰毁的废墟里; 夜里,他忍着痛苦,忍着饥饿和疲惫,把步枪驮在脊背上,摸索着从敌人的阵地上爬出来,三天后在炮火中他重又同自家的兄弟们碰在一起,像一个受了折磨的孩子似的流下了难过的眼泪。 营长问他道:“黄式勇,你为什么不把步枪扔掉? ”“报告营长”,他说:“有枪,我起码还可以换他一个呐! ”[2]
写着这些文字,姚雪垠无法抑制感情潮水放纵奔流。 那些“来自不同的省份里,说着不同的地方话”的英雄们,“八一三战争一起就出来打仗,到上海、到南京、到徐州”,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用青春的生命守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把血染的风采留给了山高水长。
关帝庙之役,日本一个中队只逃走了十几名,中国兵出其不意的把敌人消灭了。 另外,在郝家店、蔡家河、黄土关、兴隆重集、大九冲、小九冲,三零四高地,在这些大小战役里,敌人利用优势的炮火外,还不断的施放毒气和烟雾,然而中国军队在艰苦的条件中获得胜利了。
在争夺三零四高地的战斗里,中国士兵用惊人的沉着去阻止敌人的猛烈攻击……有许多中国士兵被炮火所鼓舞,被死伤所鼓舞,被烈火一般的狂怒所鼓舞,当敌人的手榴弹刚落地没有爆炸的时候,就像猴子一般敏捷的把手榴弹从地上抓起来,牙一咬,眼一合,嗖的一声投回去。 有时候,手榴弹刚出手时在空中爆炸开,中国士兵就在一瞬间倒在血泊里。 日本士兵从来没有这样英勇的死法,他们对全世界宣传着中国人是野蛮的,我想,这样死法大概就是“野蛮”的证据吧。 [3]
这些文字,不仅记下了抗日将士们英勇捐躯慷慨赴死的忠烈,也同时记下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对亲人的眷恋和对家乡的向往。 在战斗的间隙里,战士们“有的静静的坐在掩蔽部或用稻草松枝搭盖的小屋里,熟练地缝补着衣裳。 有的坐在温暖的阳光下,从身上脱下来破军装,用心用意的捉虱子……有的在学习记日记,日记本子是从敌人身上捡来的。 有的在聚精会神地一字不漏的读着包花生米的一片旧报纸……”他们并不讳言他们想家,但他们又说:“有国才有家。 不把敌人打出去,回家不是要当亡国奴吗? ……想回家,就得打仗呵! ”
一次“笔征”,拉近了作家与战士的距离。 秀才与兵,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发生了心灵碰撞:“隔着那发散着汗臭和蠕动着虱子的破军装,我认识了那些纯朴可爱的心,那心上,有着爱国者的慷慨热情,革命者的灿烂理想和每个战士所应有的那由五千年文明历史养成的自尊与自信。 ”姚雪垠情不自禁感慨复感喟:“死的人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悲愤的记忆。 活着的人除非他的灵魂已经麻木,谁肯忘掉这悲愤的记忆呢? ”
是的,不能忘掉,不该忘掉,又怎能忘掉! 崇高的爱国主义英雄情怀激扬起其更强烈的使命感,热血沸腾的作家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了肩头的责任重大。 他要再到战地去,再写英雄“交响曲”,他要把那些“悲愤的记忆”传播更远,植入更深,让它们去叩问良心,让它们去荡涤灵魂。
第二次“笔征”
1939年8月,姚雪垠又启程了。 他同臧克家一起,再一次踏上“笔征”之路。 他们一人一顶大斗笠,一人一双破草鞋,炎炎烈日下出发,瑟瑟秋风中归去。 小小的“笔部队”跋山涉水几千里,南冲北折穿越了三个省。 远征途中,他们拜访了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将士,看望了被侵略者逼得拿起枪杆的农民。 蒙城血战中的三千八百殉国英烈让他们啼血泣泪,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们囤积成山的仇货让他们触目惊心……诗人一路感慨一路吟诗,最后将这些诗结集出版时题名为《淮上吟》; 作家的收获同样不菲——成系列的报告文学诞生在他的辛苦奔波中:
《界首集》揭露了“私货和仇货猖獗的全部秘密”,用铁一样的事实告诉人们:“国外的侵略者和国内的封建势力紧密地结合着,阻碍着咱们大家向解放自由的路上走! ”《血的蒙城》是又一首英雄赞歌,周光副师长为统领的蒙城守卫者以“三四天不曾睡觉”“也没有好好吃过东西”的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着敌寇的三个机械化部队,最后全部默默地倒在了夕阳荒草中……《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总结了“第×××军政治部的同志们”“向农民进行工作”,组织成立“农民抗日会”的工作经验,对他们“从改善农民生活”“联系到抗战建国”的“基本方针”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此这般,姚雪垠用他独到的目光捕捉着豫南皖西一带的社会生活,用他特有的语言抒发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大别山抗日军民的敬仰,发泄着他对侵略者、卖国贼以及大发国难财的奸商们的刻骨仇恨。 应该承认,在当时这是一批最接地气、最具草根气息的战地通讯,它们被桂林前线出版社收集起来,以《四月交响曲》为名正式出版,从而留下了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一批真实而生动的故事。 虽然这些故事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少被提及,但是故事的主人公——那些铁血英雄们,却永远活在姚雪垠笔下,永远活在每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心里。
1962年1月,姚雪垠作《璇宫感旧诗》一组,其第18首写的就是这次笔征:“淮上迢迢路两千,风尘溽暑共车船。 笑君美忘旅行苦,一路吟诗入大山。 ”诗后注曰:“这年八月上旬,我与克家夫妇赴安徽采访。 先到漯河,然后乘船东下,经周口,抵阜阳登岸。 在阜阳停留三四日,然后赴涡阳、蒙城,转头向南,经固始,入大别山,到达金寨,当时改名立煌,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与豫鄂皖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 在大别山中大约停留一星期,从商城出山,经潢川、息县回老河口……”[4]
1995年4月下旬,笔者在奉命整理《璇宫感旧诗》期间,曾以“淮上”一首及其相关问题请教姚雪垠,没想到他对此次活动所得很不满意,其答复的中心要义如下:我同克家冒着溽暑奔跑了两个月,来回三千里,可以说白费工夫,毫无收获。 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名存实亡,“皖南事变”再有一年就要发生,蒋介石防范进步文化人士甚于防川,生怕“共产主义”钻空子渗透。 作家被限于走马看花的采访已足够可怜了,这一次却连采访的自由都没有——走到哪里都有人“招待”,等于是被软禁起来……
2010年5月,为将要在10月举行的“姚雪垠百年诞辰纪念”活动搜寻史料,经申请并由中国作协领导特批,笔者得以部分地接触到了姚雪垠的人事档案,从其自述经历的材料中,看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我们首先到了阜阳,受阜阳专员郭造勋的招待。 住了好几天,周旋于地方长官、士绅和“文化人”之间,却没有接近民众的机会。 从阜阳到了涡阳,不愿受官方招待,住在小客栈里。 但县长当晚来访,同我们大谈看相和奇门遁甲……第二天,该县长设宴洗尘,地方上的名流绅士作陪,又是一举一动都有人“招待”。 在涡阳只住了一天,觉得太无聊,便往蒙城……这天中午到达了一个大的市镇,偶然发现一群人在寨外远远的恭迎我们。 这群人包括了区镇长、商会会长、民教馆馆长、小学校长,自然还有其他的地方绅商。 我们被迎进民众教育馆中,洗脸、吃茶、用点心。 我偶然走往旁边的一间屋子,发现几个人正在赶写欢迎我们的标语,急得满头大汗。 弄得我不好意思,赶快退出。 等我们休息过后,绅士们要陪我们往街上看看。 走到街上,才看见满街贴着标语,墨汁还没干。 那些标语上写着:“欢迎劳苦功高的臧委员”、“欢迎劳苦功高的姚委员”……视察过后,回到民教馆中吃饭,自然是一餐丰盛的宴席。 第二天中午……离蒙城还有几里路远,看见一个人身穿军服,腰佩手枪,骑着脚踏车疾驰而来。 这个人在我们面前跳下车,行个军礼,恭敬的问:“你们二位可是姚委员跟臧委员吗? ”我们回答说我们是姓臧姓姚。 那人更恭敬的报告说:“县长同各机关绅士都在河边迎接。 ”然后再行个礼,又骑上脚踏车,飞驰而去。 我同克家很觉狼狈,只好把敞开的扣子扣好,心中七上八下的继续前行。 到了河边,渡船已经停在岸边等候,县长同绅士们果然一大堆人在对岸相迎。 船过了河,同欢迎的人们上了岸,忽然军乐震耳,把我骇了一跳。 原来军乐队排列在河岸上的大路旁边,像仪仗队那样的让我们打面前走过。 进城之后,让我们住在动员委员会。 当天县长设宴招待,第二天是一位姓葛的什么司令陪同着各处看看,又由这位司令请洗澡,请吃宴席。 第三天,忽然说日本打来了,我们只好匆匆的离开蒙城。 事后据说日本人打来的消息是个谣传,所以我有点儿疑心是这位县长不愿意我们停留太久,以免知道了他的罪恶(一年后他以贪污被撤职查办),才故意夸大了当时的紧张情势,好借口打发我们滚蛋……
原来如此! 始才明白姚雪垠何以视“招待”为“软禁”,何以说两个月的奔波“白费工夫”! 他带着五战区长官部的介绍信去皖北采访,唯一的目的“是想多搜集一点儿有关抗战的实际情形”,他对此行的收获期许,岂是一本薄薄的《四月交响曲》所能容纳! 然而,就因为时时处处的“被招待”,一切便都在无影无形中“被设计”了。 姚雪垠讲述以上遭遇,意在说明自己的抗战生活“漂浮于抗战现实之上,游离于历史主流之外”——主观上是在自我检讨,客观上却提供了一个史实,从而引发一种思考:作家们没有到前线深入采访的自由,是否正是当时大后方在创作上存在某些偏向的直接原因呢?
第三次“笔征”
1939年12月,姚雪垠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笔征——去鄂北前线,访问国民党第33军团。 那是一支英雄部队,其前身是打过“长城抗战”和“卢沟桥抗战”的国民党第29军。 能去这支部队走走看看,是他向往已久的热血男儿“从军行”。 兴致勃勃之时,他忍不住很骄傲地向他的朋友报告:“今年的新年我过的有点特别:日子是在马背上,在风雪细雨的战场上匆匆溜走的。 ”
按照规定的采访程序,他先到33集团军总部住了两日,再去77军司令部拜访军长冯治安将军。 在其后朝夕相处的几天里,两个人谈了很多“家常话”,“没有一点客气和虚伪”。 冯军长“会劈刀,会刺枪,会盘杠子、跳木马,会一切每个好兵所应该熟练的各种武术。 除这些以外,他还会洗衣服,做针线,做吃的,会一切日常生活上必需的技能”。 在他眼中,这位将军“是一个典型的西北军,一直保持着往日的风格。 虽然他戎马半生,作过省主席,作过集团总司令,到现在还戴着满头的高粱花子,像庄稼人差不多一样的朴素诚恳,叫你高兴去接近”[5]。
告别冯将军,他即去了钟祥县的洋梓镇附近,何基沣将军的第179师在此驻守。 何将军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之一,姚雪垠对他一直满怀敬意。 何将军则十分认可姚雪垠的学养和为人,在均县时曾数次出面邀请姚雪垠为“七七军训团”授课。 故交重逢,何将军对他格外关照。 夜半时分,忽派人去招待所把他叫醒,告知军团政治部主任有电话来,要求对他暗中监视,特意叮嘱他言行当心。 次日黎明,何将军又亲自跑来再提醒一遍。 早饭后,果然由师军法处主任领来一名青年,告知他的访问将由其陪伴始终。 形影不离地接触一段时间后,该青年竟受感化幡然悔悟,临别时向他哭诉真情,坦承自己走错了道路,恳请他帮助自己开辟新的生活。 几年后,姚雪垠据此写成一篇小说,题目叫做《人性的恢复》。
有了政治部门派出的专人陪同,姚雪垠得以堂而皇之地走上前沿阵地,名副其实地钻了战壕看了战阵,又一次真正零距离接触了那些可亲可爱的兵士们。 于是他不无骄傲地宣称“这次我在鄂北和鄂中一带去访问,看过了不少的部队”; 宣称“在火线上我搜集了不少的好东西”,“不到战场你简直想也想不到”; 宣称“我现在也有一匹马,一支枪,一百粒子弹”,然后用了十分得意的口气问询他的朋友:“你愿意来战地吗? 假如你愿意,我就驰马去接你,三五千里风霜雨雪算得什么呢? ”[6]
看得出来,姚雪垠情绪甚佳,因为战果不错:不仅有《战地春讯》《归来感》《文人眼中看军纪》《鄂北战场上的神秘武装》《〈春雷集〉题记》《神兵》等短篇倚马而成,更为后来写于安徽立煌(今金寨县)的《日本行动方向之谜》《戎马恋》《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抗战文学的语言问题》《长沙三捷》《母子篇》《笔参战》《诗人,正义的象征》《重逢》,以及后来在赴川道中和到重庆后所撰《三年间》《伴侣》《五月的鲜花》等作品作了必要的生活积累和素材准备。 姚雪垠曾在《战地春讯》里把其中一些“有趣的小事件、小材料”“作为新年的小礼物”送给他的朋友,在这里不妨打开一点略作展示:
——作战时候,后勤供应不济,官兵一两天不吃不喝是常事。 有士兵弄到一点米放到破水缸里煮,忽然听到爆炸声,原来缸底被烧裂,米和水一起从破裂处流下来……
——数九寒天,喝不上热水,饥饿的士兵弄到一点面粉,“就从塘子里弄些水来和成稀糊涂,大家高兴非常的抢着喝下去”。 重机枪手倒比较幸运,只要阵地上有敌人,射击一阵子,“就有开水或热水从枪里倒出来,不致喝冷水”了。
—— 一个兵的下唇被枪弹打去了一块,鲜血洇红了前胸,说话已经很困难,要送去军医处处理。 营长安慰他“三四天就会治好”,他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没关系,营长。 三四天后我再上来杀敌人。 ”
—— 一个士兵生了疥疮,坐在战壕里不住的抓搔着屁股。 敌人进攻了,距离百米时,他视而不见的在抓; 五六十米,他若无其事的在抓; 四五十米以内了,他拼命抓两把,就直起身来连二赶三的投去了几颗手榴弹,把敌人打退了。
—— 一个兵拿了一支很坏的老步枪。 枪栓打得发热了,再也拉不开,他就用脚踹开; 可是打了一枪又粘住拉不开了,他就再踹开,然后在枪栓上撒了一泡尿,结果把枪弄得稍好用了。
—— 一年里最冷的季节。 破烂的茅屋里住了一排人。 营长和连长查铺来,却只看见地上一堆稻草。 “人呢? ”营长眼睛里带着杀气问连长,一边又愤怒的向稻草踢了一脚。 一个人头从稻草堆里钻出来,惺忪着眼睛埋怨:“干什么踢我? 大家睡得好好的。 ”原来为了取暖,一排兵都钻进了稻草堆——“这情形是相当普遍的,有时候甚至连睡稻草的幸运也没有呢。 ”
如此这般,姚雪垠用极简省的笔墨再现了鄂北前线战士们的艰苦生活和乐观精神、坚定的意志和英勇的牺牲。 他用欣赏的目光关注着战士们身上的每一个闪光点,用喜悦的心情赞许着他们平凡的举动中蓄含的超越平凡的力量。 情之所至,姚雪垠的慨叹油然而生:“在战场上,只要是肯拿枪杆拼命的人物,不管他地位高低,年纪大小,都是豪爽的或心地朴素的。 他们除掉打仗没有多的心肝眼。 不愿意猜疑人,也不愿意自己被猜疑,所以你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总是痛快的。 ”[7]
不啻如此,姚雪垠还注意到部队“作战精神和部队纪律”的提高,注意到“部队里长官的修养和生活态度”对于部队纪律的决定性作用,注意到部队纪律的好坏“在许多情形之下”的互相关联、互为因果。 他甚至还对“鄂北战场上的神秘武装”——王川“老头子”领导下的“黄学会”之来龙去脉、组织方式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并以褒扬的笔墨写出黄学会在随枣会战和鄂北战役中修道路、抬担架、做向导、英勇参战等事迹,婉转地表达了希望政府和部队长官能了解和帮助他们,以“使这庞大的群众组织充分的发挥作用”。
然而,不能不说的是,姚雪垠赢得了第三次“笔征”,何将军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姚雪垠离开前线后不久,何将军即以“私通新四军”的罪名被调到重庆“受训”,好长时间才恢复自由。 何将军重回老河口以后,同冯治安将军等暂住酂阳旅社,其间曾悄悄去过姚雪垠寓所,告诉他的遭遇,并嘱不要去回看他,以免被特务注意到。
抗战之初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其实,早在全面抗战刚开始的1937年9月,姚雪垠就认识到了文化人深入实际斗争的重要性。 他说:“时代本身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悲喜剧,一首可歌可泣的大史诗……假若你不能拿枪杆,就拿着笔杆拼命的写去吧! 然而,我是叫你到大众的抗敌生活中去找寻宝贵的现实材料,你千万别闭着门随心捏造。 在如今,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跟抗日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关系你应该深刻的去认识,去把握。 ”[8]
既有认识,便有行动。 1938年1月下旬,姚雪垠以《风雨》主编和“全民通讯社”特约记者名义奔赴徐州,先访问了后来以血战台儿庄主力留名于世的国民党第30军,再访问了著名爱国将领于学忠及其率部驻守的淮北前线; 又深入民间抗日组织,与山东籍的游击队员们进行了两晚上的促膝长谈。 在纷飞战火中奔波近月后,姚雪垠告别宿县抵达江城,住在武汉“两湖学社”两月有余,把从抗战前线得来的宝贵素材,变成了一篇篇投枪匕首般的抗战檄文:
《蚌埠沦陷后》记录了日寇铁蹄下老百姓的苦难,揭露了当地天主堂的伪善面目和日本兵的凶残暴行:日本人将到时,蚌埠天主堂敞开大门接收难民。 许多有钱人把许多钱财送给神父请求保护。 日本人来了,“东西被抢走了,女人们不管老少,十之八九被强奸了,年轻的男人们有许多被惨杀了……”; 交过保险费的财主们跪求神甫,神甫却回答“这是你们中国人的事……”; 一个理发匠会说几句日语就变成了“要人”并且狐假虎威起来。 不料日本人看中了他的女人,跑去他家“亲善”了一番。 理发匠去告状,却得了个“侮辱皇军名誉”“破坏两国亲善”的罪名而被关起来,从此销声匿迹; “从怀远到临淮关,这将近二百里长的地域内,除掉若干驻有日本兵的村落之外,全被放火烧光了。 自怀远到蚌埠,二三十里内公路上曾有一个时期倒着二百多具死尸没人掩埋。 这些死尸自然都是善良的农人……”
《战地书简》通过信函方式,记录了山东省高密县在韩复榘命令下成立的一支游击队之经历与成长。 游击队的枪械基本上都是自带的; 游击队的官长多是地主、乡绅、退伍军官一类,士兵则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小地主和自耕农。 其中有人进游击队是想升官发财,有人是为逃避抓壮丁,有人把跟着游击队当作逃难的最上策……有一位“东北军”的廉团副参加了游击队,把一批大、中学生带进来开展政治和民运工作,于是便有了矛盾,有了冲突,有了团结,有了破裂,同时也有了发展和进步。 学生们在与各种封建人物的斗争中成长起来,游击队也从当初一听说日本人进了高密就往诸城逃跑,到被动参加诸城突围战又主动打响百尺河增援战的经历中勇敢起来。 两次战斗中各有三个表现突出的农人队员,应该就是《差半车麦秸》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吧?
《雁门关外的雷声》是一支英雄赞歌。 英雄梁雷于“卢沟桥事变”后到太原参加牺盟会,不久被委任为绥远省特派员,负责绥远全省的救亡工作。 可是不等他赶到绥远,绥远已经失陷。 右玉县县长望风而逃,梁雷便是右玉县县长; 盂县县长弃城而去,梁雷便是盂县县长; 还有偏关县县长、雁门关游击司令等,他一身数职,一个人领导着雁门关外13个县的12个抗日支队,“收复了右玉,保卫了偏关,在雁北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真正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但“他的信念永远是坚决的,正确的,纵然在最危急的时候也没有一点灰心,半丝动摇”。 他还兼着“执法司令”,带领游击队清理门户,诛杀汉奸……然而,最终梁雷被日寇包围了,杀害了,脑袋被砍下来挂在偏关城头上。 “英雄既已殉国,埋骨荒山,留给后死的是永远的纪念,衷心的哀悼; 是鼓励、奋起,和必须复仇的重担。 ”
《白龙港》抒写了长天雄鹰壮烈殉国的可歌可泣:“淞沪会战”期间,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奉命轰炸白龙港内停泊的敌舰。 临近战地时,副大队长沈崇诲驾驶的“904”号战机突发故障,发动机剧烈地震颤着……八千尺高空,刹那之间就有被烧成黑炭或跌成肉酱的要命时刻,沈崇诲拼命控制着飞机,让其以无比的速度俯冲直下……“轰隆”一声,飞机、炸弹、甲板一齐爆燃,英雄与敌舰同归于尽……
以上诸文,除了《雁门关外的雷声》,余者皆为姚雪垠早“文协”一步“下乡”“入伍”的收获。 如果说它们都是顺手拈来类的速成篇章,那么,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则是姚雪垠创作于1938年之初的传世之作。 小说主人公“差半车麦秸”本是个勤劳憨厚的农人,喜欢土地,喜欢安安生生地种庄稼。 可是,“北军来了,看见屋里人就糟蹋,看见外厢人就打呀,砍呀,枪毙呀”,逼迫着他不得不放下锄头扛起枪,怀着“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的朴素意识,在血火搏击中成长为一个英勇的抗日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后仍不肯下火线,坚持要“留下换他们几个……”短篇虽“短”,却塑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抗日游击队员形象,而这个形象身上那种土得掉渣、揭不开抹不去的乡土气息和那口活生生清凌凌的中原土话,一下子拉近了进步文学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从而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总而言之,1938年姚雪垠跑了很多路:1月徐州前线,2月淮北前线,3至5月在武汉参与全国“学联”二次会议的秘书处工作,6月去舞阳县组织召开“河南全省救亡青年代表大会”,7至8月在南阳筹备成立“青救协”“豫南执行部”,9至10月在邓县参与组织发展“地下”“青救协”,11月到襄樊“第五战区文工会”,12月去湖北均县主持“文工会”开办的“战地文化工作干部训练班”。
其间他还参与筹建了中华文协宜昌襄阳分会均县支会,并以支会名义举办了均县文艺讲习班……1938年,姚雪垠也作了很多文:《奠定保卫河南的胜利基础》《对于保卫河南的几项紧急建议》《淮北战地巡礼》《为保卫黄河贡献一点愚见》《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故乡杂感》《母子篇》《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宣言》《捕奸的故事》《悼烈士梁雷》《离散》……其中,绝大多数为宣传抗战,响应“文协”号召而作:“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 粉粹寇敌,争取胜利。 ”拿老舍先生的话说:“这不是写自己的趣味,而是写文字的实际效用啊! ”而能耗费着时间和精力写下如此多的既非乐趣使然更无创作积累但国家需要、民族需要的文字,姚雪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多强烈、多深厚,由此可知矣。
有学者曾经指出:姚雪垠在抗战时期的全部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基点,在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定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立场。 他视抗战阶段为中国人民挣脱一切枷锁、开创崭新未来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明确提出文学必须为“改造社会”服务。 因此他热情讴歌战斗的觉醒的人民大众,抨击一切压制民主阻碍进步的黑暗势力,毫不懈怠地用艺术形式昭示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必然。
或许惟其如此,姚雪垠的抗战作品才几乎是写一篇成一篇,写一部“红”一部:《差半车麦秸》获“抗战杰作”之誉; 《牛全德与红萝卜》被以“抗战名篇”相称; 《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毁誉咄咄中声名大振; 还有《戎马恋》《重逢》《崇高的爱》等,无一不是畅销书。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 它先经《读书月报》连载,再由重庆现代出版社出版。 “国统区”面积时已很小,发行受限,故一般新小说只能印2000册,《春暖》却开机就印了10000册,且未半月即售罄,只好反复印行达4次之多。
20世纪40年代末《春暖》在内地绝版后,香港地区却出现了多种翻印本,仅高原出版社一家就印行过3次,其影响深入中国香港和南洋的广大华文读者中。 直到1979年年底,新加坡籍华文作家严晖还在12月6日的《星洲日报》撰文回忆说:“《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写大别山这一群青年男女的抗战工作和生活动态,其中有几个人物,我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部小说当时相当轰动,大后方的青年读者很羡慕那种生活,觉得既新奇又很有意义。 曾有过那种生活的读者,好像重温旧梦,又思念起那一段活泼生动的日子,即便抗战结束多年,仍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
一言以蔽之:姚雪垠的抗战作品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贴近地皮“草根”,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家的抗战作品一起,“不仅奠定了抗战文学基本的创作路向,而且最大限度地改写和丰富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内容和文学取向”(杨洪承语)。
惟其如此,1943年春天姚雪垠一到重庆,即受到国共两党和进步文艺界的热情欢迎——不仅送他一顶“战区来的杰出作家”桂冠,而且所有报刊都争先恐后为他提供着登场亮相的机会:1月,《文艺杂志》发《创作漫谈》; 2月,《新华日报》副刊发《需要批评》; 3月,《抗战文艺》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特刊发《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 5月,重庆《大公报》副刊《战线》发《略论士大夫的文学趣味》; 同月,《抗战文艺》发《风雨时代的插曲》; 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文艺论文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 同月,《国民公报》发《我的学校(一)初学记》; 8月,《新华日报》发《论深刻》……姚雪垠2月抵渝,4月即当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创作研究部副部长。 所有这一切,宣示了进步文坛对其抗战文学作品的认同,宣示了“文协”对其率先践行“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导向,深入前线掘取“战壕真实”,在新型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高度肯定与褒扬。
光阴似水,日月如梭,七十多个春秋一去不返。 历史早已翻开新的篇章,却不敢忘记我们曾经的苦难与辉煌。 2015年9月2日下午,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等单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召开“姚雪垠抗战文学作品座谈会”。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在致辞中强调“这个会议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夕,我们召开一个著名作家的一个人的关于抗战题材的作品座谈会,这在我们作家协会,在文坛,我所知道的,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所以,这是一种殊荣。 这种殊荣既属于姚雪垠,也属于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属于那些齐聚“文协”麾下“以笔为枪”为抗仇寇保家国奔走呼号的前辈作家,更属于那些为抵御外侮保国保种而默默倒在了抗日战场上的民族英雄们。
注释:
[1][4]《璇宫感旧诗》,《无止境斋诗抄》(为姚雪垠书系第15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15页。
[2][3]《四月交响曲》(为“姚雪垠抗战作品选”之一种),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9-130页、123页。
[5][6][7]《战地春讯》(为“姚雪垠抗战作品选”之一种),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139页、142页、139页。
[8]《兴奋的日子开始了》,《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为姚雪垠书系第17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2页。
作者:许建辉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7806.html

2023-2024JCR鐟滄澘宕幖鐑藉炊閻樿尙鎽�

SCI 閻犱胶鍎ら弸鍐焻婢跺﹤鐏侀柕鍡曠劍婵洨绮欑憗銈傚亾娴i攱鍙忛柛銉у仜閸欏繘骞愰崶褍纭€

SSCI缂佲偓閸欍儳绐楃紒澶嬪灥椤掔喖寮甸悢宄扮亖闁硅埖娲滄灙閻犙冨椤旓拷

濞戞搩鍘奸ˇ濠氬棘閸ャ劎澹嬮煫鍥у暞濠€锟犲礆婵犱胶鐭欑紓浣哥С缁楀矂骞庨弴鐘屽綊骞愰崶褍纭€

sci闁告粌顔抯ci闁告瑥鏈弫纭呫亹閺囩喐鍩傞柛鎺炴嫹

EI闁衡偓鐠鸿櫣绉块柣銊ュ閼垫垿宕堕懞銉﹀焸闁告帪鎷�

闁告艾瀚鐔虹矓閹插檻ci

闁告艾瀚鐔虹矓閹插樈i

闁告艾瀚鐔虹矓閹辩牪ci

EI闁哄牏鍠庨崹鎿烶XSourceList

闁告ê妫楅惇缍緎sci闁哄秶枪缁洪箖寮甸悢宄扮亖婵懓娲﹂埀顒婃嫹

闁告ê妫楅惇缍緎cd-濞戞搩鍘煎ù妤冪矓閹存繍鍔呯€殿喗娲橀弸鍐极閻楀牆绁﹂幖瀛樻尰濞奸潧鈹冮幇顓熷焸闁告帪鎷�

CSCD闁挎冻鎷�2023-2024闁挎冻鎷�

濞戞搩鍘鹃~鏍⒔閵忕姴鐎婚柛鏍細閵嗭拷2023

濞戞搩鍘煎ù妤冪矓閹寸偛螚闁哄秶枪缁洪箖寮甸悢宄扮亖闁告ê妫楅惇楣冩儎椤旇偐绉�

2023妤犵偛顕晶妤佺▔椤撶偞绂囩紒澶嬪灦婵⊙囧冀缁嬭法濡囬柡鍫㈠枎閸ㄦ棃鎯勯鑲╃Э闁挎稑鐗愰崵婊堟倿閸撲緡娼犻悗娑宠缁憋拷

2023妤犵偛顕晶妤佺▔椤撶偞绂囩紒澶嬪灦婵⊙囧冀缁嬭法濡囬柡鍫㈠枎閸ㄦ棃鎯勯鑲╃Э闁挎稑鐗忛妵鐐村濮橀硸娼犻悗娑宠缁憋拷

闁告ê妫楅惇楣冨礌濡も偓閵囧洭寮界粙璺ㄥ

2023闁绘鐗忛鍥础娴e搫顣煎☉鎿冨幗閺嬪啴寮界粙璺ㄥ闁烩晩鍠栫紞锟�

2023-2024JCR鐟滄澘宕幖鐑藉炊閻樿尙鎽�

SCI 閻犱胶鍎ら弸鍐焻婢跺﹤鐏侀柕鍡曠劍婵洨绮欑憗銈傚亾娴i攱鍙忛柛銉у仜閸欏繘骞愰崶褍纭€

SSCI缂佲偓閸欍儳绐楃紒澶嬪灥椤掔喖寮甸悢宄扮亖闁硅埖娲滄灙閻犙冨椤旓拷

濞戞搩鍘奸ˇ濠氬棘閸ャ劎澹嬮煫鍥у暞濠€锟犲礆婵犱胶鐭欑紓浣哥С缁楀矂骞庨弴鐘屽綊骞愰崶褍纭€

sci闁告粌顔抯ci闁告瑥鏈弫纭呫亹閺囩喐鍩傞柛鎺炴嫹

EI闁衡偓鐠鸿櫣绉块柣銊ュ閼垫垿宕堕懞銉﹀焸闁告帪鎷�

闁告艾瀚鐔虹矓閹插檻ci

闁告艾瀚鐔虹矓閹插樈i

闁告艾瀚鐔虹矓閹辩牪ci

EI闁哄牏鍠庨崹鎿烶XSourceList

闁告ê妫楅惇缍緎sci闁哄秶枪缁洪箖寮甸悢宄扮亖婵懓娲﹂埀顒婃嫹

闁告ê妫楅惇缍緎cd-濞戞搩鍘煎ù妤冪矓閹存繍鍔呯€殿喗娲橀弸鍐极閻楀牆绁﹂幖瀛樻尰濞奸潧鈹冮幇顓熷焸闁告帪鎷�

CSCD闁挎冻鎷�2023-2024闁挎冻鎷�

濞戞搩鍘鹃~鏍⒔閵忕姴鐎婚柛鏍細閵嗭拷2023

濞戞搩鍘煎ù妤冪矓閹寸偛螚闁哄秶枪缁洪箖寮甸悢宄扮亖闁告ê妫楅惇楣冩儎椤旇偐绉�

2023妤犵偛顕晶妤佺▔椤撶偞绂囩紒澶嬪灦婵⊙囧冀缁嬭法濡囬柡鍫㈠枎閸ㄦ棃鎯勯鑲╃Э闁挎稑鐗愰崵婊堟倿閸撲緡娼犻悗娑宠缁憋拷

2023妤犵偛顕晶妤佺▔椤撶偞绂囩紒澶嬪灦婵⊙囧冀缁嬭法濡囬柡鍫㈠枎閸ㄦ棃鎯勯鑲╃Э闁挎稑鐗忛妵鐐村濮橀硸娼犻悗娑宠缁憋拷

闁告ê妫楅惇楣冨礌濡も偓閵囧洭寮界粙璺ㄥ

2023闁绘鐗忛鍥础娴e搫顣煎☉鎿冨幗閺嬪啴寮界粙璺ㄥ闁烩晩鍠栫紞锟�
閻犲洤鍢查敐鐐哄礃濞嗗簼绻嗛柟顓у灲缁辨繈宕欐潪鏉垮/濞戞挻鎸搁崺锟�/闁搞儴妫勯崬瀛樺緞閿燂拷/濞戞搩鍙€鐎氭娊寮敓锟�/闁稿繈鍔岄鐔虹矓閹寸偞鍩傞柛鎺戯攻鐢綊鎳¢幇顏嗙憿闁告瑦鍨奸妴鍐箰閸パ屽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