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在诗歌的风箱中,臧棣游刃有余地调动风力,鼓冶出许多能激活伟大的暗示的作品。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激活伟大的暗示,主要在于他对语言神秘性力量的调度。 臧棣对于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比如他会认为诗的幸福的核心是人们可以安于语言的智慧,有时他对语言是依赖的,
在诗歌的“风箱”中,臧棣游刃有余地调动风力,鼓冶出许多“能激活伟大的暗示”的作品。 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够激活“伟大的暗示”,主要在于他对语言神秘性力量的调度。 臧棣对于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比如他会认为“诗的幸福的核心是人们可以安于语言的智慧”,有时他对语言是依赖的,比如他会认为“对于诗的境界而言,最根本的还是,让语言来决定想象。 ”但是语言的这种所谓“神秘性力量”,对于臧棣而言也许并不神秘。 虽然他将诗的语言看作是“对应于神秘的召唤”,但实质上诗的语言的本质不过是“实验性的”。 正因为是“实验性的”,所以这其中可以挖掘的“可能性”便是无限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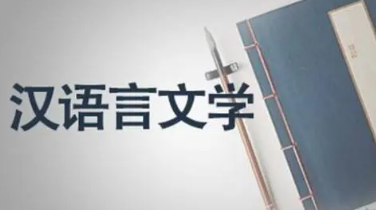
臧棣曾经对瓦雷里的“纯诗主义”感兴趣。 瓦雷里后来颇为关注物本身的象征性和词语本身之间的关系,曾声称“一个词的激发功能是无穷无尽的”,而这与臧棣在诗歌实践中注重语言的繁复以及语义的再生成有着重要关联。 举他的《蓝盐简史》一诗的前三节为例来看:“不同于那些常见的/白色结晶,以及奢侈的贫穷中/你有一个关于人类的偏见/只能靠它来纠正。
文学论文范例: 浅谈英美文学中的生态批评认识
//首先,你得学会面对/你的伤口是蓝色的——/非常深,深到傍晚的空气/仿佛被神秘的疼痛狠狠稀释过; //清洗必须及时,以及最关键的,/抓一把,撒到伤口上,/你会听到一只亲爱的狮子/从你身体里发出过震天的吼叫”。 读这首诗,我有两点最直观的感受,一是对诗歌语言的“好奇”,二是诗歌似乎带着“面具”。 其实,臧棣本人对于诗歌语言就带有好奇心,他曾说:“我们最需要的诗,是从语言的好奇心开始的诗。 ”而诗歌也“只能深刻于语言的好奇”。
从《授粉师》来体会一下:“刚刚翻越过四十不惑,/流大汗流得像黑熊并不满足于/用芭蕾的脚尖踮起/一个硕大但却优美的身躯; /中年男性,可疑的魅力/定型于再无耻辱可供洗刷; /而骄傲并未过时,但温和作为/一种生命的效果,会自动阻止/他过度反省:这所谓的不惑/像不像专为中年男性设下的/一个分寸感十足的局。
//……而迷人的香气/则来自阳光的抚摸。 过滤在/微风中,两性花多么捷径。 /譬如,黄瓜花就很善于雌雄同株。 /轮到人能否经得住人心的考验时,/你必须和他一样确切地知道:/在茎秆的低位上开放的,/通常是雄花,而那些晶莹的花粉/只有借助细细的毛刷,才会完成/一个小小的秘密。 没错,不太起眼,/却关键得近乎宇宙还有悬念”。 我觉得这种“好奇”,一方面来自于语言本身所带有的美感和“寓意”特性,另一方面则主要来自于诗人对语言和句子的“心凝”与“形释”,以及如何将语词与外在的物理事象加以“冥合”。 对于诗人而言,处理好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绝对是一项本领。
在诗歌语言上,臧棣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从他所主张的“诗人成熟于语言的傲慢”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臧棣认可诗歌的“面具性”,认为“面具,是诗歌送给语言的最好礼物。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转换,西方学者对诗歌在功能上的变换曾有非常敏锐的分析:“诗在技巧上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准; 他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 越来越成功地坚持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个人的感觉,以致完全脱离社会,直至先是感知然后是感觉都全然不在了。 ”
“诗人为生活所迫——即为个人经验所迫——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词汇和起组织作用的价值。 ”(考德威尔著《幻想与现实》)这段话明显指出诗歌在功能上有从社会层面到个人层面转化的一面,诗歌写作越来越“坚持个人对生活的感知与个人的感觉”,甚至开始“集中注意力于某些词汇和起组织作用的价值”。 但“危机”有时就意味着“出路”,因为这恰恰暗示了诗歌的另一种重要功能——话语功能。
“诗歌话语一直力图保持的就是语言创始活动中对意义的敏感性,对感受自身的敏感性。 ……对诗歌话语而言,话语活动是一个永无终结的启蒙过程,是对人类敏感性与感受性的持久的启蒙,也是语言的自我启蒙,即对意义感知领域的无限拓展。 这是诗歌话语的双重功能,既参与建构社会的象征视阈,也消除那些已经固化的社会强制仪式或堕落为仪式形态的象征主义。
诗歌话语忠实于感受性、敏感性,不断开启对意义新的感知方式,同时忠诚于隐秘的象征秩序,致力于未完成的象征主义视域的建构。 ”(耿占春著《失去象征的世界》)诗歌话语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话语”! 读臧棣的诗歌,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臧棣的诗歌“安于语言的智慧”,致力于对语言的挥斥与重构,为诗歌在“话语功能”的开拓上留下了巨大可能性。
作者:赵目珍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8690.html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2023-2024JCR影响因子

SCI 论文选刊、投稿、修回全指南

SSCI社会科学期刊投稿资讯

中外文核心期刊介绍与投稿指南

sci和ssci双收录期刊

EI收录的中国期刊

各学科ssci

各学科sci

各学科ahci

EI期刊CPXSourceList

历届cssci核心期刊汇总

历届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CSCD(2023-2024)

中科院分区表2023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历届目录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

2023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社会科学)

历届北大核心

2023版第十版中文核心目录
请填写信息,出书/专利/国内外/中英文/全学科期刊推荐与发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