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发表咨询在线!

本文摘要:摘要:生、死、爱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三大主题,诗人龚学明始终怀着一颗悲悯的诗心,在时间与空间的场域中,对文学的三大主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诗性探索。他对死亡痛苦的思索、探寻着死亡的本质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做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人一直在寻找着生命的来处
摘要:“生、死、爱”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三大主题,诗人龚学明始终怀着一颗悲悯的诗心,在时间与空间的场域中,对文学的三大主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诗性探索。他对死亡痛苦的思索、探寻着死亡的本质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做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人一直在寻找着生命的来处,在诗人看来,自何处来的生命本源不可知,但可以预知生命的去处。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龚学明的诗正是这样的有境界之诗。
关键词:现代诗,灵魂,龚学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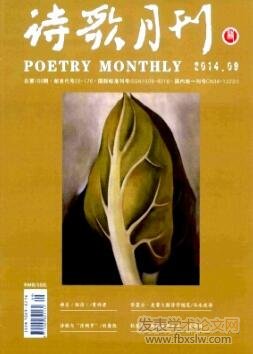
爱默生说:“在地平线上有一种财产无人可以拥有,除非此人的眼睛可以使所有部分整合成一体,这个人就是诗人。”[1]龚学明无疑就是拥有这样一双慧眼的诗人。“生、死、爱”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三大主题,龚学明始终怀着一颗悲悯的诗心,在时间与空间的场域中,对文学的三大主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诗性探索。
一、对生命无常悲叹的同时唤起对生命的赞美和珍惜
生命无常,人生易老,自古无人可以逃脱,面对死亡我们都有相同的惊恐和无助。尤其眼睁睁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离去,龚学明无法抑制自己的巨大悲痛,然而痛苦中,他依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将一己之悲,化为所有人的悲情,将人世无常与天地万物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用反衬的手法,以天地万物永恒的轮回反衬出生命的短暂……他在《遗址》一诗中写道:哦,五千年历史又怎样?父亲们拥有相同的惊恐:面临死亡那一刻多么无助2016年我的父亲走入古人队列离他们近,距我们远我相信,五千年的冬天都是一样的风吹落苦楝树的叶子龚学明对死亡痛苦地思索,探寻着死亡的本质和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做哲学意义上的思考,死亡是万千生命的重新孕育和轮回,是自然不断轮回中的一种,是对宇宙不可知的探索,死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痛苦的思索中,诗人对生死已经有了自己坚定的信仰,灵魂是不死的,它是超越死亡的永恒:鸟声稀有,而田地湿润,孕育植物的轮回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拿着鸟兽和神人纹饰的玉器,向不可知跪拜然而活着的我们还对生死有着不可逾越的恐惧,对生与死的一体,在矛盾中犹疑着:“而我们,在这么多年后,对生死仍疑惑不决”。有了对死亡坚定信仰的龚学明,又在不断进行着寻根的求索:这太湖流域的荒蛮之地我的母亲告诉我,我们是北方人我高大的身材和宽大的脸庞都异于夷人。
至此,我对根的挖掘陷于茫然但又有多少人能找到遥远的来处我们在不明不白里变成石头的粉末、树的眼神人一直在寻找着生命的来处,这是千百年来一直叩问不已的关于生命哲学的追问: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在诗人看来,自何处来的生命本源不可知,但我们可以预知生命的去处,终究要化灰、化石头的粉末,只有灵魂成为树的眼神,长久地注视着这生生不息地变化着又恒久不变的宇宙。龚学明对这千百年来的哲学难题有他独到的注解,有他独到的领悟……龚学明的《荒原》有着同样的悲叹之美,有冷峻的悲伤,有节制的情绪,有真切的难以捉摸的神秘和难以表述的不可知。我的泾上村,我爱的相思我的荒原,我无奈的生命我的时间不多天将黑———真正的黑将消灭万物:我们一无所见让我走近这最后的芦苇夕阳的象征让你们烦躁劲风吹出力的坚决———每一株高大芦苇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男人的不屈……历史镜头中的高耸物,是一座墓碑:我将在墓碑里朗读诗歌,走完一生龚学明感叹生命无常的同时,坚定生死也如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轮回,为此不断唤醒人们对生命的赞美和珍惜:我愿意承认此刻是美丽的不要向后追忆,不要随云远思水菖蒲的叶子多于黄花密集而细长的绿叶因风而生风一来,它的柔美比风柔美娇嫩的浅黄在河水清澈的记忆下一次比一次沉入沟纹深处。
泰戈尔在《美的亲证》一文中说,“通过我们的真理观,我们认识了宇宙中的规律;通过我们的美感,我们领悟了宇宙中的和谐……我们对物质世界中的和谐理解得越来越充分,我们的生命对创造之喜分享得越多,我们在艺术中对美的表现就变得更具有真正的普遍性……美是真,真是美。”[2]因此对美的感悟,就是在万事万物的关系之中,感受和谐在自然事物和自身形态之中的充分统一。
龚学明正是感受了大自然此刻和谐的柔美。一切都是多余的,哪怕美好的追忆,哪怕诗意的远方,都无法撼动此刻的和谐美好!花与叶相互辉映,风与叶柔美相交,清澈的河水深深地倒映着这美好,多么和谐!多么宁静!这生命之美,超越了一切,此刻,岁月就是这样静好,诗意就是这样灿烂!爸爸珍爱人世的短暂他手握蒲扇,遥望星空的背景在风的现实中谋划/他对细微之事和琐碎的人生一样重视爱用娟秀的心思记录/他将物质放大不愿浪费一丁点神的恩赐人生虽然短暂,但是爸爸,何其珍爱他所拥有的这短暂的人生!世俗琐碎的生活,爸爸快乐地接受,星空之上的美好愿景爸爸一样拥有,他用细腻的心思去捕捉生命里点点滴滴的美好,他把这一切都视为神的恩赐而倍加珍惜。维多罗夫说:“一位诗人,应该讲述那些少了他,便永远没有人讲的东西。”[3]龚学明的诗填补了“长久被漠视的父亲的诗学意义,唤回了被忘却的父性,这一自持而自尊的文化隐喻。”[4]
二、对生命和生存的审视
对着陷入焦灼之中急匆匆赶路的现代人群,有担当的诗人龚学明借他喜爱的意象“冰痕”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冰面上/它过于光滑/就像人生是圆滑的”,每个人都是猫着腰行走,小心呼吸,讨好生活,唯恐怠慢打翻了眼前的苟且,即使这样小心翼翼,圆滑世故,“它的厚薄和何时冰裂/我们并不能测定/而冰窟窿的寒冷,是真实的/它在真相的最底层/冷冷等待全部的落水者”,依然不能做到周全于所有,生活依然会不可预料地塌陷,依然会让自己陷入不可知的深渊,人世的薄凉冷彻入骨抑或陷入灭顶的绝望,四顾茫然,无力而无助……生活如同这晃荡的怪物难以解释它一天天占领高地一次次覆盖血迹它白色的刃尖有毒的轻吟……越向深处走去陌生的风声呼啸不能拨开迷雾已经远行的父亲怀中的猫……浅浅的叫声利爪的影子隐现龚学明通过陌生化及蒙太奇的手法把“晃荡的怪物、白色的刀刃、有毒的轻吟、陌生的风、迷雾、远行的父亲、怀中的猫、浅浅的叫声、利爪的影子”这些意象,组合成一组奇异、神秘、诡谲的画面,把谜团一样复杂而艰辛的生活,如电影放映一般呈现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意境充满无限的诗意和无限的张力,熟悉又陌生,似是而又非。“好的诗歌,会像一把尖锐的锥子,扎进人的惰性的血,使之震动、惊奇,获得一种对生活的超常感受”。龚学明说,“诗歌有时可以进入神性写作,不受意识控制,获得奇句”。
这一组诗句,正是神来之笔,神识组合,你不必去深究它的意思,只要感觉这神秘的境界即可,艺术的存在,旨在唤回人们对生活的感受。生活空间如此逼仄,生活只剩苟且,人们却如此满足,把空虚当美好:即使无事可做也心满意足花朵一样的心情只要开在春天里说“我没有受冷落”又说,“好吧,我描摹一个人的坐姿”空虚,无所事事的生活,只要还有人关注自己,就心满意足,“我”早已不是“我”,“我”只是别人的模仿者,“我”更像是没有灵魂的“我”的复制品,仿佛镁光灯下笑容灿烂寻求关注的小丑……玻璃厚实没有新鲜的风灯光过白白得像老生常谈像一些嘴在斗嘴语言多么苍白其实,它的脚很想出去走走但它立刻按住自己:“不可乱动,一动就要失去”它庆幸只是一念之闪那些走累的椅子散了骨架而更多的空椅子在后面排队单调重复、不变的生活,老生长谈,乏味憋闷,在这里如失去水的鱼,要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
外面精彩的世界,无限的风光,有着无限的吸引,世界这么大,多想去走走!但是习惯已经让自己害怕失去所拥有的,哪怕是让自己喘不过气的憋闷的生活,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甚至庆幸自己没有妄动,没有丢弃这鸡肋的位置,因为还有那么多人虎视眈眈自己的位置,还有那么多人因为随意妄动失去了这个位置……这是一群“不为什么”活着的人。对于一个关注社会现实,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感的诗人,当然不会在上述的生存状态里沉沦,他是逃离、超越这逼仄的空间的,这如夜般压抑的黑:“夜晚总在猎杀我,我侥幸逃脱/它在我的额头留下晕眩/在我的腰间留下酸痛/它让我白天背上部分的黑”。读到这儿,不禁想起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那个囚禁自由的监狱,“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只有真正坚强的人可以救赎自己,只有伟大的人救赎自己的同时也救赎别人。
就像影片中瑞德的名言:有些鸟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因为它的羽毛太过美丽。诗人就是那只关不住的鸟,是伟大的救赎者,他用诗歌的翅膀飞翔,拯救,唤醒……龚学明说:“我的世界观、宗教观是有神论的,人是派遣,万物也是,都是生命的依托。”其实,它不是我我是神一手操纵的,像云朵被伟大的天气操纵但我更愿意躺在水面上我愿意被水托着带走(我会一点浮水),我愿意这生活之水上柔和一些,带我向东向西最后,我愿意在水中沉没那么温柔,那么干净地死龚学明是神派遣的一朵祥云,渴望纯净温柔的水面包围着自己,任意东西,没有黑暗没有邪恶,这是神性笼罩的洁净之地,这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彼岸,这是所有干净的灵魂最后的归处……
三、对生命真情的体验
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龚学明的诗正是这样的有境界之诗。王国维评价李煜的词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5]王国维引用尼采的话,赞美后主的词是用真心和血写成的,是饱蘸真情的好词,唯有情真则意切。龚学明书写至爱亲情的诗何尝不是“以血书者”?从父亲的病情变化直到父亲去世,每一首诗都感人至深,记录着当时的心路历程,对父亲至真至纯的情感跃然纸背之上,正如龚学明自己所言:这组诗,很多是流着泪写完的。依稀,我们可见纸中洇出的泪光:那个正飞翔的是我的父亲吗?已从自己躯体分离从熟悉的衣服和笑容中分离———从母亲的恸哭和悲伤的唢呐中分离———从繁复的烟火味中分离。
他手中抓着微风灵活而又轻盈。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我看不到他,听不到他,抓不住他我。失去了亲爱的父亲这是父亲去世那天,龚学明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写就的诗。诗写得极其隐忍,忍住泪,忍住哀,读诗的我们,却读得泪水涟涟,心痛连连,我们似乎看到喑哑的声音在呼唤:父亲,那是你么?尤其,最后“我”后的那个句号,那种哽咽难言,那种痛彻心扉……都在这停顿里缠绕。“一首诗的情感张力也在这里,在失去亲人的大哀痛与形式之间,一首诗的深度不是来自情感的直接表白,而是深蕴在情感的节制中。”[6]
《手机》也这样倾诉,这样克制着:“父亲已在阳光的背面/好想拨那个熟悉的号码/但我不敢”。明知那个号码再也无法拨出,却依旧幻想着,可以再听一听那熟悉的声音,可以再感受那来自父亲特有的关爱,但“我”在不敢中克制着冲动的情感,也克制着思念的泪水。王国维的意境说,强调一个“真”字。有意境的诗歌是能够写出融入作者真挚情感的景物,即“情景交融”“融情于景”,龚学明的这些诗作皆是以心会景、心物交融的佳作。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一文中也指出:“一切美底光是来自心灵的源泉,没有心灵的映射,是无所谓美的。”[7]
龚学明的《这些树》就是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有境界的景物诗。多么敏感的树。神说,生命与生命必须区别———看到白云就微笑看到雨水复流泪是柳树吗?心中模拟透明的镜子它爱美丽有很强的自尊心在清澈的水面上写一次次被风吹走一个诗字越写花开得越多是合欢树吗?风中,热烈的表达它写自己的爱情写父母的爱情写人间各式的爱———耿直的爱如泥土迷离的爱似春雨香樟树!高举,树冠的呐喊这些田野里惯见的粗犷写意有正义感新欢日出用笔椽子更粗的笔写田野里的大海广袤的丰收也写夜晚星星月亮(略有隐忧的沉默死寂)与其说这些树,不如说是有着敏感心灵的人,他们向往白云那样的自由纯粹,他们善感多情,“看到雨水复流泪”。
柳树有颗玻璃心,爱美且自尊心强,写出一首首如花的诗;合欢花,用饱胀的情感写人类各式的爱;香樟树是粗犷伟岸的男子汉,正义、有胸怀、有成就,也有夜的柔情,有星星月亮般通透的温柔情怀。用当代著名的诗人车延高对龚学明诗作的评价来作结语:“纯粹是具有穿透性的。要么干净,可以听见滴水穿石之音;要么致命,可以直抵饱含情感的灵魂。”[8]
诗歌论文投稿刊物:《诗歌月刊》办刊方向以“专题策划”为主旨迄今推出“博客专刊”“中国诗歌地理专刊”“安徽新诗阵线合刊”“中间代诗歌理论合刊”“中国文艺复兴特大号”“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合刊”“中间代诗人21家合刊”“中国新诗90年90家合刊”等在诗界内外反响强烈被视为官刊民办的典范.
转载请注明来自发表学术论文网:http://www.fbxslw.com/wslw/21626.html

2023-2024JCR闁荤喐绮嶅妯虹暦椤掑嫬绠归柣鎴f閻愬﹪鏌eΟ鍨毢闁规枻鎷�

SCI 闂佽崵濮抽懗鍫曞磿閵堝鍑犻柛鎰靛枟閻掕顭跨捄鐚村伐闁诲繋绶氶弻鏇㈠幢閺囩姴濡芥繝娈垮枛濞层劎鍒掑▎鎴炲晳闁靛牆鍊告禍鎯归敐澶嬫暠闁告瑥绻橀弻娑㈠Ψ瑜嶆禒婊堟煕濞嗗繒绠绘鐐村姍瀹曟儼顦茬痪顓涘亾

SSCI缂傚倷璁查崑鎾绘煕濞嗗秴鍔ょ紒鎰殘缁辨帗寰勭€n亞浠村銈嗗笧閸犳牕顕i悽鍛婂亜鐎瑰嫭澹嗘禍鏍⒑绾懎鐓愭繛鍙夌矋閻忔瑩鏌i悩娆忓暙椤忣剚銇勯弮鎾村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婵傛潌鍥ㄧ節濮橆剚顥濋梺鎼炲劘閸斿孩绔熺€n喚鍙撻柛銉戝啯娈插┑鐘亾闁跨喓濮寸粈鍡椻攽閻樿精鍏岄柣顓熺懅缁辨挻鎷呴崫銉愶紕绱掑Δ鈧惌鍌炵嵁鎼淬劌鍗抽柣妯鸿嫰缂嶅﹪鐛幇鏉跨倞鐟滃秶娑甸埀锟�

sci闂備礁鎲$划宀勵敊閹剁棗i闂備礁鎲¢悷銉╁嫉椤掑嫬鏋佺痪顓炴噷娴滃綊鏌¢崶鈺佹瀾闁糕晛鍊块弻娑㈠箳閻愭潙顏�

EI闂備浇銆€閸嬫捇鎮规ウ鎸庮仩缂佸娼¢弻锝夊Ω閵夈儺浠归梺鐓庣仛閸ㄥ灝鐣烽崼鏇熷殟闁靛绠戦悞鎼佹⒑閸涘﹤閲滈柟鍑ゆ嫹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绫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Ο鍧�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佺浜悧鐚歩

EI闂備礁鎼悧蹇涘窗鎼淬劌鍨傞柟璺ㄥ厡XSourceList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窏ci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р攽椤旂偓鍤€婵炶绠撻崺鈧い鎺戯攻鐎氾拷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穯d-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鐡ㄧ换宥夊礉閸涱垪鍋撳▓鍨灍婵炲弶锕㈠鎼佸礃椤斿吋鐎梺缁橆殔閻楀棛绮婇敃鍌氱閻庢稒蓱鐏忕増绻涙總鍛婃锭闁崇懓鍟撮獮鍥敇閻旈鍔梻浣告啞鐢亪骞忛敓锟�

CSCD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2023-2024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妤e喛缍栭柡宥庡幗閳锋棃鏌曡箛鏇炐㈤柣搴☆煼閺屾盯寮介鐘电獥闂侀潧妫撮幏锟�2023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顕崑娑滅亣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⒑閸涘⊕顏勎涘Δ鍛剳濡わ絽鍟崕搴€亜閺冨洤浜圭紒澶涙嫹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佸姍瀹曢潧饪伴崼鐔封偓鍧楁煕閹捐尙璐版繛鑲╁█閹鈽夌€圭媭鍚呯紓浣瑰敾閹凤拷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绻樻俊鐢告倷閺夋埈鍤ゅ┑顔斤耿绾ǹ岣块悩缁樺€垫繛鎴濈枃椤撹櫣绱掗幉瀣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ㄣ偅閸愩劎顦卞┑掳鍊愰崑鎾绘煏閸パ勫枠鐎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

2023闂備胶绮〃鍛存偋韫囨侗鏁勯柛銉墮绾偓婵炶揪绲介幖顐︺€傞悡搴樻闁瑰灝鍟獮妤呮煛鐎n亜鏆g€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梻浣哄劦閺呪晠宕伴弽顐ょ闁跨噦鎷�

2023-2024JCR闁荤喐绮嶅妯虹暦椤掑嫬绠归柣鎴f閻愬﹪鏌eΟ鍨毢闁规枻鎷�

SCI 闂佽崵濮抽懗鍫曞磿閵堝鍑犻柛鎰靛枟閻掕顭跨捄鐚村伐闁诲繋绶氶弻鏇㈠幢閺囩姴濡芥繝娈垮枛濞层劎鍒掑▎鎴炲晳闁靛牆鍊告禍鎯归敐澶嬫暠闁告瑥绻橀弻娑㈠Ψ瑜嶆禒婊堟煕濞嗗繒绠绘鐐村姍瀹曟儼顦茬痪顓涘亾

SSCI缂傚倷璁查崑鎾绘煕濞嗗秴鍔ょ紒鎰殘缁辨帗寰勭€n亞浠村銈嗗笧閸犳牕顕i悽鍛婂亜鐎瑰嫭澹嗘禍鏍⒑绾懎鐓愭繛鍙夌矋閻忔瑩鏌i悩娆忓暙椤忣剚銇勯弮鎾村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婵傛潌鍥ㄧ節濮橆剚顥濋梺鎼炲劘閸斿孩绔熺€n喚鍙撻柛銉戝啯娈插┑鐘亾闁跨喓濮寸粈鍡椻攽閻樿精鍏岄柣顓熺懅缁辨挻鎷呴崫銉愶紕绱掑Δ鈧惌鍌炵嵁鎼淬劌鍗抽柣妯鸿嫰缂嶅﹪鐛幇鏉跨倞鐟滃秶娑甸埀锟�

sci闂備礁鎲$划宀勵敊閹剁棗i闂備礁鎲¢悷銉╁嫉椤掑嫬鏋佺痪顓炴噷娴滃綊鏌¢崶鈺佹瀾闁糕晛鍊块弻娑㈠箳閻愭潙顏�

EI闂備浇銆€閸嬫捇鎮规ウ鎸庮仩缂佸娼¢弻锝夊Ω閵夈儺浠归梺鐓庣仛閸ㄥ灝鐣烽崼鏇熷殟闁靛绠戦悞鎼佹⒑閸涘﹤閲滈柟鍑ゆ嫹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绫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佽褰冨Ο鍧�

闂備礁鎲¢懝鍓р偓姘煎墴椤㈡鎮㈤搹鍦厠闂佺浜悧鐚歩

EI闂備礁鎼悧蹇涘窗鎼淬劌鍨傞柟璺ㄥ厡XSourceList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窏ci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р攽椤旂偓鍤€婵炶绠撻崺鈧い鎺戯攻鐎氾拷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礊缁跺穯d-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鐡ㄧ换宥夊礉閸涱垪鍋撳▓鍨灍婵炲弶锕㈠鎼佸礃椤斿吋鐎梺缁橆殔閻楀棛绮婇敃鍌氱閻庢稒蓱鐏忕増绻涙總鍛婃锭闁崇懓鍟撮獮鍥敇閻旈鍔梻浣告啞鐢亪骞忛敓锟�

CSCD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2023-2024闂備焦瀵ч崘濠氬箯閿燂拷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妤e喛缍栭柡宥庡幗閳锋棃鏌曡箛鏇炐㈤柣搴☆煼閺屾盯寮介鐘电獥闂侀潧妫撮幏锟�2023

濠电偞鍨堕幖鈺呭储閻撳篃鐟拔旈崘顏嗙厠闂佺懓顕崑娑滅亣闂備礁鎼粔鑸电仚缂備焦妞界粻鏍ь嚕閻㈠憡鍋勭€瑰嫭澹嗘禍鏍⒑閸涘⊕顏勎涘Δ鍛剳濡わ絽鍟崕搴€亜閺冨洤浜圭紒澶涙嫹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佸姍瀹曢潧饪伴崼鐔封偓鍧楁煕閹捐尙璐版繛鑲╁█閹鈽夌€圭媭鍚呯紓浣瑰敾閹凤拷

2023婵°倗濮烽崑娑㈩敋椤撶喐娅犳俊銈勮兌閳绘梹銇勯幘璺轰沪缂佸倸娲ㄧ槐鎺撳緞鐎n亞浠告繝纰樺閸パ冨敤缂備礁顑堝▔鏇熶繆閸ヮ剚鐓涢柛顐犲灩閺嬪酣鏌涢妸锔筋棃闁诡垰瀚伴、娆撴嚃閳哄唭顓㈡⒑閹稿海鈽夐柣妤€绻樻俊鐢告倷閺夋埈鍤ゅ┑顔斤耿绾ǹ岣块悩缁樺€垫繛鎴濈枃椤撹櫣绱掗幉瀣

闂備礁鎲¢敋婵☆偅顨婇幆鍥ㄣ偅閸愩劎顦卞┑掳鍊愰崑鎾绘煏閸パ勫枠鐎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

2023闂備胶绮〃鍛存偋韫囨侗鏁勯柛銉墮绾偓婵炶揪绲介幖顐︺€傞悡搴樻闁瑰灝鍟獮妤呮煛鐎n亜鏆g€殿喚鏅划娆戞崉閵娿儺娲梻浣哄劦閺呪晠宕伴弽顐ょ闁跨噦鎷�
闂備浇宕垫慨鏉懨洪妶澶婂簥闁哄被鍎查弲鏌ユ煟閹邦剚鎯堢紒鈧崘鈺冪闁糕剝顨堥崙鍦磼鐠囧弶顥㈤柡宀€鍠栭、妯款槻闁诲繗灏欑槐鎺撴綇閵娧呯杽閻庤娲橀悷锕€岣块鍫濈骇闁割煈鍣ḿ锟�/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箰婵犳艾绠伴柟闂寸閺勩儵鏌ㄩ悤鍌涘/闂傚倷鐒﹂幃鍫曞磿閺夋嚦娑㈠礋椤栨俺鍩為柣搴㈢⊕閿氱紒鍓佸仱閺屻劑鎮ら崒娑橆伓/婵犵數鍋為崹鍫曞箹閳哄懎鐭楅柍褜鍓熼幃妤€顫濋鐐╂灆閻庢鍣崜鐔煎极閹剧粯鏅搁柨鐕傛嫹/闂傚倷鑳舵灙缂佽鐗撳畷婵嗙暆閸曞灚鏅㈤梺缁樻濞咃綁鎯岄幘缁樼厵閻庣數枪娴狅箓鏌涢埡浣糕偓鍧楀蓟濞戙垹绠抽柟鎼灡閺侀箖鏌i姀鈺佺仩缂傚秴锕獮濠囨晸閻樿尙鐤€濡炪倕绻愬Λ娑㈠箟閸ф鈷戦柛娑橈功閹冲嫰鏌涢妸銉e仮濠碘剝鎸冲畷姗€顢欓懖鈺婂敹闂備焦鎮堕崕婊呬沪閼恒儺鍟�